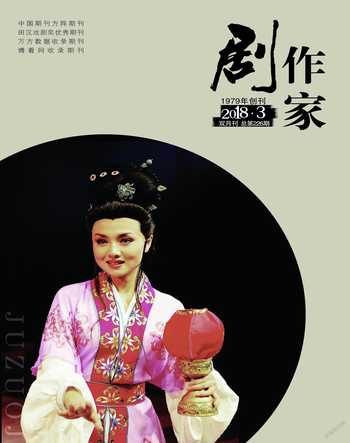出了象牙之塔后
2017年是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這一年,黨的十九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數據顯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共推出50臺劇目,其中包括17臺新創劇目,11臺原創劇目以及33臺復排劇目。全年演出共計794場,全年觀眾達29萬人次左右。其中上海市內演出602場,包括進社區演出45場、進學校演出85場,進樓宇和商圈演出23場,下基層演出53場,近4.8萬社區、學生、白領觀眾受益。國內巡演165場,境外巡演27場。
北京話劇演出穩定增長,全年演出4915場,同比增長7.8%。其中兒童劇市場火熱,科普劇、歷史劇等創新形式與寓教于樂相結合,受到親子家庭歡迎,全年共演出了3848場。
這一年,各類話劇活動紅紅火火,“紀念中國話劇110周年演出季”“紀念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展演”“全國話劇優秀新劇目展演季”“第三屆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活動”等競相登場,但是優秀劇本的缺失、戲劇票價過高等老問題仍未有轉變的跡象。
從新劇目來看,主旋律題材話劇創作一枝獨秀,但手法陳舊、主題先行的老毛病依舊存在,缺少突破,亟待總結與反思。
中國話劇是110年前在時代變革的潮流中萌生的,草創之初,缺少劇本、導演、演員、觀眾。如今,這“四缺”的問題基本解決,隨著社會的發展及藝術表現形式的多元化,新的矛盾又浮現出來,等待著更多的戲劇人去開掘、去破解。
是貴族藝術還是大眾藝術?
主旋律題材話劇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現象,以往有過不少探討。一般來說,這類作品體現了一個時代的主流精神,在提振人心、凝聚共識、表達正能量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也更能夠得到政府的重視與褒揚,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影響甚大。
2017年,主旋律題材話劇仍然是各個國有院團原創的重點,國家話劇院的開年大戲《人民的名義》是一部現實主義反腐大戲,由周梅森編劇,王曉鷹導演。據介紹,該劇藝術地再現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反腐斗爭的驚心動魄,為觀眾呈現出一場反腐高壓下信念與權欲的博弈。國家話劇院的《谷文昌》是文化部慶祝十九大召開重點創作的劇目。全劇講述了谷文昌在擔任福建省東山縣委書記期間,對黨忠誠,心系百姓,讓“荒島”變為“寶島”的事跡。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大型話劇《國際歌》聚焦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上海,全劇通過對具有堅定革命信仰的夏若冰的形象塑造,表現了一批有志青年懷揣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背負中華民族的希望,發動并依靠工人階級,踐行《國際歌》的題旨與要義,在危難中不畏懼、不退縮、不逃避,堅定勇敢地尋求著中國未來之道路。天津人藝推出的大型原創航天題材話劇《九天攬月》,是向建軍90周年獻禮之作。講述了畢業于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火箭博士鄭華強,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放棄了美國豐厚的待遇,投身于中國導彈研究事業的故事。武漢人藝的大型原創話劇《王荷波》截取了黨的紀檢工作奠基人王荷波革命生涯中的幾個片段,再現了他從一名普通鉗工歷練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生命歷程。遼寧人藝的大戲《開爐》演繹了東北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期,英雄的奉天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除奸、抵抗活動。寧夏演藝集團話劇院的《閩寧鎮移民之歌》展現了寧夏生態移民搬遷歷史工程,講述了在移民搬遷的過程中移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表達了移民群眾對中央及地方黨委、政府實施生態移民這項民生工程的感恩之情。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話劇團創作排演的敘述體話劇《從湘江到遵義》展現了湘江戰役后,紅軍將士面臨多路強敵圍追堵截、內部思想不統一等困境,在迷惘、焦灼、痛苦中憑借堅定信念艱難探索,最終迎來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遵義會議的召開。
這些主旋律題材話劇投入巨大,不乏名編劇、名導演、名演員加盟,獲得了包括國家藝術基金在內的各類資助與嘉獎,媒體也提供了相當大的篇幅進行報道,但似乎并未得到相應的觀眾認可與市場肯定。原因還是老問題:觀念陳舊、缺乏新意、主題簡單、摻水嚴重。一些主旋律題材話劇的“速朽”,不僅是公共資源巨大的浪費,還對戲劇生態造成破壞,并且潛在地帶來了話劇創作新的危機。
為紀念話劇誕生110周年,文化部、中國文聯聯合召開了座談會。會議在回顧了中國話劇的110年歷程后指出:我國的話劇事業面臨新機遇,也面臨新要求。一些話劇藝術工作者就聚焦現實題材創作等方面做了發言。話劇藝術家徐曉鐘談道:中國話劇110年的歷程,形成了有我國歷史特點的傳統。他認為:當下中國話劇面臨著許多重要課題,比如話劇工作者如何面對新語境下多元化文化需求的觀眾。“為了適應劇場‘新觀眾的需要,部分戲劇的創作者和組織者著意迎合低級趣味、娛樂需求,存在著浮躁、短視、急功近利等現象。有的話劇創作缺乏生活根基,文化蘊涵缺失;有的小劇場戲劇‘快餐化,也有某些大劇院的戲劇‘不接地氣,存在著思想不夠精深、藝術不夠精湛、制作不夠精良的問題。”
比起一些泛泛的表態,徐曉鐘的話還是比較中肯的。中國話劇面臨的重要課題還可以再加上一條:如何警惕貴族化與狹隘的功利主義傾向。話劇是舶來品、洋玩意兒,自其發生便具有啟蒙色彩,為了落地生根,曾自覺地借鑒傳統戲劇,很快便成為一種新興的大眾文化。錢理群先生曾指出:中國話劇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搖擺于廣場藝術和劇場藝術之間,而中國現代話劇正是在廣場戲劇與劇場戲劇相互對立與滲透中得到發展的。110年過去,脫離現實生活,脫離最廣大的人群所思所想,唯領導、專家口味的現象層出不窮,“投資是政府,領導是觀眾,獲獎是目的,倉庫是歸宿”,這個順口溜形象地揭示了當下一些所謂大戲創作的實質。歷史上,戲劇消費也曾經為少數精英階層所獨占,但在消費社會階段,伴隨著大眾文化的成熟,話劇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作為一種精神產品,承擔著傳播文化、思想和價值觀的重要作用。一旦孤芳自賞,成為“圈子文化”,它的貴族化傾向漸顯,也就不可挽回地喪失了大多數觀眾,最終陷入絕境。
我們不時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話:“原來主旋律話劇也可以這么好看,這么感人,這么接地氣。”這真是莫大的諷刺。主旋律并非福星高照,也非洪水猛獸。問題的出現,是我們對這類題材創作的理解不夠深入,進行了貌似討巧,實則低級化、庸俗化的呈現。
2017年的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上,《酗酒者莫非》應該是最受關注的一部戲劇作品。該劇由波蘭導演陸帕根據中國作家史鐵生的小說改編。五個小時的演出時長,令每個人都會在這部戲里找到屬于自己的共鳴,并沉浸回味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酗酒者莫非》也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它表現了現代人普遍存在的苦惱與困惑。陸帕說:“戲劇更像一個儀式。它比心理專家更能幫助我們自我了解,也更可能改變人生。我們在看戲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新的思考問題的角度。”
這便是戲劇存在的價值。
商業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嗎?
“知乎”上有一個帖子《為什么話劇票的價格這么高?》,其中寫道:“作為一種大眾藝術,話劇的票價怎么這么高,這樣如何能大眾化?而與之相比,一張電影票卻要便宜得多。”
筆者大致看了一下后面的跟帖,倒是總體上為話劇的高票價做各種各樣善意的說明。票價這個問題過于復雜,牽涉到不同的體制、政策、規模等問題,但做戲能賺錢,也無需隱瞞,開心麻花不是已經成為“中國話劇第一股”了嗎?由《盜墓筆記》小說改編的話劇,第一部總票房近3500萬。第二部僅首輪演出就狂卷2000萬票房,刷新了國內話劇市場的多項票房紀錄。陳佩斯的喜劇《托兒》,在全國各地連續演出達120場,票房近4000萬元。一家有影響的刊物還登出了這樣標題的文章:《中國話劇:資本正在到來,時代剛剛開始》。
話劇的商業化,不是什么新鮮話題,贊成也好,反對也罷,它都在那里。正方的觀點是,可以促進話劇市場的繁榮,吸引更多觀眾;反方則認為,這樣做無異于飲鴆止渴,話劇會因此沾染銅臭,變得膚淺。
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之中,簡單地否定一個從前沒有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不過,我們的確發現,當下戲劇生態中的某些問題,確與所謂的市場化有關。
在2017年的中國話劇舞臺上,我們不缺乏主題先行、內容淺白之作,但深入內心、叩擊靈魂、引人深思的力作卻是稀缺品。本來,即便從戲劇史的角度看,這樣的作品同樣不可多得,那些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來自漫長歲月的累積。但至少我們能夠感覺到一代一代的戲劇人努力的方向。
在現實中,如果說,國有劇團的天平常常向“政治正確”的一方傾斜的話,民營機構則更多是在商言商。一些團體與從業人員對劇作的選擇常常是“生意眼”。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專業劇場演出的話劇場次中,60%以上為民營戲劇團體創作演出,2017年的數據尚未見到,但無疑為上升趨勢。
民營戲劇團體沒有政府的資助,家底兒要自己攢,一切依賴票房,于是,為賣座、贏利,或走明星路線,或走“大IP”路線,對嚴肅的題材敬而遠之。一位制作人直言:國有院團的話劇,都“太嚴肅、苦大仇深。人們笑不起來。看完以后心情不舒暢”。于是,在一部號稱情感喜劇的說明書上,我們看到了這樣似是而非、曖昧含混的《導演的話》:“兩性關系探討了千年,到現在基本都成了隔靴搔癢的無用功。當繁育后代不再是必要的前提,兩性關系似乎有了無限的可能。現代國家的崛起、自由精神的張揚、個人價值的追求,給人們享受生命之美、兩性關系的愉悅提供了便利與動力。”
當劇場里充斥著迎合當下、迎合個人趣味的戲劇產品,衡量藝術的審美標準就變得混亂,許多演出,從話劇藝術的角度看毫無價值,甚至在倒退。這種因追逐利潤而生的現象甚至在向一些不差錢的國有院團滲透,一些頗有成就的導演迷戀于所謂的民族化、眼花繚亂的大制作、載歌載舞,以吸引觀眾的眼球,這已經失去了話劇應有的性質。審美上與當代世界戲劇的差距在拉大。戲劇學者丁羅男指出:“繁榮的戲劇舞臺,離不開黃鐘大呂般的大制作,也缺不了短小精干的舞臺表達。”在他看來,當下話劇市場之“火”,明顯偏重于商業類戲劇而非小劇場創作。“2017年全國小劇場戲劇優秀劇目展演”于9月在北京舉辦,21部參演作品中,話劇有12部,戲曲有9部。但是,數據顯示,這幾年,小劇場話劇的演出場次、票房收入都在持續下降。
2017年11月1日,彼得·布魯克的最新作品《戰場》在上海戲劇學院實驗劇場開演。30年前,彼得·布魯克排演了9小時的劇場史詩《摩訶婆羅多》,轟動世界劇壇。而《戰場》則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進行重新創作,全長只有70分鐘。聯合導演瑪麗·赫蓮娜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彼得希望人們去聆聽某種寧靜、寂靜。這種寧靜、寂靜并不是那種強加于人的,而是大家一起分享的一種寂靜。當敘事足夠強的時候,人們就可以做到靜下心來去聆聽這樣的一種寂靜。”正因為如此,《戰場》的風格簡潔、干凈,展現了一位戲劇大家返璞歸真的追求。遺憾的是,中國戲劇界并不買賬。一些業內人士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太簡單了”“大師也不過如此”等等。在話劇舞臺日益綜藝化、娛樂化的當下,他們忘了,一點都不酷炫華麗恰恰是話劇藝術的本原。
相比中國電影,話劇從策劃創作到宣發營銷,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在大眾傳媒發達的時代,對劇目進行廣泛宣傳,擴大影響,吸引觀眾,天經地義。但如今的話劇要靠過度包裝與宣傳才能收到一定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悲哀。網上不負責任的叫賣,最終為高票價找到合理的理由,許多戲動輒上千元的票價,令許多真正熱愛話劇的觀眾因為買不起票無法走進劇場。長此以往的惡性循環、竭澤而漁,話劇的市場永遠不能真正地紅火起來。
“話劇熱”背后隱藏著的這些問題,需要從體制、機制上加以理順,國家話劇院副院長王曉鷹曾表示:話劇正處于“新時期戲劇”以后又一個繁榮時期,參與戲劇創作的力量更為多元,演出的場次和觀眾人次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數量,票房業績更是以前難以想象的。“話劇在‘走市場的最初過程中,可以用娛樂性的作品去探尋發展之路。但是,一定要避免泛娛樂化的現象。”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總經理楊紹林也指出:“放眼全球,我們能非常清楚地認識到,戲劇這個行業的定位應是非營利的,就中國話劇市場現狀來看,離這一步還很遙遠。”希望這樣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
觀看之道
2016年,英國學者尼爾·麥克格雷格的《莎士比亞的動蕩世界》一書引進中國出版。從這部有趣的書中可以了解到,伊麗莎白時代,公共戲劇是一種全新的商業娛樂形式,觀眾來到劇場看戲,往往帶著各種水果、點心,甚至酒精飲料,這與現代劇場的秩序完全不同。今天,中國的話劇觀眾都是有著體面職業收入和高雅情趣的人,彬彬有禮的他們不會在劇場中做任何不得體的舉動。但是,關于話劇,一份說明書是不夠的。
2017年北京人藝的一些劇目引發了購票長龍,據報道,2017年6月話劇《茶館》開票時,有觀眾凌晨3時許就排隊買票,開票僅6個小時,《茶館》的12場演出票就全部售罄,680元的最高票價一度被炒到了3000元。此種火爆現象還吸引了一些外媒的注意,視為中國“文化消費環境大有改善”的佐證。此外,烏鎮戲劇節的一票難求,二、三線城市出現話劇熱等,都是一些為戲劇界津津樂道的新聞。
但是,必須指出,與話劇觀眾的增加相比,“審美準備”卻不容樂觀。許多年輕觀眾進劇場,不過是嘗嘗鮮,是一種缺乏持續性的行為。一些人或許只是為了發個朋友圈,獲得點贊。話劇票務市場在逐漸地向二、三線城市下沉,以此尋求新的增長點。這不能說是壞事,但話劇的審美,最終是不可能像某些商業電影那樣,靠討好“小鎮青年”來完成的。
演后交流是很多劇團、劇場喜歡的一個做法,但有質量的交流委實有限,雖然很難判斷積極參與、勇于提問的觀眾是否代表話劇觀眾的主流,但比起國外同類場合,眼下話劇觀眾的戲劇常識以及對戲劇的理解的確不容樂觀。有業內人士表示:我們不能只“適應”,只“服從”,更不能無原則地一味“遷就”,甚至對非健康、非審美的創作傾向不做辨析、批評,一味聽之任之。
2017年,學者易中天首次擔任編劇的話劇《模范監獄》在京滬兩地演出,吸引了不少觀眾。戲的選材、立意都令戲劇界耳目一新,但平心而論,編劇技術上的問題很多。導演或許“懾于”名人的威力,舞臺呈現循規蹈矩,缺乏新意。凡此種種,一般觀眾很難辨別判斷,除了新聞媒體一味地叫好,似乎也沒有戲劇界的專業人士對此客觀地加以評析。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鑄劍》的演出。第七屆林兆華戲劇邀請展閉幕大戲《鑄劍》先后在上海、哈爾濱、北京上演。該劇改編自魯迅的同名小說,特邀波蘭導演格熱戈日·亞日那與中國演員合作,著名演員史可在劇中飾演母親莫邪,飾演國王的是波蘭表演藝術家萊赫·洛托茨基。《鑄劍》表達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對經典著作的理解。演出后,觀眾分歧很大。有人認為創作者誤讀了魯迅的作品,看不懂;有人認為“外來的和尚”被高估了。本來這是個可以進行很好的學術探討的案例,但無論是演后談環節,還是后來的媒體報道,均未見到嚴謹、客觀的評價與對觀眾的有效引導。
話劇110年,媒體上照例又熱鬧了一陣,但也只是熱鬧了一陣而已,缺少反思,無關憂患。比之于人,110歲是罕見的高壽,但對一種藝術樣式來說,卻很年輕。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戲劇傳統,我們不必為中國話劇比古希臘戲劇遲到了兩千年、比莎士比亞小了四百年而妄自菲薄。當我們跋涉于這條艱苦而神圣的戲劇之途、一頁一頁書寫著我們自己歷史的時候,卻應落筆莊嚴,愛惜名譽與光榮,否則,到了120年、130年,我們又將拿什么作為華誕之禮呢?
(張曉歐: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