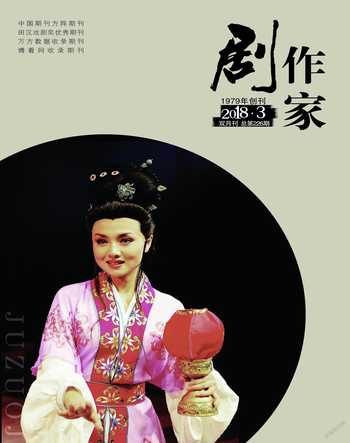《維羅妮卡的房間》:一出好看的商業戲劇
李志娟
百老匯經典驚悚劇《維羅妮卡的房間》自演出以來一直備受關注、經久不衰,該劇的編劇艾拉·萊文是美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曾創作小說《羅斯瑪麗的嬰兒》《死前之吻》和電影《魔鬼圣嬰》。
演出開始,隨著幕布緩緩拉開,在暗淡的光線下,觀眾便開始進入該劇所營造的奇特幻覺之中。年輕的女子蘇珊娜和新交男友拉里,在波士頓市郊的一個旅館邂逅了一對中年夫婦后,被帶入莊園里一個塵封已久的房間。舞臺被布置成一個密閉房間的模樣,家具皆被罩上白布。隨著白布被揭開,觀眾可看到一個典型的少女房間——以美式田園風格裝潢,靜置著床鋪、沙發、桌椅、櫥柜、梳妝臺等等,書桌上有留聲機和相冊,小茶幾上擺放著一副拼圖。隨著白布一同被揭開的是一個破碎的南方舊夢,觀眾隨著舞臺上演員的言語和動作,緩緩地觸碰到這個家庭的黑暗之心。
在維羅妮卡的房間里蘇珊娜和中年夫婦進行著漫長的交談。夫婦倆自稱是家中的仆人,他們認為蘇珊娜長得酷似死去的維羅妮卡,因此希望她能留下來做短暫的角色扮演,去安慰重病中的茜茜。茜茜是家族中唯一存活下來的孩子,和維羅妮卡之間存在著親情的羈絆。
或許是看見這個家族始終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蘇珊娜動了惻隱之心。劇情發展至此,觀眾能從中感受到一絲不祥的端倪,例如茜茜始終未曾出現,老夫婦似乎在極力掩藏什么,蘇珊娜的男友拉里究竟是什么身份,等等。隨后,蘇珊娜獨自在維羅妮卡的房間里,穿上維羅妮卡的洋裝,把頭發梳得和維羅妮卡一樣。蘇珊娜成為了維羅妮卡,從這一刻起,劇情急轉直下。
中年夫婦再次上臺,然而已不是之前的模樣。一直佝僂著的老婦突然直起腰板,換上利落肅穆的黑色套裝,她的丈夫身著黑色西裝,成為一位不怒自威的工廠廠長。當蘇珊娜感到情況危急,想要中斷所謂的“演出”時,中年夫婦則以家長不容置疑的威嚴口吻,一遍遍地告訴她:你不是別人,你是1935年的維羅妮卡。
由于在觀賞過程中觀眾始終是站在和蘇珊娜相同的視角——觀眾和蘇珊娜一樣不了解中年夫婦和拉里,對維羅妮卡的房間發生過什么充滿好奇。對蘇珊娜的認同感是觀眾很快入戲的原因。因此,當面對“1972年蘇珊娜”身份的突然剝奪和被囚禁、擺布、監視的慘狀,觀眾易將自身代入,從而陷入和蘇珊娜同等的恐慌中。如何證明“我是我”以及證明自己的身份,成為接下來本劇的核心劇情。顯然,在封閉的空間里,外部時間的流逝無從知曉,中年夫婦因而擁有絕對權威,蘇珊娜也將奮起反抗。
但是,在維羅妮卡的房間里,一切物件似乎都在證實蘇珊娜是精神分裂的病人:中年夫婦找出一箱她曾經扔到樓下的求救紙條,桌上收音機里播放著1935年的廣播,日記本里有精神分裂者寫下的故事。中年夫婦為蘇珊娜找來的心理醫正是她的男友拉里。眾人一致表示是蘇珊娜精神錯亂,將醫生拉里幻想成自己的男友并編出多種身份。導演更是采用了多種特效,如鏡中鬼影、鬼娃娃等營造詭異的氛圍,使維羅妮卡的房間成為一個充滿不祥征兆的恐怖區域。在蘇珊娜的反抗過程中,能證實她是精神病的細節也越來越多,觀眾恍惚,甚至開始慢慢地認為蘇珊娜就是維羅妮卡幻想的人格。
劇情看似反轉,實則依舊疑點重重。觀眾仍不能完全確定那個波士頓的大學生“蘇珊娜”是否真實存在,拉里為何排斥肌膚觸碰,中年夫婦的真實身份是什么,房間里究竟隱藏了怎樣的過去。情節環環緊扣,懸疑層層疊加,秘密與謊言交織,觀眾探求真相的欲望愈加強烈。
蘇珊娜在舞臺上逐漸崩潰,當承認了自己就是維羅妮卡的時候,老婦開始扮演了一個審判者的角色。她用力為蘇珊娜梳頭,并把邪惡的罪名加在她身上。維羅妮卡其實是一個擾亂家庭秩序者,她勾引父親,誘奸弟弟,甚至殺死了妹妹茜茜。此刻,劇情將蘇珊娜扮演的維羅妮卡從一個單純的精神病者變為一個惡魔,又一次反轉,維羅妮卡的形象再一次復雜化。劇情的高潮則是老婦真正行使了審判的權力,將替代維羅妮卡背負罪惡的蘇珊娜殺死在維羅妮卡的房間里。
蘇珊娜死去了。舞臺的燈光也恢復了正常。中年夫婦又恢復之前佝僂的老態,拉里拖曳死去的蘇珊娜,把尸體帶到另一個房間。隨后,觀眾從舞臺上三人的話語中了解到有關維羅妮卡及整個家族的更多信息,一點點拼湊出事實的真相。直到幕落的那一刻,觀眾們才能穿透層層的迷霧,知道在維羅妮卡的房間里發生過什么——劇情反轉了,原來,老婦就是維羅妮卡。在她的童年時期,她的母親溺愛茜茜而不愿接近她,只因童年所受的暴虐與責罰,她有了驅不散的童年陰影。在青春期的時候,她為了報復母親,開始引誘父親和弟弟,并殺死茜茜。等長大后,她和弟弟結婚了。她所犯下的罪行也得到了懲罰,維羅妮卡和弟弟生下的禁忌之子也背負著不能觸碰女性的苦痛,她成為妄想型精神病人,永遠無法踏出心靈的房間。
劇情發展至此,《維羅妮卡的房間》具有了濃厚的精神分析學及心理學色彩。精神分析學說創始人弗洛伊德始終將人性中邪惡的“陰影”與兒童期的創傷聯系起來,認為童年期所受的陰影會作為一種始終被壓抑的情感常存于意識之中,甚至能誘發人格分裂。老婦正是因為童年創傷而屢屢犯下暴行,她一次次將“維羅妮卡”的身份強加在被拐騙來的年輕女子的身上,以此逃離自己的身份和過去,并通過扮演審判者角色來掩藏體內真實存在的自我。
人格分裂始終是驚悚戲中屢見不鮮的元素。作為一出商業戲劇,導演和編劇都無意向觀眾探索分裂人格和人類意識之間潛藏的奧秘,單單把人格分裂作為一個噱頭,一個吸引看客的驚悚元素,一個給劇情更百轉千回的合理解釋。《維羅妮卡的房間》在情節設置上充滿了戲劇張力,并有一個由“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組成的線性時間結構。每一次情節的轉變都充滿了懸念與驚奇,采用的多媒體影像技術及燈光、音樂的配合更將氛圍渲染到令觀眾毛骨悚然、驚叫連連的程度。因此,在導演、劇本、演員、舞美、燈光等各項都達標的基礎上,人文關懷不過是錦上添花。
懸疑戲劇的結局往往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戲劇的結尾,觀眾看到了亂倫、戀尸、精神分裂、童年陰影、密室兇殺、連環命案等多種元素的雜糅。誠如有學者所言,按照逃避主義美學原則,商業電影會盡量避開枯燥的日常現實和敏感的政治、歷史現實,采取非現實化敘事。《維羅妮卡的房間》擁有強烈的戲劇沖突、跌宕起伏的情節設置、異于常人的人物設定、密集直接的心理刺激,可以看出這是一部娛樂性強的商業戲劇。商業懸疑劇并不是舞臺的全部,卻最能將觀眾吸引到劇場。誠如希區柯克所言:“每個人都享受一場完美的謀殺。” 走進劇院的觀眾無意從劇中感悟到藝術的深刻與真實,所需要的不過是通過揭秘過程得到某種強烈刺激,在勞碌都市生活中享受片刻休憩與愉悅。
懸疑劇的娛樂性特點使其從來不缺乏觀眾,這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經久不衰、南派三叔的作品改編劇場場爆滿的原因。在越來越多的戲劇習慣打著“非商業”“藝術”“實驗”的旗號,來掩飾其匱乏的戲劇技巧和空洞無物、毫無才華本質的今天,觀看一出如《維羅妮卡的房間》這樣目的單純、追求感官和心理刺激的商業戲劇,不失為一個不錯的消遣選擇。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