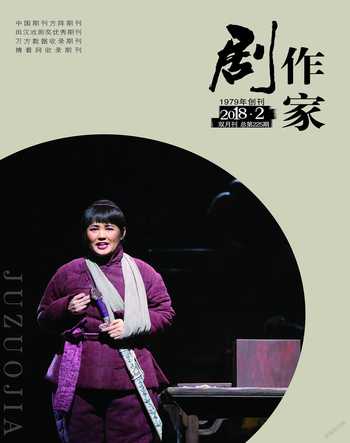學會死亡?學會生活
朱琳
這是一部聲名遠播的作品,幾乎所有看過這部戲的朋友都向我推薦。起初我對這部戲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僅從名字上來看,幾乎可以斷定這是一部悲劇,即提到了“最后”那或許是一部跟死亡有關的戲。持懷疑態度是因為太多與“死亡”題材相關的作品都在極力營造一種悲劇氣氛,無論從燈光、音樂的設計上,還是演員臺詞、語氣的處理上,無時無刻不彌漫著濃重的“死亡”氣息,讓觀眾“不得不”感受到死亡這一情境,因而悲從心中來。這種由環境影響情緒的方式是我不喜歡的,我認為真正催人淚下的作品,一定是以情節取勝,而非外在因素。但對于金士杰老師的表演我一直是欣賞佩服的,因此最終還是走進了劇場。
誠如所料,《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課》果然是一部圍繞“死亡”這一話題的戲。戲中一個叫米奇的學生,畢業之后迫于生計放棄了原本的愛好和夢想,成為了一名成功的記者。在一個深夜訪談節目中,他看到被訪者竟然是曾經與自己相伴多年的大學教授莫里。然而此時的莫里已經不再是在學校時意氣風發的模樣,取而代之的是他患上了絕癥——肌萎縮型脊椎側索硬化癥,也就是我們近些年有所了解的“漸凍癥”。這種病無藥可醫,可以說從得病的那天開始,幾乎每天都能夠感受到自己日漸僵硬,直至最終器官喪失功能,然后死亡。人快要死了,我得去看看他。懷著這樣的心情,時隔十六年,米奇第一次去拜訪了莫里。沒想到的是莫里并沒有垂死之態,反而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為例,用最后的時間為學生上了關于人生的十四堂課。內容豐富,像和煦的春風融化了米奇那顆日益世故的心。
幾乎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死亡”成為了每一個中國人都很忌諱的詞。我們總會發現這樣的例子,如果一個人的家中有新生的嬰兒,那么所有的親朋好友都會去慶賀,可如果一個人的家中有人逝去,那參加葬禮的人多半是憂郁哀痛,并且參加完儀式就希望盡快離去。我們沒有人會刻意注意死亡,我們的文化不鼓勵我們去關注死亡,我們都希望盡量地躲開死亡。可是,死亡并不會因為我們的懼怕、我們的閃避就遠離我們。無論我們多不愿意承認,但死亡的確是一種必然。更有人指出,我們生來就是為了死亡的,這聽上去非常悲觀。而莫里老師就是告訴我們,既然死亡是一種必然,那么不必刻意躲閃,張開雙臂,擁抱它。他為此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文化體系:“你要知道自己會死,并且隨時做好準備……這樣你在活著的時候,就會比較投入。”正是由于這樣的一種心態,在這最后的十四堂課里,他能那么淡然地談論那些困擾學生米奇、同時也困擾著我們的一些問題。
看這部戲時觀眾普遍有很強的帶入感,劇中的米奇跟生活中的我們是那么的相似。我們沉溺于老師的表揚之中,我們為自己的成就喜不自勝,我們以忙碌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認為自己在群體中至關重要、必不可少,并以此為借口來推脫責任,背叛承諾,不以為意。我們自認為自己很幸福,畢竟我們獲得了物質上的滿足,我們得到了他人的肯定,我們實現了社會價值。可是當夜深人靜,只有你一個人躺在床上的時候,“遺憾”“孩子”“死亡”“家庭”“婚姻”等等這些或虛或實的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或許因為忙碌,這些問題被忽略了,但它們從來不曾消失。當我們想一探究竟的時候,米奇作為代言人向莫里老師提了這些問題,于是觀眾們便自然地像學生一樣靜靜傾聽,等待老師答疑解惑。而說來奇怪,為我們解疑的這位老師身患絕癥,每天都感知著自己的身體又“死”去了一部分,同樣,他也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由于感知到了死亡而絕望、懊惱、痛苦。但在這之后,他仍然保持著每天接待訪客,為這些他認識或不認識的、對生活充滿焦慮和疑慮的人解決問題,盡管只是簡單的聊聊天,但無論是米奇還是其他訪客都受益良多。一個瀕死之人究竟是懷著怎樣的心去做這些事情的呢?“施舍同情,讓我覺得我還活著。”這便是莫里老師的答案。我想,用善良、博愛這樣的詞無法去描繪這樣美麗且豐富的心靈,唯有說他是一個好人。他希望所有人既然還活著,就請順從本心,快樂地生活。因為要 “學會與自己和平相處” ,“活得不開心還不如死去”。
這或許是每一個“心靈雞湯”都有的內容,是最淺顯的道理,可我們真的明白嗎?更多的時候相比于思考,我們更心安理得地忙碌著,被手機、微信、網絡占據著生活,電話一個接著一個,一天有時間做五份報表,但沒有時間感受友情、親情、愛情。我們只為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活著。于是,越來越多的感情被我們忽略了,那些跟感情相關的事被我們日漸拋棄了。這也是為什么畢業時米奇答應了莫里老師會回去看他,但一拖再拖,直至老師身患重病。于是他懷著想要表達慰問的心給莫里老師打電話。
“你好,我找莫里·施瓦茨教授。”
“你是哪位呀?”
“我是米奇·阿爾博姆。”
“米奇呀,你怎么敢不叫我教練呢。”
這是時隔十六年后師生之間的第一次對話,“一本正經”的米奇以一顆沉重甚至帶有憐憫的心打給老師。他以為光陰荏苒,老師早已不記得他是眾多學生中的哪一個,可沒想到,莫里老師非但沒忘記他是誰,并且連兩 人在學校期間互相獨有的稱呼都記得清清楚楚。演出到了后半部分,米奇對莫里老師有介紹——莫里老師家里的什么都是舊的,電視、衣櫥都是舊的,我想是因為他的內心被情感填滿,所以在物質上才會無欲無求了。如果人在精神豐腴和物質滿足上只有一個選擇,那么莫里老師選擇了精神,這讓他很幸福,甚至無懼死亡,他說“一棵樹的葉子最好看的時候,就是落葉之前”。而米奇,或者說這十六年中的米奇選擇了犧牲夢想以盡快達成物質要求,他覺得自己很成功,可莫里老師一語道破:“成功?這是么?不快樂的成功是不幸福的。”“你和你的心能和平相處么?很幸運,我現在可以。”多年來米奇一直試圖忘記舅舅罹患胰腺癌時因化療而脫發嘔吐的慘狀,更希望的是忘記那時落荒而逃的自己,于是他避忌死亡,與莫里的第一次會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希望更多地炫耀現在的自己,他不愿意談莫里的病。面對莫里告訴他“我快死了”,他很客套地勸慰:“沒事的,沒事的。”他拒絕與莫里的“加分項”——擁抱,因為他認為這樣客套的交際是不該談論死亡這種深刻沉重的主題的,于是第一次的見面以米奇的“逃走”結束。但莫里有自己的魔力,他這種劍指內心的洞察力吸引著米奇再次拜訪。隨著拜訪的頻繁和深入,米奇自己本身對于這每周二的會面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期待,同時他愿意像上學的時候一樣,帶著食物去探訪他,在談話時也越來越能放下工作,敞開心扉,將困擾自己多年的問題一一拋出。隨著莫里老師的解答,他也越來越多地感受到生活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了。于是在最后我們看到,他放棄了工作中的競爭,他只想為老師的離去痛哭一場。而更可喜的是,最后他重新彈起了鋼琴——他年輕時的最大愛好。通過對莫里老師死亡的解讀,他明白了到底要怎么活著。
作為觀眾,我的眼淚幾乎從開場到散場就沒有斷過。事實上不僅僅是我自己,演出到了下半場,啜泣聲已經彌漫在整個劇場當中。這的確是一部讓人哀傷的戲,但卻毫無上文所提到的刻意營造死亡氣氛的那種形式感。相反的,之所以這么哀傷,更多的是因為在演出進行中喜劇因素的穿插。我是在看了戲劇演出之后又看了原版小說《相約星期二》,從中能感到的悲劇體驗與話劇版相比著實少了許多,我想大概原因也在于此。小說更直觀地記錄了十四堂課的內容,而戲劇演出中透過演員的表演和導演的二度創作,為這部本應“死氣沉沉”的戲注入了新的活力。金士杰飾演的莫里老師在告訴米奇自己日后將無法活動要靠人抱著的時候,毫無自怨自艾的語氣,相反他用了一種極其滿足,甚至帶有炫耀的口氣跟米奇說:“被人抱來抱去也不錯,感覺自己像個嬰兒。”其實米奇跟觀眾都知道,這是他自己化解尷尬、自我安慰的一種方式,而事實是當他需要被人抱起來的時候,意味著他病情的加劇,這里用喜劇化的手法處理人物語言,反而更能讓觀眾感受到莫里教授內心的安逸樂觀與他身體所受病痛之間的巨大反差,令我們在敬佩莫里的自嘲精神和更清晰地認識到苦難深沉之中深受感動。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活人葬禮”是另一個很鮮明的例子。莫里老師認為人們會在追悼會上對已經逝去的人說很多很好聽的話,可是死的那個人卻什么都沒有聽到,于是他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就舉行了這樣的一場葬禮,并且鼓勵自己的學生,“你也該試一試”。看似滑稽可笑的一件事,其中卻滿含悲情色彩,可謂悲中帶喜、喜中帶悲,觀眾在悲喜交加中不自覺地被帶入情境之中,為不久后莫里老師的逝去而哀傷不已。除了在人物臺詞的處理上,劇中還在環境的悲喜對比上來刻畫人物。例如米奇拿著雞蛋沙拉去看莫里老師時,嘴里向觀眾描述著他們以前在學校共進午餐的情景——莫里老師吃著雞蛋沙拉跟他談天說地的時候他總要躲閃來自莫里老師嘴里噴射出的“黃色小子彈”。這里用了一個極其幽默的比喻,讓觀眾忍俊不禁。再見到雞蛋沙拉的莫里也高興得像個孩子似的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叉,但是他已經不能熟練地使用餐具了,他連一口飯都吃不進去,蔬菜葉子被弄到桌子上、地上,到處都是,他的身上也粘上了沙拉醬。回憶與想象中的美好再次被現實的無情打破。盡管米奇一再說沒事沒事,我們仍然看到莫里老師把頭歪向另一側,張大了嘴,無聲地大哭著。可以說之前的“黃色小子彈”能引起多少的喜劇氣氛,這里的悲劇色彩就有多大。到了演出的最后,莫里老師連說話都吐字含混、氣若游絲了。他跟學生說,在他死后要米奇帶著鮮花和三明治去墓地看他,米奇很悲痛。
“那個時候你卻什么都不能講了。”
“那時候,你講,我來聽。”
“我在一個暖和的下午,在你的墓地里,拿著鮮花,拿著三明治,自言自語。”
當米奇把這個場景再次重復給觀眾講的時候,讓所有觀眾忍俊不禁,這看上去確實是一個不能再可笑的場面了。但其實觀眾都知道,這是莫里老師在彌留之際給學生留的最后一個功課,讓米奇在老師離去之后仍能時刻記得什么是自己所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每個人在聽到那個場面的時候笑了,可笑完之后,眼淚又再次流了下來。而后來我們看到,米奇遵守承諾去看了莫里,他覺得很奇怪,他在這樣一個地方,做著這么奇怪的事情,卻覺得那么自然,原來這是星期二的下午。盡管他的語氣很輕松,卻讓觀眾跟他的情感融為一體,進入到一種無障礙的藝術審美境界,沉浸在對莫里老師——那個每天都離死亡近一點卻仍不斷地溫暖他人的老教授的追憶里。或許我們都該知道怎么死,因為我們必須明白應該怎么活著。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