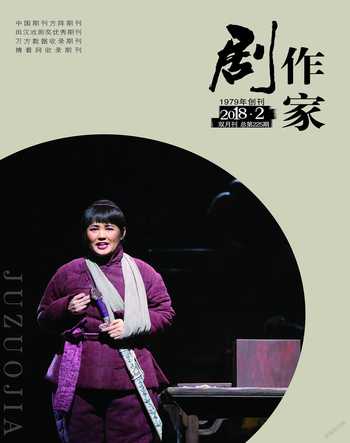漫談戲曲音樂的抒情性
張文敬
戲曲音樂是戲曲藝術獨特的組成部分,中國戲曲同西方戲劇本質上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戲曲的抒情性強于敘事性,而西方戲劇的敘事性則顯著優于中國的戲曲。也就是說,來源于西方的話劇藝術在編織故事情節和矛盾沖突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而傳統的中國戲曲在抒情方面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戲曲的抒情性究竟表現在哪里?顯然,戲曲的抒情性來自于不同戲曲劇種中演員的精彩演唱。《毛詩序》中說:“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這段論述很好地闡明了詩歌與歌詠、舞蹈、音樂之間的關系,以及音樂在情感表達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同屬音樂的戲曲音樂當然也在其中。那么如何在戲曲伴奏中通過技術性的轉換表達,發揮出戲曲音樂的抒情性?
通常來說,戲曲伴奏作為戲曲音樂的組成部分,它的基本職能是“托腔保調”。“托腔保調”是指戲曲樂隊在演員唱腔伴奏過程中所起到的烘托作用以及和演唱者之間緊密合作的關系。“托、裹、襯、墊”是戲曲音樂在“托腔保調”中常用的四種技法。但戲曲的伴奏僅有“托腔保調”是遠遠不夠的,在“托、裹、襯、墊”等技法之外,演奏者還要通過自己對劇中人物的理解和對演唱者的了解,演奏出既符合劇中人物情感所需要的音樂,又不喧賓奪主地使伴奏與唱腔達到完美的融合,從而達到水乳交融和渾然一體的藝術效果。
例如在“板腔體”戲曲類型中,京劇的【二簧三眼】是一個傳統而又常見的板式,在很多劇目中都有這一板式的應用。像《文昭關》中伍子胥唱的“一輪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攢”,《捉放宿店》中陳宮唱的“一輪明月照窗下,陳宮心中亂如麻”和《清官冊》中寇準唱的“一輪明月照窗欞,有寇準坐館驛獨伴孤燈”都是【二簧三眼】板式的唱段。誠然,三個劇目里的三個不同人物所演唱的唱腔都是【二簧三眼】這種板式,但劇目的劇情和人物的身份以及情緒卻各不相同,這就需要演奏者在配合演唱者的同時,烘托出各不相同的意境和情緒來。《文昭關》中伍子胥的身份是一員楚國的武將,但此時卻遭遇滿門被殺的厄運,他一心到吳國借兵報仇,卻被困在昭關。這時伍子胥的心情應該是悲憤和憤懣的,這就要求演員和演奏員分別在演唱和伴奏中既表現出武將身份上的見棱見角,又要突出人物悲憤的情感。相比之下,《捉放宿店》里的陳宮則又是另外一種心境。陳宮起初私放曹操是緣于曹操的人格魅力與遠大抱負,陳宮放棄了中某縣縣令的爵位,本來是要與曹操共圖起義的大事,不料卻親眼目睹了曹操親手殺死了父執呂伯奢的全家。面對曹操“寧可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種殘暴奸雄,此時陳宮的內心充滿著無限的悔恨。“一輪明月照窗下,陳宮心中亂如麻”的唱段也恰是陳宮在深夜暗自自省時發出的感嘆,因此這段唱腔要表現出人物內心的悔恨交加,這與伍子胥的悲憤心情就不一樣了。《清官冊》里寇準的【二簧三眼】唱腔則又是另外一種情形。身為七品縣令,本無資格進京面圣的寇準突然接到圣旨,調他去往京都,又不知調他進京為了什么事。平素一向克己奉公的寇準雖問心無愧,但在此時也很難心如止水,畢竟突然調他進京的原因是未知的,所以在寇準的演唱中要突出人物的猶疑。通過以上簡單的分析,不難比對出雖然是相同的板式,但由于劇情、人物、身份的各不相同,勢必要求演員在演唱過程中運用不同的情感進行應對,以完成音樂形象的塑造。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戲曲音樂所要做到的恰恰是輔助演員挖掘、渲染、烘托出不同的情境與情緒,最終在整體音樂形象的塑造中達到藝術效果的高度統一。
抒情之于戲曲音樂是無處不在的,但這需要演奏者在學習和實踐中,對伴奏的劇目、人物和唱段中的劇情、人物關系、人物內心思想活動以及演唱者有一個整體的了解與把握。除了善于學習和觀摩,還需要演奏者勤于思考和分析,最終才能賦予戲曲音樂以抒情性和音樂形象以靈魂。
責任編輯 李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