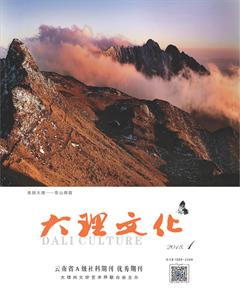《大理文化》的魅力
編者按:
《大理文化》始終堅持以發現和培養本土文學藝術人才為己任,以發掘和弘揚優秀歷史文化為目的,使期刊更加突出了大理特色,彰顯了地域文化,同時兼具開放性和包容性,刊物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因此得到不斷提升。最近,兩位云南省社科期刊的審讀專家李光云和杜雪飛老師對《大理文化》的欄目設置、選發內容、編輯特色、裝幀設計進行了深度精煉的點評,肯定了優點,指出了不足。讓本刊全體編務人員深受鼓舞,對進一步辦好《大理文化》充滿了信心。
如何解決文學期刊與讀者漸行漸遠這一問題,眾多文學期刊使出全身解數,試圖通過更名、改版、名家壓陣、內容添加等辦法手段而突出重圍,但效果依然不佳,最終還是回到了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的四大板塊上來,原地踏步的狀態未得到丁點兒改善。文學期刊缺乏個性的張揚和特色的展示,一度成為編者、作者、讀者之間的熱門話題。近日,筆者在閱讀了《大理文化》月刊2017年第2期、6期、8期后,感覺到文學期刊所遭遇的困境并無束縛住該刊編輯的手腳,他們通過精心的策劃,使欄目所承載的內容,變得豐富而厚實,讓所刊發的作品釋放出文學的思想和文化的涵養,從而抵達讀者的心靈。
十年前,筆者針對《大理文化》,曾寫過一篇《大理文化的品位》的閱評短文,言說了《大理文化》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嚴格遵循辦刊宗旨,立足本土、深挖本土,源源不斷將大理悠久的歷史,絢麗的自然風光,多彩的民族文化充分地展現在讀者眼前,得到了學界的認可和讀者的喜歡。
時過境遷,如今的《大理文化》已由當年的雙月刊變為月刊,以文學為主要內容取代了原本以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全新變化。在變化的過程中,無論是開本的形式、版面的鋪陳以及頁碼增添。還是紙張選擇和印裝質量都有了明顯的提升。特別是精當的欄目設置,使刊出的作品與欄目要素虛實結合、內容緊貼。如2017年第2期“開篇佳作”中的《植物書》,第6期“開篇佳作”中的《村莊在上》,第8期“開篇佳作”中的《隨筆二題》,三篇文章均出自女性作者之手。習習的言物詠志,左中美的記事抒懷,楊海蒂的寫人論道,都使散文、隨筆這種讀者喜愛的文體變得更加靈動鮮活。三位作者將細膩的情感揉進行文流暢的敘述中,使散文回到真實的狀態中。這是因為散文最根本的要素就是真實,而不是胡編亂造。以上三篇作品裝入“開篇佳作”一欄,其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小說平臺”一欄中的《我們的唐克妮》《山行》《823的陰影》《爸爸去哪里》等篇什,是傳統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幾位作者在小說創作中都顯露了文學才華,無論是故事講述、人物塑造、情節安排、細節描寫、語言對話都有較為全面的掌控。只是短篇小說的精致和唯美的表達,是需要長時間的生活積累及千辛萬苦的磨煉才能實現的。于是創作出具有時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真情實感的短篇小說,成了眾多小說家乃至名家追求的夢想。“散文空間”和“詩歌廣場”的設置,無疑為該刊增添了光彩。如果從當今讀者閱讀文學作品的擁有率來看,散文當首,小說、評論次之,詩歌基本無人問津。原因是散文書寫的廣度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且行文的自由觀照了萬事萬物,所以“散文空間”的設置,就顯得十分重要。而詩歌的滑落,是因為一些所謂的詩人不知曉詩歌所具有的特征,陷入了無病呻吟、隨心所欲的泥潭,敗壞了傳統的詩風,難怪讀者感嘆,寫詩的人比讀詩的人多。而《大理文化》則不然,通過“詩歌廣場”一欄推出一大批謳歌時代、贊美生活的詩歌作品。無論是狀物抒懷、寄情山水、吟誦鄉愁還是關注社會熱點以及風土民俗的詩歌都充滿了濃濃的詩情。而那些淺薄的、東拼西湊的、晦澀難懂的、沉迷文字游戲的“詩”,統統被“詩歌廣場”的編輯棄之。這也許是“詩歌廣場”受到讀者關注的原因吧。
筆者在閱讀“詩歌廣場”一欄的詩歌作品時,也注意到了一些生硬直白,缺少詩意和詩句太長的詩,特別是句子長的詩,不利于閱讀和傳播。然而存在的不足之處,絲毫影響不了“詩歌廣場”的存在。
除以上言及的,《大理文化》的封面設計及內文中的圖片使用,頗具匠心,恰到好處。筆者最傾情的是該刊獨具特色的“編輯手記”,之所以獨具特色,是因為眾多文學期刊未曾有過這種做法。“編輯手記”的設置,一是保障了刊物的整體質量,因為質量是一份期刊的生命線,包含了精心造稿,精心編輯、精心校對的全過程。二是編輯在讀稿、選稿中提高了判斷、取舍的能力。三是通過對一個欄目或一篇文章精準的評介,為讀者起到了閱讀的引領作用。四是每個欄目及其文章的責任編輯通過言簡意賅、行文精煉的文字表述,既練就了編輯的寫作能力,也實現了編輯素質的全面提高。
“大理旅游”“大理記憶”“大理藝苑”“大理講壇”等欄目的設置,還原了當年《大理文化》辦刊人的初衷,顯得各有千秋,所刊發的文章凸顯了魅力大理所應有的本色。
鑒于筆者看到的只是《大理文化》2017年的第2期、第6期及第8期,雖不能窺見該刊全貌,但那些感人的作品依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許就是《大理文化》的魅力所在。于是寫下這篇短文,愿與《大理文化》編輯同仁共勉,并盼得到指正。
【作者簡介】李光云,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云南省社科期刊審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