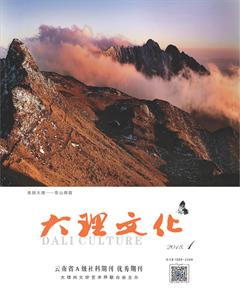鳥道雄關行記
王雪梅
去鳥道雄關采風的車駛入了彎彎曲曲的山路,路繼續向前,車繼續顛簸。坐在這車上,還真是有歷經驚濤駭浪的驚心動魄。也許,我該看看外面,分散一下顛簸的感覺。想到這,我把眼光看向窗外。哇!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那山,是從天而降的,一瀉而下的綠,猶如九天仙女飄然而下的綠長裙。愛美的仙女姐姐嫌綠色太單調,不能盡顯她的氣質與個性,便用巧手繡上一樹一樹的白杜鵑花,讓她的長裙更多些靈動與層次。風兒輕輕吹過,綠裙白花柔柔舞動,這正是仙女姐姐在向我們展示曼妙舞姿。看著看著,我便有了買條綠底白花的飄飄長裙的愿望,有了做回仙女姐姐的遐想。
這綠底白花的長裙還在我心底蕩漾,馬上又有新東西沖擊我的味蕾。車窗外,一路都是帶刺的小黃果,都在唱著歌兒招著手:“路旁的花兒正在開,樹上的果兒等人摘,等人摘。”這小小的黃果是我童年的最愛,我們當地人都叫它黃泡,也許是它像一個一個的泡泡而得名吧。
童年時,每到這個季節,總會與幾個小伙伴相約去摘。摘的時候總是爭著搶著,可吃的時候又總是慷慨解囊,毫無保留地分享著,品嘗著,說笑著。那酸酸甜甜的味,至今記憶猶新。那一串一串的笑語,至今縈繞腦際。我幾次躍躍欲試,想在車駛過黃泡樹的一剎那,順手摘幾小顆解解饞。坐在旁邊的同志發現了我的動機:“小王。注意安全,等下會有你吃的。”我扮個鬼臉,只得乖乖坐好。
車停了下來,我們到石甲村委會小憩。雖說是小憩,但收獲并沒有因為小憩而停止。隨著彝家阿妹端茶倒水走過,吸引你目光的定是那身絢麗的彝家盛裝耀眼得如同盛開的山茶花,熱情、奔放。我是愛美的,一直貪婪地盯著漂亮衣服不放。這時,村委會的同志征求女同胞的意見,要不要做回彝家姑娘,這可樂壞了我,迫不及待就要換上。
到了彝家姑娘的閨房,那一身彝裝竟讓我無從下手,它猶如天邊扯下一片一片的彩云,一塊做長裳,一塊做小褂,一塊是圍腰,一塊是裹背……就是一塊一塊的,好像都沒有裁剪,沒有縫制,更沒有釘紐扣……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穿!
彝家小姐姐一邊幫我穿衣服,一邊給我介紹這一片區服飾的特點:我們彝族服飾以銀飾和繡花為主。你看,我們已婚女子結發髻,發髻呈寶塔壯。發髻上戴“別子”(“別子”其實就是發卡,它分4串,每串有兩個燈籠繡球、兩個響鐘和兩尾小魚,均為銀制品)。發髻外包裹黑包頭(未婚女子不裹包頭,戴銀鼓帽),包頭上有銀串珠和亮球裝飾。上衣領和袖、襟,鑲上多層、鮮艷且樣式不相同的金銀絲瓣或自繡花紋。上衣外罩齊腰藍布短領褂,領口飾有由7個銀鼓釘拼成的5個葉子,彝語稱之為“披巴”。領褂四周用銀鼓釘鑲邊,共4排,每排36顆,一件領褂有200多顆。胸前佩戴銀質“三須”針筒,“菱角吊”和雞心型繡花荷包。腰間系圍腰。背背直徑一尺左右的圓裹背,上繡兩朵太陽花,一大一小,對稱排烈。裹背分內外兩層,中可載物。鞋是繡花鞋,船型或鳳頭型。鞋面繡40余朵小花,中夾40余片綠葉。
一套服飾,竟有這么多學問。它的美,不僅是外在美,更是有內涵的美。我不禁贊嘆起彝家先人的用心和智慧。
第一次穿上盛裝,我掩飾不住做彝家人的驕傲和美不過盛裝的嬌羞,甚至幻想著我就是待出嫁的姑娘,羞答答地送出我親手繡制的荷包。村委會的一位老藝人告訴我:“我們彝家人的圍腰與圓裹背都有著優美的傳說。”
“彝族人稱圍腰為‘給布,比漢族人的要大,一般長55公分,寬40公分。左右下鑲各自喜愛的花邊。從民族學角度講。給布表現彝族女性的羞恥意識。”紅山講起了故事:“傳說天地老祖來人間閑逛,看見一個貌美如花農婦在地里種小麥,老祖驚異人間有這等靈物,就想考考這農婦:喂,你一天鋤地鋤了多少鋤?農婦看一看老祖說:我一天鋤了幾千幾萬鋤,你一天走路走了多少步?老祖無話可答。第二天,老祖騎著高頭大馬來到農婦家,高聲對農婦說:我上馬還是下馬?農婦走到自家門檻上,對老祖說:我進門還是出門?老祖又輸了。老祖感覺世間女子太聰明了,應該讓她們收斂一點,就拿出一個圍腰送給農婦。農婦系上圍腰后,就沒男人聰明了。從此,彝族人便有了圍腰。”
老藝人講完圍腰的故事,又講起“圓裹背”的故事。圓裹背的故事比圍腰的故事要感人些:它講述的是一對青年男女相愛,遭到迫害后逃到山洞,蜘蛛吐絲織網封住洞口救下他們的事。這是一個不畏權勢、戰勝惡勢力的故事:是一個可歌可泣追尋真愛的故事;這更是一個“滴水之恩,泉涌相報”的感恩故事。紅山講得繪聲繪色,我聽得津津有味。這又豈止是一個故事,這些服飾在繁復的花紋中蘊含著豐富的故事和民族情感,像是彝族文化里的山茶花,在美麗中飽含著獨特的氣質。這是一個民族的氣魄和靈魂:一身服飾、一種精神、一種象征。
吃過中午飯,真正開始走古道。對我來說,古道就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就是一首古老的歌,隨著叮叮當當的馬鈴聲。從遠古回蕩至今。歌聲流過昨天、今天、明天,是那一路的艱辛,一路的期盼……
不是么,那石板坡的每一塊石板上,那些深深淺淺的印記是阿哥一步三回頭的“腳跡窩”。趕起馬幫,走出這山澗,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歸,才能再見到阿妹的身影聽見阿妹的山歌。多想說“阿妹阿妹等著我”,又不敢說:這一路,重重關山,漫漫風雨,猛獸出沒,匪徒搶殺,馬幫一去歸期不定,怕誤了阿妹青春和心意。一路的糾結一路的留戀,阿妹只得藏心里,藏夢里:只得為你唱響離別的歌:“阿哥走過石板坡,石板坡上風吹過。哥愛小妹口難說,只把阿妹記心窩。”
走在石板路上,聽著石板坡每塊石板下的水流過,那是阿妹想念阿哥流淚時的嗚咽。阿哥你不辭而別,但阿妹知道昨晚阿妹窗前你來過。深情的目光在月光下閃爍,你的身影在月光中婆娑。阿哥啊阿哥,你為何不叫阿妹等著哥?
阿哥啊阿哥,你從石板坡上走過,可知阿妹送你也到石板坡?“石板塊塊哥走過,淚水滴滴妹送哥。阿哥阿哥你回頭,回頭看看阿妹我。”
馬幫遠了,阿哥遠了,相思近了,想念近了,“趕馬調”“送郎調”唱起來了……
走過斜揚而上的石板坡,也就到了山頂。往左走,彌渡與巍山的交界處,立有一塊長1,45米,高40厘米,厚20厘米的石碑,上面自右至左刻著“鳥道雄關”四個大字。石碑旁邊,不知道是一小座石房子還是算一塊碑,上面還有淺浮雕神像,反正我是叫不出神像名字的。但這些神像,定是能祈求平安、豐收、興旺的!
據說,每年的仲秋時節,成千上萬的候鳥從高緯度地區向低緯度地區遷徙,飛往緬甸、印度、馬來半島等地過冬。于是有了“鳥道雄關”一景。“鳥道雄關”不僅是一條鳥道,也是一條馬幫之道。站在這石碑旁邊,腦際不僅浮現霧朦星稀的夜晚,當地彝民在這里燒起松明火誘惑各種鳥撲向火邊捕鳥的情景;眼前還會浮現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崎嶇山道,趕馬人不緊不慢走過,留下深深淺淺的馬蹄印;當然,耳邊仿佛還能聆聽到叮當叮當的馬鈴聲;還能感受那一段歷史的久遠與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