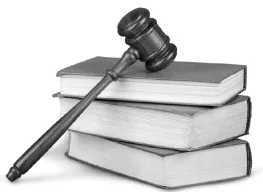司法體制改革背景下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
李瀟瀟
(300387 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 天津)
一、公序良俗原則概念的提出及正當性
公序良俗原則的最早立法見于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當事人不得以特別的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公序良俗原則的本意是當事人的法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目的是維護多數不特定人的利益,限制私權的濫用。時至今日,2017年3月15日頒布的《民法總則》中首次使用國際通用的公序良俗一詞代替社會公共經濟秩序等詞,體現了公序良俗原則限制私權濫用的主要功能,同時也是限制公共權力的體現,與國際通行立法相一致。
公序良俗原則產生和法律適用的正當性可以用法國法學家狄驥“社會連帶關系”理論來論證。社會連帶關系理論認為人們在社會中聯合,并且始終是聯合著的。人在社會生活中必然與他人與社會產生聯系,這種聯系就是社會連帶關系。社會連帶關系不僅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更是國家和法存在的基礎。法律規范作為社會規范的一種,其存在是為了維持這種社會連帶關系。
二、當下司法適用經驗與評析
提到公序良俗原則在我國的司法適用,就不得不提起“蔣倫芳訴張學英”案。本案經人民法院以遺囑違反《民法通則》第七條的“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為由宣布該遺囑無效,從而使張學英無法得到遺囑指定的財產份額。這一審判得到了廣大社會群眾的擁護,但在法學界卻出現了眾多不同的聲音。首先,從社會公共利益角度。遺囑生效所帶來的法律后果直接影響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妻子蔣倫芳。而很明確的一點,社會公共利益的指向應是全社會中多數不特定人的利益。因此,以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由判定遺囑無效是不符合法律邏輯的大前提的。其次,從法律位階上看,《繼承法》相對于《民法通則》又為特別法,在繼承法有明確規定的情形下,應以繼承法為先,除了當事人民事行為違反民法基本原則。結合本案:當事人的遺囑中若加以違反公序良俗的條件作為遺囑生效的要件時,如禁止對方再婚或遺贈以加強這種不正當的兩性關系為目的的遺囑,應屬違反社會公德,當屬無效。而本案中以同居行為將效力瑕疵延伸至本身合法的遺囑行為判定其無效,實屬公序良俗基本原則的援用不當。
三、司法體制改革背景下的審判現狀與完善
(一)公眾輿論與司法責任制
法官員額制與司法責任制的落實對于監督法官的審判工作,提高審判工作總體質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明確司法責任是否會使一部分法官在行政干涉削弱之余,反而會更受公眾輿論等外界因素影響審判思路和審判結果。有理由相信,法官員額制下,法官審判時會不由自主地希望追求一種社會渴望的正義,從而引起以公序良俗原則為代表的法律基本原則司法援用率的提高。而前述論證顯示,這一比率的提高對于個案正義的實現并不是一劑良藥。
(二)保持法官的審判獨立
言論自由和網絡環境的發展,造成了當下公眾輿論足以形成空前的影響力,進而對法官的獨立審判造成壓力。因此,員額制下保障法官的審判獨立應從司法責任追責標準化和法官職業道德的深化兩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健全統一的司法責任追責的標準,包括案件質量認定標準及有區別的責任承擔。制定一條法官看得見、摸得著的不可逾越的高壓線。沒有統一的標準,司法責任的落實就無從談起;沒有統一的標準,司法責任的公公正承擔就無從談起,反而會成為阻礙法官審判獨立的絆腳石。同時,法院系統應構筑起相對應的法官責任承擔體系。主觀上故意違法審判的責任與因能力不足過失導致的瑕疵案件的責任承擔方式應有所區別,也要綜合考慮法官個人判案的瑕疵案件出現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中對于審判責任承擔范圍、相關人員的違法違紀情形、審判責任的分工承擔和審判責任的承擔方式做出了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需要進一步細化規則以期完善司法責任制,最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第二,加深對法官職業道德的培養和深化。有了司法責任制的外在監督,個案正義的實現更需要內在提升法官的職業道德。作為一種職業規范,法官職業道德所體現的法官行為直接關系到案件程序的正當性和案件結果的公平正義;關系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更關系到我國的法治進程。正是由于法官掌握著審判權,公平正義的裁判可以起到定紛止爭、實現正義、維護法律尊嚴的作用,因此,法官的職業行為更應受其職業道德的約束。法官應嚴格依法判案,慎以原則和道德習慣入法。
四、結語
公序良俗和個案正義都是司法審判中所追求的價值理念,但在司法實踐中,二者經常不能兼顧。隨著公共權力的擴大和網絡環境下言論自由影響力的提高,在平衡兩種價值理念時,公眾會自主自發地拔高公序良俗的地位進而影響司法人員的價值取向。但以法官為代表的法律從業人員所追求的價值理念中不應是以社會效應最優化為最優選擇,而應是以合法的程序追求個案正義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