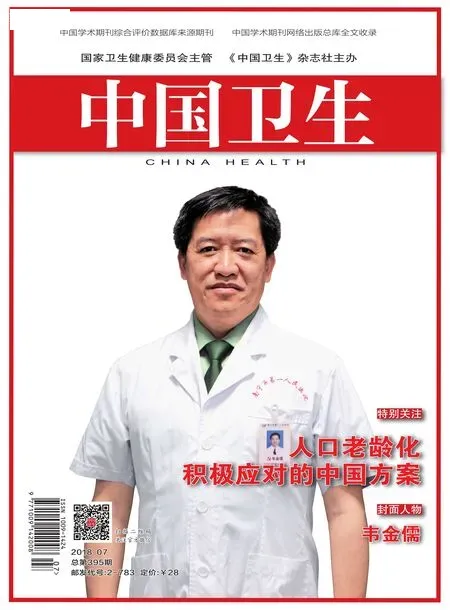邁入醫療衛生資源配置新階段
2018-09-12 03:42:44徐鳳輝
中國衛生
2018年7期
文/徐鳳輝
國家醫療保障局的組建,其實質是機構和資源的整合,將人社部、國家衛生計生委委、國家發改委、民政部以及商務部等涉及醫療資源管理的職能進行合并,通過政府機構改革,進而實現優化醫療資源配置。
統一醫保管理 完善國家治理體系
隨著經濟水平提高、人均壽命延長,以及醫療技術進步等因素推動,人們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需求呈現螺旋式增長。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體制,不僅面臨以最少資源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挑戰,也面臨如何公平有效配置資源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健康需求的挑戰。通過近10年探索,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醫療領域供給側改革經驗,并將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以緩解醫療衛生資源浪費和分配不公的問題。國家醫療保障局的組建,將分權于原國家衛生計生委、人社部、民政部、藥監局等原有國家機構掌控的醫療資源,通過集權化管理方式提高資源供給效率,為增加和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奠定基礎。
國家醫療保障局統一基本醫療保障行政管理職能,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重要探索的一個縮影。新組建的國家醫療保障局可能涉及3個層面挑戰:內部管理和組織架構問題,涉及籌資、支付、監管等內部管理機制建立,以及內部組織架構體系的設計。國家醫療保障局組建后,可能需要多層次、垂直化管理,如設立省級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市級醫療保障管理局等。國家醫療保障局如何統籌地方醫保機構設置,協助地方醫保機構整合醫療機構和醫療資源,是國家醫療保障局未來政策實施的組織基礎。……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合理用藥探索(2022年1期)2022-11-26 00:22:32
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1年4期)2022-01-14 02:35:48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11期)2018-11-23 09:47:26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6期)2018-06-22 10:25:54
資源再生(2017年3期)2017-06-01 12:20:59
華人時刊(2017年23期)2017-04-18 11:56:38
中國衛生(2016年5期)2016-11-12 13:25:28
小學閱讀指南·低年級版(2016年1期)2016-09-10 07:22:44
中國衛生(2015年5期)2015-11-08 12:09:48
中國衛生(2014年7期)2014-11-10 02: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