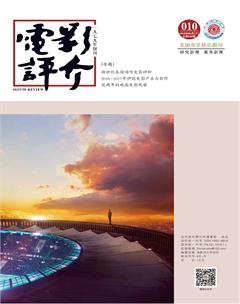印度新概念電影的跨越與重建
張玲
2017年,《摔跤吧,爸爸》在中國火熱上映,緊隨其后的《神秘巨星》《小蘿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線》也反響熱烈,口碑不俗。短短的時間內,印度電影似乎成為了國內電影市場的新寵,備受追捧。這些電影作品擺脫了印度電影“無歌舞不電影”的刻板印象,用新穎的題材和極具感染力的故事,宣告了印度電影“故事為王”時代的到來,而這些無一不是印度新概念電影思潮影響下的結果。以寶萊塢為代表的印度新概念電影思潮對印度電影實現對傳統形式的突破和超越,構建更為國際化的新式印度電影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 從歌舞片到故事片的變革
有人說歌舞片不一定是印度電影,但印度電影一定是歌舞片,一直以來,印度電影和歌舞似乎是密不可分的,優美的音樂,曼妙的舞姿構建了傳統印度電影獨具特色的民族風情。在傳統的印度電影中,歌舞的地位超然,它們并不依附于電影的故事情節,在電影中每每呈現為一個完整的歌舞場面,大量電影的歌舞甚至可以直接截取成為獨立的音樂作品進行售賣。有些電影中歌舞幾乎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存在,成為電影的主要賣點,從這個角度看,稱印度電影為歌舞片也并非言過其實。
這種情況當然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但印度文化中悠久的歌舞文化傳統為印度電影中歌舞的扎根和蔓延提供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從歌謠來看,印度有著悠久的吟唱歷史,大量的文化經典都是以吟唱的形式存在并進行傳播的。至今印度還保存著包括《摩柯婆羅多》《羅摩衍那》和《吠陀》等多部經典的數種吟唱方式。舞蹈的歷史同樣悠久,印度最早對于宇宙和世界的理解就是以“濕婆之舞”的形式來加以呈現的。正是這些悠久的歷史傳承讓印度人形成了鮮明的歌舞傳統。因此,在印度,歌舞幾乎伴隨了人們生活中所有的重要環節——從出生、結婚這樣的人生大事,到宗教政治的節日慶典,歌舞總是貫穿其中。而歌舞對戲劇的影響早在梵劇時代就開始了,就連梵劇的創始人“婆羅吒”,其名字本身就含有樂者和舞者的含義,印度戲劇和歌舞的關系之密切可見一斑。
這些文化基因決定了歌舞傳統在傳統印度電影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從最早的有聲電影《阿拉姆·阿拉》開始至今,印度電影在本土的發展都因為其中的歌舞元素獲益良多。但是,這種以印度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戲劇表現形式,在國際市場上則容易“水土不服”,因為其間豐富的歌舞展現常常伴隨著對敘事的割裂和擠壓。比如早期的印度電影《大篷車》,這個故事內容其實并不復雜:女主人公在不明真相下和殺父仇人結合,在真相大白后出逃、尋親,最后復仇。從情節上看這是一部典型的“希區柯克”式的電影,可是卻并沒有帶來“希區柯克”式的觀影體驗。因為貫穿電影的數段“輕歌曼舞”將追逃的緊張和沖突的激烈銷蝕殆盡。歌舞內容不僅使電影敘事變得拖沓,也過度強化了電影中的抒情效果,將觀眾的視線過多的分散到了更為次要的愛情元素中,破壞了電影的整體敘事效果。
這種情況在印度電影中比比皆是,有研究表明印度電影“在一般情況下,音樂舞蹈要占據全部影片的1/4到1/3之多”[1],這樣的比重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作品中都是絕無僅有的。而這樣的電影結構必然會擠占電影本身的敘事空間,打斷整個故事的敘事節奏,形成電影敘事的片段化和敘事的延宕。這種打亂電影敘事節奏,割裂電影敘事時空的方式,嚴重影響了海外觀眾對于印度電影的理解和接受,這對于印度電影在國際市場的發展來說顯然是不利的。這也是張藝謀導演在采訪中調侃印度電影“自娛自樂”的重要原因。
而電影作為一種敘事藝術,故事才是其內容的根本。從美國的電影大師格里菲斯對狄更斯敘事藝術的推崇,到俄國現實主義戲劇代表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對體驗的關注,無不體現了敘事在電影中的重要性。對此,部分印度電影人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因此早在2000年左右,寶萊塢的電影工作者率先舉起了“新概念電影”的大旗,提出打破傳統局限,回歸電影敘事的創作理念,對不利于電影敘事的傳統元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其中就包括了對傳統電影中歌舞的重新定位和演繹。
從近期在中國上映的幾部電影來看,這種變革可謂成效斐然。無論是《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還是《小蘿莉的猴神大叔》,都給觀眾呈現了一個頗為精彩的故事,不僅在形式上實現了對傳統的突破,在故事的鋪陳和展開上都表現出張弛有度的純熟和自如。這些作品徹底擺脫了印度電影“歌舞片”的既定印象,歌舞片段大量減少,故事性得到增強。比如在《摔跤吧,爸爸》中僅有一個婚禮中的歌舞場景,而《神秘巨星》雖然以音樂夢想為作品主線,但是作品除了展現女主角音樂天賦的歌曲演唱以外,傳統的抒情性歌舞片段一個都沒有,這無疑是對電影敘事空間的極大釋放。另一方面,敘事成為了電影的核心。在這些電影中,無論是歌舞還是音樂都和故事情節緊密結合,成為了電影敘事的輔助手段。比如《神秘巨星》中的女主人公演唱的幾首歌曲,從在家的自彈自唱,到后來錄音室的專業錄制和舞臺表演,這些音樂的內容都是水到渠成的情節演繹,都對故事的發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動。音樂在這里成為了構建電影故事的必要元素。
同時,這些作品的敘事手段也更為大膽老練。電影拋棄了傳統單一的敘事線索,轉而運用多維度敘事的方式來構建了一個更為立體的故事結構。
二、 題材的豐富和突破
愛情、戰爭和神話是印度傳統電影的三大主要題材。印度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豐富的傳統文化是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其中敘事性的神話史詩和宗教故事成為了印度電影題材的天然來源。這些經典不僅有著廣泛的受眾基礎,而且神話和宗教傳說中“因果報應”的故事構架,“真善美”的價值觀也讓篤信宗教的印度人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因此,從史詩巨著《摩柯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到宗教神話,成為了早期印度電影故事的起點。印度歷史上的第一部電影《哈里什昌德拉國王》就是一部來源于印度神話的作品。除此之外,《火燒楞伽城》《克里希那大神的誕生》等等都是取材于傳統神話或史詩的電影作品。
除了戰爭和神話,愛情也是印度電影中一個長盛不衰的題材,在印度電影中,愛情題材的喜劇電影不勝枚舉。甚至在很多其他題材的作品中,愛情往往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比如前文提到的《大篷車》,本是懸疑的題材,在女主出逃遇到大篷車隊后卻話鋒一轉,變成了富家女、司機和吉普賽女郎之間的三角戀情,最后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圓滿為結局。20世紀90年代改編的電影《暮色下的男人》則是側重刻畫了失明拳擊手和女主角之間的患難見真情的愛情故事,而對好萊塢原版《驚聲尖叫》中的懸念驚悚徹底忽視;哪怕到了2001年神話史詩題材的電影《阿育王》中,印度電影對愛情的熱情也依然不減,整部電影用了超過一半的內容來展現阿育王的英偉以及他和卡瓦奇公主之間凄美的愛情……凡此種種不可勝數。
美好的愛情、夢幻的烏托邦和偉大的英雄成為了印度傳統電影中所展現的核心,這種極度理想主義的故事構架像一場一場循環不息的夢境,雖然能讓觀眾獲得一時的滿足,但一輪一輪往復下來,單一的題材故事,總會讓人覺得乏味厭煩。更不用說在不斷推陳出新的國際電影市場,突破和創新才是關鍵。因此,瞄準國際市場的寶萊塢電影,也開始嘗試更具突破性的題材,比如2009年上映的《三傻大鬧寶萊塢》,通過嬉笑怒罵對僵化教育體制進行了尖銳的諷刺。《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則對當下印度社會中女性生存狀態進行關注,對女性在印度社會中遭遇的種種不公和壓迫進行了暴露和批判;《小蘿莉的猴神大叔》中“猴神大叔”送小蘿莉回家的故事,展現了人性、博愛、包容和理解等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和觀念。故事中凸顯出來的人性大愛,超越了國家的政治壁壘和宗教的信仰差異,回歸到人與人之間最本真的情感。簡單純粹感人至深。《起跑線》更是用戲謔的方式討論了印度社會中教育公平的問題。所有這些作品相較于傳統印度電影的題材內容,不僅是類型上的豐富,更是價值維度上的突破,實現了從傳統價值向現代普世價值的轉換。這里面雖然不乏商業利益推動下對西方主流價值觀的迎合,但是同時也使印度電影擺脫了傳統題材中虛幻的理想主義,實現了對現實問題的回歸和批判。
三、 人物的去臉譜化
美國學者羅伊曾經說:“印度電影承接了其兩千多年來的歷史傳統。電影人物并不代表具有復雜心理活動的實體,而僅是道德原型。”[2]事實上,道德化人物的二元模式是印度電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所遵循的原則,有英俊、熱情、豪爽的男主人公,就有或兇狠或風流的浪蕩子;有溫柔多情的漂亮淑女,也有妖艷狡黠的蕩婦;父親永遠是專橫的代表,母親則總是親和而包容……簡單的是非判斷將故事中的人物劃分為不同的兩個陣營。而這些人物就在這個二元結構中被固定下來形成套路,成為表演采用的程式化原則。當人物都成為了道德符號的時候,所有的形象都被簡化,就像京劇中的臉譜,忠奸善惡都直白成臉上的油彩。所以在印度的電影中我們總能找到“千人一面”的人物形象,簡單而刻板,缺乏其作為“人”的個體的內在特征,內心和思想、性格和喜好都被忽略掉了。這種人物往往單薄得像一張臉譜,無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摔跤吧,爸爸》中的人物刻畫卻讓人感到驚喜,這里沒有等待拯救的柔弱女主角,而是自立自強,不斷突破自我的摔跤冠軍。電影中的女主人公有叛逆、有反思、有成長,朋友的買賣婚姻讓她警醒;國家隊的虛榮和繁華也會讓她迷失;比賽的挫折和困難則讓她最終實現自我的回歸和成熟。正是這些曲折而復雜的內在刻畫,讓這個叫吉塔的女孩子深入人心。而故事中看似常規的家庭設置:專橫傳統的父親,慈愛親切的母親,卻給了人們超常規的體驗。我們發現這個專橫的父親并不引人反感,因為在他的專橫下面,還有一顆慈父的心:他會在深夜為辛苦訓練的女兒揉腳;他也認可女兒的價值,要把女兒培養成“偉大的女性”,而不是商品和男人的附庸。“嚴師”和“慈父”在這里融為一體,讓父親的形象看起來威嚴但又不失溫情。同樣生動的人物,我們在《起跑線》中也能看到。在這部電影中父親的“專橫”形象完全被推翻,電影中的拉吉是一個完全符合西方主流價值判斷的“新父親”:他尊重妻子,疼愛女兒,有擔當和責任感。會在妻子難過時柔聲安慰,也會在聚會上和女兒盡情玩鬧,在他身上剝離了傳統“父權”的威嚴,實現了生活本質的回歸。同時,電影還著重刻畫了拉吉內心的矛盾和沖突:既有他為了女兒的名校入學名額不擇手段,又有他面對良心譴責的羞愧和掙扎。多個層面的塑造讓拉吉這個人物具有了復雜性和生動性,從而更為真實立體。
四、 民族文化的堅守與融合
面對強勢的西方電影文化,全盤西化和固守傳統都不是印度電影可持續的發展選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發展才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單純的某一種模式或文化都不可能成為永恒的主導和絕對的真理。印度電影從之前的“自娛自樂”到現在的走出國門,先破后立的過程不可避免。但是,“破”并不意味著對傳統文化的完全拋棄,而是對舊的形式的打破。“立”也不是對好萊塢的照搬照抄,而應該是對民族文化和本國文化新的解讀和演繹。因此,寶萊塢電影雖然在題材、形式和思想上都發生了轉變,但是卻并沒有脫離對本國和本民族的現實關照,無論是對印度女性地位的探討,對教育制度的批判,還是對宗教問題的思考,所有種種都保持了和印度社會的密切關系。甚至是備受爭議的歌舞傳統,阿米爾汗也在《神秘巨星》中用彩蛋的形式對其致以敬意。
印度作為世界上的電影生產大國,其每年的電影產出量高達1500部,數量遠遠超出包括美國好萊塢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但是,程式化的故事和風格讓印度電影止步于國門。印度新概念電影通過對傳統電影的跨越和重建,讓印度電影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使其在跨文化傳播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1]彭驕雪,印度“馬沙拉”影片的藝術風格[J],當代電影,2005(4):92-95.
[2]Chute,David: Gods walk the earth, Film Comment,New York,Jan.1995,Vol.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