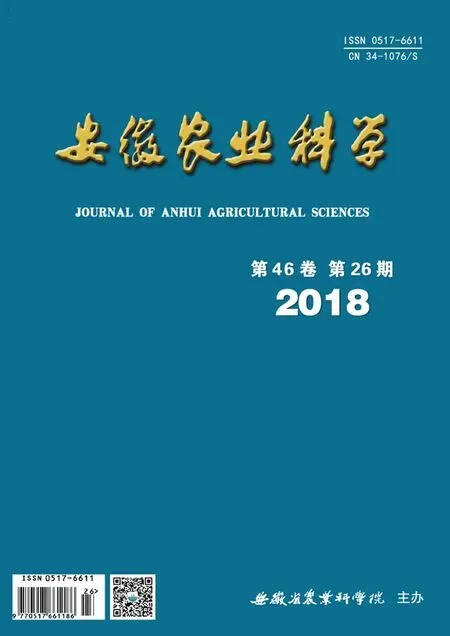植物氮素高效吸收研究進展
陳 坤
(廣西大學農學院,廣西南寧 530004)
氮素是作物生長發育必需的元素之一,是植物體內一些生長激素、核酸、磷脂和蛋白質的重要組成成分,對作物最終產量的貢獻高達40%~50%[1],對植物的生理代謝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氮素是植物生長發育過程中需要的諸多營養元素中影響作物的產量與植株生長的主要元素[2]。農業部2013年發布的《中國三大糧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研究報告》表明,我國三大糧食作物氮肥當季平均利用率僅為33%,雖然進入國際上公認的適宜范圍,但仍然處于較低水平。氮肥利用率的低下不僅浪費資源,而且很大程度上造成生態環境的污染。為此,總結近年來植物對氮素吸收的研究現狀與進展,旨在為相關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1 作物氮效率的研究
不同植物或同一種植物的不同品種間在氮素吸收和利用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3]。1939年Harvey首次報道不同氮效率基因型玉米之間氮素吸收、利用方面存在差異,提出“氮效率基因型差異”的概念,之后有許多學者針對作物的氮效率進行廣泛研究。作物的氮效率定義和名稱較多,并且差異很大,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參數[4]。Moll等[5]將氮效率(nitrogen use efficiency,NUE)定義為在土壤中,植物在單位有效氮中獲得的產量,并把氮效率劃分為氮素吸收效率(nitrogen uptake efficiency,NUpE)以及氮素利用效率(nitrog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NUtE):氮吸收效率=植株總吸氮量/總供氮量,氮利用效率=作物產量/植株總吸氮量。Hirose[6]認為氮效率為作物干物質與作物的氮吸收量之比,Baligar等[7]認為氮效率反映植物吸收轉運利用氮素的能力。先后有許多學者針對不同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相繼提出多種氮效率評價指標(表1)。這些指標均是研究者根據自身需求,結合自己研究方向,從特定的角度選擇指標來評價作物的氮效率,但均是在Moll等對氮效率的定義上進行發展延伸的。
影響作物氮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有研究表明[7],根系在土壤中的生長以及形態結構分布會受到不良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因此根系的吸收面積大幅度降低,從而影響作物對氮素的吸收。王朝暉等[14]研究表明,土壤的水分脅迫導致氮素吸收量降低40.16%~72.10%,產量減少36.11%~72.13%。Barkin等[15]研究表明,植物葉片蒸騰速率的大小與根系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受到空氣中持續升高的CO2濃度的抑制作用,影響根系吸收轉運氮素的能力,進而降低氮素效率。Fashola等[16]研究表明,氮肥的合理施用可以有效減少養分的損失,提高植物對氮素的吸收、利用效率,促進作物的生長發育,并可以有效地提高產量。
2 作物氮素高效吸收機制
迄今為止,有諸多研究表明,氮素的吸收和利用效率在不同基因型作物間均存在顯著差異。植物高效利用氮素主要有2種機制:一種是氮素的高效吸收,也就是植物在較低氮水平下吸收較多的氮素;另一種是氮素的高效利用,也就是用較少的氮素生產出較多的干物質[17]。該研究主要針對氮素吸收效率的研究現狀進行闡述。
2.1氮素高效吸收的生理機制根系是植物吸收水分和無機養分的主要器官,多種物質的同化、轉化和合成均在其中進行。根系對氮素的吸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根系的生理特征和形態特征的影響[18],因此,根系的生長發育狀況直接影響作物的氮素吸收能力。有研究表明[19],影響植物氮素吸收速率的關鍵因素主要有根系活力、根系的生長分布、根系形態和根系的吸收動力學等。
2.1.1根系形態特征。根系的形態構型在很大程度上與根系吸收水分、養分能力密切相關,根系在土壤中的空間分布、與土層的接觸面積,均對作物的養分吸收起至關重要的作用[20]。Garnett等[21]研究表明,在低氮條件下,植物根系形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植株吸收水分與養分的能力。黃高寶等[22]研究表明,玉米的根系干重、根系長度、根系表面積和根密度等形態指標的差異是造成不同基因型玉米間產量和氮效率間差異的主要原因。
2.1.2根系活力。作為反映根系生命活動的重要生理指標,根系活力泛指根系的吸收、合成、氧化和還原能力等[23]。較大的吸收面積和較強的根系活力有利于根系對水分和養分的吸收,對于提高作物的產量以及肥料利用率有重要意義[24]。王秀波等[25]研究表明,隨著氮素水平的增加,小麥的根系吸收面積、根系含水量和根系還原力均呈現增長趨勢。劉敏娜[26]指出,在不同氮水平和處理時期,氮高效基因型菠菜具有較強的根系活力。

表1 國內外氮效率主要評價指標
2.1.3根系吸收動力學。NH4+-N 和 NO3--N是植物在生長發育及器官建成和各種生理生化過程中的重要氮源[1]。NO3-在植物的發育過程中起到信號物質的作用。根據吸收系統對NO3-親和力的差異,可分為高親和轉運系統(HATS)和低親和轉運系統(LATS)[27],其中HATS又可以分為組成型高親和力轉運系統型(cHATS)和誘導型高親和力轉運系統(iHATS),LATS可分為組成型低親和力轉運系統(cLATS)和誘導型低親和力轉運系統(iLATS)[28]。根系的吸收動力學可以用來作為不同基因型對營養元素適應能力的指標[29],同時也可以揭示不同基因型作物對元素吸收差異的本質原因。最大吸收速率(Vmax)和米氏常數(Km)是根系吸收動力學中主要的參數,Vmax值越大,吸收的內在潛力越大;Km值越小,親和能力越強。
Cacco等[30]將根系吸收氮素的動力學參數分為4種情況:①高Vmax低Km,適應范圍較廣;②高Vmax高Km,適應高濃度養分條件;③低Vmax高Km,適應范圍很窄,在任何濃度條件下均處于劣勢;④低Vmax低Km,適應低濃度養分。熊淑萍等[31]研究表明,不同氮效率基因型小麥的Vmax值與Km值間有顯著差異,均表現為氮高效基因型小麥具有較高Vmax值和較低Km值。
2.2作物氮素高效吸收的分子機制NRT是硝酸鹽轉運蛋白基因,分為NRT1和NRT2 2個子家族。NRT1家族蛋白主要參與LATS,而HATS主要由NRT2家族蛋白參與進行[32]。兩者是高等植物硝態氮轉運蛋白的2個家族,目前為止,在擬南芥中發現NRT1家族中至少有50多個成員,NRT2家族中有7個成員。NRT2家族的成員是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焦點,這是因為在外界NO3-濃度較低時NRT2對NO3-吸收有積極的作用[33]。Desnos等[34]通過對擬南芥的研究證實在NO3-濃度較低時,側根的生長直接受到AtNRT2.1基因的調控,且與植物體內的碳氮比有關。張玉瑩[35]研究發現,氮高效基因型油菜根系BnNRT1.1基因相對表達量在任何氮水平下均顯著高于氮低效基因型,但BnNRT2.1基因表達量無顯著差異。孔敏等[36]通過對白菜的研究得出,在白菜根部,BcNRT2的表達量最高,為誘導型表達。Chopin等[37]研究表明,種子的萌發率可通過AtNRT2.7的超量表達來提高。
AMT是銨轉運蛋白基因,分為AMT1和AMT2 2個子家族。根據AMT動力學特征,NH4+的吸收可分為低親和非飽和吸收(LATS)和高親和飽和吸收(HATS)。HATS在NH4+濃度<1 mmol/L時占優勢,NH4+濃度>1 mmol/L時LATS占優勢[38]。Engineer等[39]通過對擬南芥研究表明,在低氮脅迫下擬南芥AtAMT1.1在根中表達,而氮充足時在葉片中表達。Hoque等[40]研究表明,在低氮條件下,OsAMT1的高效表達可顯著促進銨態氮的吸收。鄧若磊[41]研究發現,在一定范圍濃度內,隨著NH4+處理濃度的降低,OsAMT5表達水平均呈不斷下降趨勢,表明OsAMT5的表達受高銨離子濃度的誘導。
3 問題及展望
近年來,關于植物氮素的吸收、利用及其在植物體內的轉化過程在生理方面以及分子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并且取得一系列的成果。通過對作物品種間氮素吸收效率差異性研究,結合形態、生長特征等的生理特征,明確植物響應低氮脅迫形態學變化的生理生化機制。目前,雖然在一些植物中鑒定出許多NO3-和NH4+轉運蛋白,但氮素轉運蛋白家族成員眾多,對多數轉運蛋白還未進行完全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且植物種類眾多,對某些植株的轉運蛋白領域的探討幾乎為空白。對它們的基因篩選以及功能鑒定還有待進行更深程度的探討。加深植物氮素吸收利用的研究,使植物最大限度地對氮肥進行吸收利用,為增加作物產量、提高作物品質以及改善生態環境等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