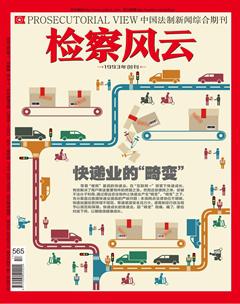李玲:開發二次人口紅利,突圍老齡化時代
史亞娟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但對于失能半失能老人,無論是入住養老機構,還是居家養老,抑或依托社區照護,都難以獲得方便有效的醫療服務。醫養結合如何體現中國特色?與之配套的醫療服務體系如何搭建?與此同時,鼓勵退休的銀發人員再就業在國際上早已成為一個有效手段,但在國內卻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如何在老齡化社會延長人口紅利的周期,完善體制機制進而把老年人的優勢發揮出來?
帶著以上問題,我們采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
醫養結合要回歸“中國特色”
《檢察風云》:在現行體制下如何推動“醫養結合”?
李玲:為讓老年人更好地安度晚年,我國提出了“醫養結合”,但我覺得它不能面向所有的老年群體,應該讓老年人中相對年輕的那些人去發揮他們的作用。當然“年輕”老年人也可能生病,需要照料,所以現在就用“醫養結合”的方法。
“醫”和“養”如何結合?還是要以“養”為主。國家現在的“醫養結合”是以家庭為基礎、以社區為支撐,醫養結合機構只是其中一個補充。要讓那些健康的、還能發揮作用的老年人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然后精準地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服務。
此外,“醫養結合”還是要回歸中國特色。我自己作為一個即將要到老年的人,覺得沒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了。老人其實都是一樣的,應以家庭養老為主。現在大部分老年人都是到了確實不能在家養老的時候,才會到養老機構去。在這之前,社區要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式養老既需要專業醫療的幫助,也需要家庭保健式的照料,以及社區的照料。同時養老更多是一種健康的養生,包括為老年人提供文化、鍛煉、娛樂、社交等一系列豐富的晚年生活。由此看,讓老年人老有所養,才是最好的養老。如果再引入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則可以支撐起未來一種新型的養老模式。比如你可以在家里安裝一些監控,用一種隨時能與老人溝通的設備和儀器,讓老人實現自我照顧。
《檢察風云》:人老了之后最大的需求莫過于醫療。要踐行中國式養老,國內是否有與之配套的醫療衛生體制?
李玲:與國外相比,中國現在在傳染病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近期的疫苗事件,折射的是國人在更高水平上對健康生活的需求。我們在傳染病的控制上,死亡率是非常低的,其中疫苗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我們在非傳染病上,如高血壓、糖尿病、癌癥等慢性病上的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我一直有個重要觀點:中國最大優勢在于醫療衛生。中國曾創立好的體系,而且這套體系的根基還在。現在中醫的方法得到世界越來越多的認可,中醫背后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全面、系統、綜合。由此我們更應該大力傳播養生文化與健康生活方式。
《檢察風云》:中國式的養老,如何能夠彰顯我們的傳統文化?
李玲:中國是一個講孝道的國家。十九大報告里面提出,積極應對老齡化,要建立養老、敬老、孝老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比如在未來,你和父母同住一起,你支撐父母的養老,可以免稅等,這樣一些政策制度,就是我們孝道文化的體現。
我期待的中國未來的養老模式,應該是要讓每個老年人都能夠老有所為,都能夠健康長壽,都能夠繼續為社會、為家庭做貢獻。而且中國文化講究修身養性、無疾而終,用現在通俗的語言,就是要健康地活著,沒有痛苦地死亡。
開發老年人口的二次紅利
《檢察風云》: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最顯著的一個特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老齡化,只是中國的問題更加嚴重。那么老年人到底是成本還是收益呢?
李玲:或許很多人會認為老年人是成本。人老了,不工作了,需要拿退休金,就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退休金的支出,一個是醫療的支出。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老年人確實是一個負擔。
但是我想,是不是應該重新定義一下“老年”?比如60歲、65歲都稱為老年人,那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定義。美國的養老金制度是1935年在大蕭條時期由羅斯福總統制定的,那時候人的平均壽命只有60歲。但是今天呢?今天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6.7歲。美國也在77歲、78歲。如果還按原來的年齡領養老金,就不太恰當了。現在美國也在延遲獲取養老金的時間,從65歲延遲到67歲,不過跟當年沒有太大的區別。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也在重新定義老年人,將60歲-74歲定為年輕的老年人,75歲-89歲定為老年人,90歲以上定為長壽老人。我就屬于年輕的老年人這個層次,我已經快退休了,我的同學們大多已經退休了。一般情況下,女性工作到55周歲就能退休了。我在研究老齡問題時,常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力資本浪費!作為女性,我自己的感受是,50歲—60歲是女性最佳工作年齡段,是時間、精力最充沛的時候。遺憾的是,我們很多同齡人大多已經退休在家了。
《檢察風云》:那么怎么才能把老年人變成收益呢?也就是老齡化不能只盯著成本,如何把老年人的優勢利用起來呢?
李玲:改革開放40年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就是因為我們充分利用了人口紅利。如今,這批人正在漸漸老去。但我們能不能利用他們的二次人口紅利呢?45歲-59歲的人、60歲-74歲的人,其實完全是有工作能力的。
我的同齡人以及我父母那一輩,本來工作好好的,一退休就開始無所事事。因為沒有工作的壓力了,在過去那種大家庭還可以抱抱孫子、忙忙家務,但現在很多都是獨生子女家庭,兒女們現在還沒有生孩子,甚至還沒有結婚。有些人退了休以后沒事干,就開始跑醫院,把看病當成了職業。
實際上,我們不應該把老年人變為一種成本,而是要用創造性的方法、更加彈性的方式,讓他們繼續發揮作用。開發人口的二次紅利,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新動力。
老年人幫年輕人避開創業的“坑”
《檢察風云》:怎么用好老年人,其實國家已經開始行動——最近教育部、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銀齡講學計劃實施方案”,如何看待這一政策舉措?
李玲:鼓勵老年人再就業、再創業這非常好!現在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對很多職業來說,老師要資格老的,醫生要資格老的,年輕醫生你還不愿意讓他看呢,因為他沒有經驗。接下來怎么把這些人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我很期待下一步不僅有銀齡的老師、銀齡的醫生、銀齡的科學家、銀齡的工程師,還要有銀齡的社工和志愿者。
遼寧省已經說要支持老年人自主創業了。我覺得太對了。年輕人創業的風險太大了,為什么?因為如果一個大學生剛畢業、甚至沒有畢業就去創業,沒有社會經驗,成功的機率很低。我認為,即便成功了也只是一種偶然,因為他們對社會根本不了解。而退休的或者即將退休的人,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也有社會資源,他們去創業,可以領著年輕人一起干,幫年輕人避開那些陷阱、那些風險。
我最近就在想:將來退休后就不再研究醫改了,也不再研究經濟學了,人一輩子都搞一件事兒,好像還沒有達到“全面發展”。看了《我不是藥神》后,我想以后也去寫寫電影劇本,醫改是多么好玩的事兒。而社會就是要鼓勵老年人退休后去做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讓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同時又能為社會創造價值。
《檢察風云》:我們怎么才能創造一種機制,不讓老年人與年輕人在就業上形成矛盾?
李玲:老年人不退,哪來的工作崗位?大家可以一起想想辦法。比如,國內的干部有一個“退二線”的說法,處級干部50歲退二線,副廳、局級干部55歲退二線,但他們其實并沒有退休,只是從管理崗位上退下來了。
同樣的方法,能不能用在企業老職工身上?這既不叫退休,也不同于現在的“返聘”,就是從一線退下來了,但還是可以繼續工作。只是他必須把原來的位置、原來的編制騰出來,這樣年輕人才可以進來。但老職工依然是可以繼續發揮自己的價值的,在關鍵時刻輔導好年輕人,發揮“志愿者”的作用。這些其實都是組織內部的機制設計問題。
編輯:鄭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