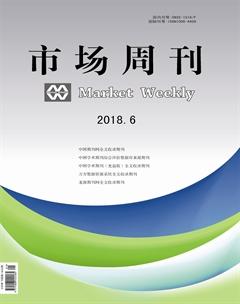基于城市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的脆弱性測度
摘 要:通貨膨脹作為一種風險沖擊,能夠顯著增強貧困人口的脆弱性水平。基于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CPIp)進行脆弱性測度,能夠準確體現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沖擊。依據2010—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微觀數據測度出,CPIp高于CPI 近4個百分點;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實際影響后,樣本中20.5%的家庭為脆弱性家庭。因此扶貧政策應多關注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以進行脆弱性人口的精準識別。
關鍵詞:通貨膨脹;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貧困脆弱性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8)06-0084-03
一、 引言
貧困問題由來已久,傳統觀點認為貧困狀態是長期靜態的。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研究發現貧困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即具有動態性。Levy(1977)的研究證明了基于貧困時間度量進行貧困研究具有重要意義。Peter C.Rydell(1974)基于美國紐約1967—1973年的數據證實,雖然以某一時點觀察得出貧困者具有福利依賴的特征。但是以時間維度進行測量,發現大部分的家庭并不是始終貧困的。Duncan(1985)利用1967—1975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樣本數據中將近1/3的人在貧困1年后下一年度實現脫貧。針對中國貧困研究,研究者利用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說分解農村總體貧困,發現將近一半的貧困者只是暫時性處于貧困的狀態。羅楚亮(2010)分析得出農村兩年內持續貧困家庭比率不高。貧困具有動態性,當前非貧困者由于風險沖擊而陷入貧困,因此貧困的分析應該考慮風險沖擊因素,脆弱性的概念由此引入。
誘發脆弱性風險的因素是多維度的,既包括社會環境因素,也包括經濟、政治等因素。就城市居民而言,最常見的風險有疾病、失業、通貨膨脹、滯脹等突發事故。通貨膨脹作為當前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表現,對貧困群體的沖擊值得關注。自2007年以來,我國經歷了新一輪通貨膨脹。此次通貨膨脹的顯著特征在于其構成和推動主要來自食品類價格的急劇上漲。2012年到2016年間,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平均為102.2,食品類CPI平均為104.9CPI均以上一年度為100作基準。,食品類價格上漲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城市貧困人口恩格爾系數明顯高于其他社會群體。如2012年按收入五等劃分,城市貧困家庭用于食品類的支出占其生活總支出的比重為51.8%,中等以及最高收入家庭該比重分別為46.8%與 39.8%。另外,相對于多數農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費完全置身于市場中,其對于食品價格上漲的敏感程度高。因此,代表社會平均通貨膨脹水平的CPI難以準確測度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沖擊。要準確測度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需要重新編制針對貧困人口的消費價格指數,為了區別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我們稱之為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CPIP)。
已有關于脆弱性的測度,并沒有直觀體現通貨膨脹風險沖擊的影響。而依據CPIP進行城市貧困脆弱性的測度,能夠準確體現通貨膨脹對城市貧困人口的實際沖擊。文章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家庭微觀數據,進行CPIP的構建,隨后依據CPIP調整貧困標準、進行貧困脆弱性的測度,通過與CPI調整的貧困標準所測度的脆弱性進行對比分析,以著重體現通貨膨脹沖擊下,貧困脆弱性的動態變化。
二、 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的構建
總結分析已有針對CPIP的計算方法可以被歸為兩種。一種方法是在現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編制基礎上,通過調整食品與非食品的權重來測度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一般選取食品支出的權重為60%,這是由于國際糧農組織規定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超過60%即為絕對貧困。另一種方法是根據貧困家庭自身消費支出構成作為權重來計算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相較而言,方法一的優點是操作簡單,而且方便與現有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銜接與對比;缺點是由于城市貧困家庭自身消費結構內部之間差異較大,所選取的權重是否就能夠客觀精確地反映出其消費結構特點有待商榷。方案二的優點是可以準確反映貧困人口的消費結構特點,缺點在于準確記錄家庭微觀消費數據的執行操作存在困難。
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CFPS調查推行單位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該調查通過系列追蹤收集包括個人層面、家庭層面以及社會層面微觀數據,以反映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動態變化。2008、2009年在北京、上海、廣東三地進行了初訪和追訪,2010年就全國層面正式開展訪問,2011年對2010年調查的家庭層面進行追訪,2012年進行全面追訪。文實證分析部分所利用的數據基本來源于家庭層面問卷,因此可以整理獲得2010—2012年3年期的追蹤樣本數據。微觀數據,采用方案二測度CPIP指數。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Xi指城市貧困人口付諸各類消費品的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比例。Pi指第i類消費品的價格指數。國家統計局將居民生活消費(服務)分為八大類: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與其他,所以i的取值范圍為1—8。本文按照人均家庭純收入十等分組劃分貧困家庭為了反映出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沖擊的嚴重程度,此處測度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時選用收入十等分組的方法。:收入排序位居最低10%位的家庭即為貧困家庭。CPIP測度結果見表1。
通過表1可以得出2010—2012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均以上一年度等于100進行分析,2010年前者數值為103.2,后者數值為106.4,二者相差3.2個百分點;2011年前者數值為105.3,后者數值為110.1,二者相差4.8個百分點;2012年前者數值為102.7,后者數值為106.3,相差3.6個百分點。平均而言,2010—2012代表貧困人口通貨膨脹水平的CPIP高于代表社會平均水平的CPI近4個百分點,這說明一方面貧困人口實際承受的通貨膨脹水平高于統計局公布的社會平均通貨膨脹水平;另一方面,依此調整貧困標準更能準確測度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沖擊。
三、 基于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的脆弱性測度
(一)城市貧困標準的調整
建構CPIP目的在于準確反映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因此依據CPIP調整貧困標準,并進行脆弱性的測度可以直觀反映出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后,城市貧困脆弱性的變化。即將通貨膨脹作為一個風險沖擊因素分析其對城市貧困脆弱性的影響。依據CPIP調整的國際貧困標準能更加準確反映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基于此進行貧困度量更有利于準確識別貧困人口。為此,此處利用上節測算出的CPIP調整每人1天2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調整結果見表2。
結果顯示,2010年依據CPI調整的1天2美元國際貧困標準為3165.6元/人·年,而依據統計年鑒公布的CPIP得出調整的該標準為3263.5元/人·年,二者相差97.9元/人·年,該數值約為2010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的5%;2011年前者標準為3230.1元/人·年,后者標準為3377.3元/人·年,相差147.2元/人·年,占2011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的7.3%;2012年前者標準為3150.3元,后者調整標準為3260.8元/人·年,二者相差110.5元/人·年,約占2012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的7%12010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963.3元,2011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012.6元,2012年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為 1592.9 元。。平均而言依據CPIP調整的國際貧困標準比用統計年鑒公布的CPI調整的貧困標準高約119元/人·年,該數值約占樣本中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的6%。
(二)貧困脆弱性測度
縱觀已有研究,不同學者對脆弱性有不同的定義認識。Glewwe and Hall(1998)定義的脆弱性是宏觀政策沖擊而造成的損失,此處的宏觀政策既包括宏觀政治政策也包括經濟政策。Pritchett et.al.(2000)和 Mansuri, Healy(2001)將脆弱性定義為一個家庭在未來幾年期限內至少有一年陷入貧困的可能性。Chaudhuri, Shubham(2002)將脆弱性的風險期限更加具體化,提出脆弱性是指家庭在下一年陷入貧困的可能性。Kuhl, Jesper(2003)將脆弱性定義為家庭因重大沖突而引發的收入或者消費水平下降到貧困標準以下的概率。韓崢(2004)對脆弱性的定義為風險與應對風險能力相對抗的結果。貧困動態學將脆弱性與暫時貧困相結合,將脆弱性個人或家庭等同于暫時處于貧困狀態的個人或家庭。世界銀行在2009年發布的《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中將暫時貧困與絕對貧困的時間分界點設為3年,并定義3年中至少有1年貧困的家庭即為脆弱性家庭。本文依據貧困動態學的概念將脆弱性家庭定義為:3年中至少有1年人均家庭純收入低于貧困標準的家庭。
依據樣本家庭的人均家庭純收入與調整前后的1天2美元國際貧困標準可以測度出2010—2012年調整貧困標準前后3年持續貧困、3年中有2年貧困、3年中只有1年貧困的發生率(其中,3年內連續收入水平低于貧困標準定義為持久貧困,3年內只有1年或者2年收入水平低于貧困標準定義為暫時貧困),依此得出3年中至少有1年收入水平低于貧困標準的比率,詳見表3。
通過表3可知,依據3年中至少有1年收入水平低于貧困標準的家庭即是脆弱家庭的概念定義,考慮物價上漲對貧困家庭實際沖擊之前,樣本中有18.68%的家庭為脆弱性家庭,考慮該影響后該比例增加為20.5%,上升1.82個百分點。這說明,在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下,20.5%的家庭是脆弱性家庭,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脆弱性測度將遺漏近2%的樣本家庭。
將全部家庭按照東、中、西三個地區進行劃分來考察地區之間不同。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家庭實際沖擊后,無論是暫時性還是持久性貧困,西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最高,相應的脆弱性也高于東部地區與中部地區。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后,西部地區超過五分之一的樣本家庭是脆弱的。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文章通過構建CPIP準確反映城市貧困人口實際承受的通貨膨脹水平,并依據CPIP動態調整貧困標準,以此準確測度考慮通貨膨脹的實際影響下城市貧困脆弱性的變化。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 貧困人口實際承受的通貨膨脹水平高于社會平均水平
當前通貨膨脹的主要特征在于食品價格上漲速度高于其他類消費品上漲速度。而城市居民食品消費完全依賴于市場交易,再加上城市貧困人口恩格爾系數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這多種因素的疊加使得城市貧困人口實際承受的通貨膨脹水平理論上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因此,依據貧困人口消費特點構建CPIP以反映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具有現實意義。本文依據2010—2012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家庭微觀數據,經過測度得出CPIP比CPI高將近4個百分點的結論,這證明了貧困人口承受的實際通貨膨脹程度嚴重于社會平均程度。
2. 依據CPIP調整的貧困標準高于用CPI調整的該標準
制定CPIP的目的之一是依此進行貧困標準的調整來實現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理論上,依據代表貧困人口實際通貨膨脹水平的CPIP調整的貧困標準高于依據代表社會平均通貨膨脹水平的CPI調整的貧困標準。本文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微觀數據測度得出二者的差別為119元/人·年,該數值占貧困家庭人均純收入的6%。
3. 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實際影響后,樣本中20.5%的家庭為脆弱性家庭
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微觀數據進行暫時貧困與持久貧困的測度,得出以下結論:家庭樣本中將近2%的家庭3年持續貧困;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樣本中0.26%的家庭將被遺漏于持久貧困的測度、1.6%的家庭被遺漏于暫時貧困的測度、2%的家庭被遺漏于脆弱性的測度;考慮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實際影響,樣本中20.5%的家庭為脆弱性家庭。
(二)政策建議
1. 依據CPIP制定有針對性的物價補貼措施
基于文章的研究與證明,通貨膨脹對貧困人口的實際影響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因此依據CPIP進行通貨膨脹背景下有針對性物價補貼措施至關重要。實踐中,早在2004年浙江省就出臺政策編制CPIP并依此進行有針對性的物價上漲補貼措施。2004年浙江省正式出臺《關于對困難群眾實行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漲動態補貼的意見》。根據《意見》,依據低收入群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基本生活物價補貼措施。《意見》規定自2005年起每月編制一次,每季度上報一次,每年向社會公布低收入群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原則上,低收入群體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在3%—5%(含)之間的,給予城鄉低保對象不低于半個月當地全額最低生活保障金標準的物價補貼;漲幅在5%—10%(含)之間的,給予城鄉低保對象不低于一個月當地全額最低生活保障金標準的物價補貼;漲幅在10%以上的,另行研究確定補貼標準。隨后江蘇省、上海市等均推行編制低收入群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工作,以對貧困群體進行物價補貼、增強困難家庭抵御通貨膨脹沖擊的能力。國家應該積極推進全國范圍內依據CPIP制定通貨膨脹背景下有針對性的物價補貼措施。
2. 依據CPIP動態調整貧困標準以精準識別貧困人口
基于文章上述“城市貧困標準的調整”內容的分析可以得出:依據CPIP調整的貧困標準高于依據CPI調整的貧困標準。因此,理論上,依據CPIP進行貧困標準的動態調整更有利于精準識別貧困人口。貧困具有動態性,暫時貧困家庭在經受通貨膨脹沖擊后極易轉變為持久貧困。一般而言,暫時貧困與持久貧困的時間界限為3年。在通貨膨脹風險沖擊的背景下,應該每3年依據貧困人口消費價格指數動態調整貧困標準,以實現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
3. 扶持政策應多關注城市貧困人口的脆弱性
阿瑪蒂亞·森在其著作《貧困與饑荒》中深刻揭示出貧困與易受風險沖擊的特點之間存在緊密關聯性。貧困實際上反映出個人或者家庭不良的能力狀況,也說明在面對沖擊時的易受挫的特點,這反映出脆弱性的本質。關于貧困的分析研究,引入脆弱性是一種前瞻性的視角。已有關于家庭所承受的負向外部沖擊而造成的影響的估計顯示,脆弱性的家庭易受風險的沖擊,而且這種影響有代際相傳的特征。因此,基于脆弱性視角的政策干預與政策實施加強至關重要。貧困的救助政策也不僅僅局限于使其脫離貧困線,還應該關注貧困家庭的脆弱性,避免其再次陷入貧困以及陷入深度貧困。
參考文獻:
[1]Levy, Frank. How Big is the American Underclass?[M]. Washington D. C Urban Institute,1977:135.
[2]Peter C. Rydell and et al. Welfare caseload dynamice in New York City[J].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1974,vol 11:110-127.
[3]Duncan, Greg J. Corcoran, Mary; Gurin, Gerald; Gurin, Patricia. Myth and Reality: The Causes and Persistence of poverty[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Management,1985,vol 4:516-536.
[4]Jalan, J. and M. Ravallion. Transient Pover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8,vol 26:338-357.
[5]羅楚亮.農村貧困的動態變化[J].經濟研究,2010(5):123-138.
[6]Glewwe. P and G. Hall. Are some Groups More Vulnerabl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than others?Hypothesis Tes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eru[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56(1):181-206.
[7]Pritchett. L·. A·Suryahadi. and S·Sumarto.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A Proposed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Indonesi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2437·2000.
[8]Mansuri. G·. and A·Healy. “Vulnerability Prediction in Rural Pakistan”[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meo. 2001.
[9]Chaudhuri. S. J·Jalan. and A·Suryahadi.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No·2002(1):02-52.
[10]Kuhl, Jesper. Househould Vulnerability-analyzing fluctuations in consumption using a simulation approach[J]. Institute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2003.
[11]韓崢.脆弱性與農村貧困.農業經濟問題[J].2004(10):8-14.
[12]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家庭追蹤調查[DB/OL].2012.http://dx.doi.org/10.18170/DVN/45LCSO.
[13]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對困難群眾實行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漲動態補貼的意見[J].浙江政報,2005(2).
作者簡介:
杜啟霞,女,山東莒縣人,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經濟管理學院助教,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貧困與社會救助、醫療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