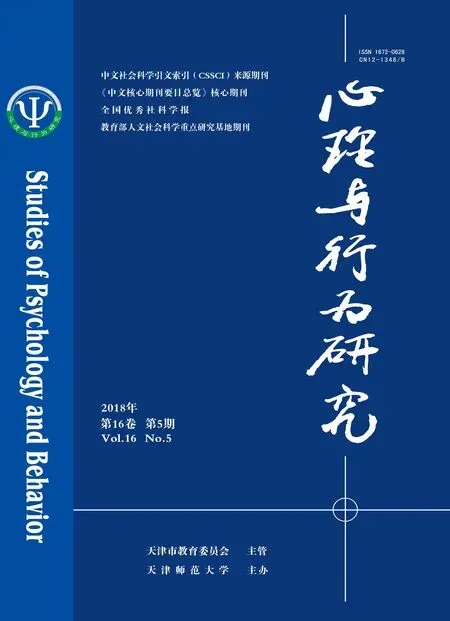情緒對信任的影響:來自元分析的證據 *
袁 博 孫向超 游 冉 劉福會 李偉強
(寧波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寧波 315211)
1 引言
信任是指建立在對他人的意向或行為的積極預期基礎上,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風險)的一種意愿(Rousseau,Sitkin,Burt,& Camerer, 1998)。信任對于個體與群體適應以及有效地進行政府、組織與經濟系統管理都起著重要作用(Bazerman,1994;Donaldson, 2001),其產生與運作機制一直是心理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在以往研究中,常常將信任看作是一種不確定情境下的風險決策行為,決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決策風險,獲得最大收益。因此,從理性認知的角度來看,個體是否信任他人主要決定于對托付他人的風險與所獲收益的權衡(Kramer, 1999)。
然而,信任行為并非完全理性的認知加工過程的產物,情緒也是影響信任的重要因素(嚴瑜,吳霞, 2016)。情緒是一種復雜的心理活動,包括效價、指向性、確定度、投入度以及結果評價等多個維度(Smith & Ellsworth, 1985)。其中,情緒的效價(正性、負性)是研究者們關注的一個重要維度。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效價的情緒會影響個體的道德判斷、風險感知以及決策行為。例如,負性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個體對他人的道德判斷的嚴苛程度;積極情緒會提高個體對風險情境中合作對象的正向感知,從而促使他們做出更積極的決策行為(Bless & Fiedler, 2006;Bodenhausen, Mussweiler, Gabriel, & Moreno, 2001;Clore, Schwarz, & Conway, 1994)。
情緒往往被認為是一種非理性的“沖動性產物”,然而作為心理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情緒與個體的理性認知加工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關于情緒如何影響個體的決策行為(包括信任),研究者們主要持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情緒信息會直接附加于認知進而影響個體決策行為。如連接語義網絡模型(Bower, 1981)認為,個體在對當前信息進行編碼和提取時,會對與當前情緒信息一致的部分表現的更敏感,即“心境一致性”效應(Winkielman, Knutson, Paulus, & Trujillo,2007)。積極的情緒使個體傾向于對他人與社會事件做出更為積極的判斷,增加對他人的信任;而消極的情緒體驗則會產生相反的作用。有研究發現,高興、感恩等積極情緒可以促進合作行為與利他行為的產生,提高對親密他人的一致感,增加對他人的信任(Forgas, 1998; 韓香香, 2013);而憤怒、悲傷等消極情緒則會降低人際信任水平(Dunn & Schweitzer, 2005)。
雖然有很多研究支持“心境一致性”假說,但也存在另一種觀點認為,情緒對決策行為的影響是復雜的,個體的認知加工過程會調節情緒對決策行為的影響。如情感滲透模型(Forgas, 1995)認為,情緒對決策行為的影響是復雜而非直接的,心境一致性效應的出現需要一定的條件。面對不同的目標線索信息,個體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情感滲透策略。近年來有關情緒與社會判斷關系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如Dunn和Schweitzer(2005)的研究表明,當個體面對熟悉的受信者時,相對于中性情緒,積極情緒對信任起到了促進作用;而對于陌生的受信者,情緒狀態對信任的影響并不顯著,即信任行為會受到信任者的情緒狀態以及受信者特征的共同影響。由此可見,信任目標線索(如受信者的熟悉度)可能會調節情緒對信任等社會判斷的影響。
在考察情緒對信任的影響時,情緒的誘發方式是較為重要的一個因素。以往的研究中,對于情緒的誘發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兩種:(1)材料啟動。包括圖像類材料誘發(如視頻、圖片)以及文字材料誘發(如詞語、情境故事閱讀),具體包括如情緒圖片啟動法(Lang & Bradley, 2000)、Velten情緒啟動法(情緒語句啟動法)(Velten, 1968)等。(2)直接書寫任務(directed-writing task)。要求被試認真思考并寫下一定數量與目標情緒相關的事物或曾經經歷的情境,以此誘發被試的情緒狀態。以往研究發現,被試在不同的誘發方式下產生的情緒效價水平并不一致。如袁婉秋(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圖像材料與詞語材料對正性情緒與中性情緒的喚醒效果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實驗過程中情緒的不同誘發方式可能作為影響情緒與信任關系研究結果一致性的調節因素之一。
此外,信任的測量方法的不同也可能會調節情緒對信任的影響。基于信任的定義,對于信任的測量主要包含兩種:問卷法與行為游戲法。問卷法用于測量個體的信任傾向與信任信念,是針對個體對他人或特定對象是否值得信任的一種心理期待的評估(何振芬, 2014)。行為游戲法主要以被試在游戲中的合作行為為信任的指標。目前Berg,Dickhaut和McCabe(1995)設計的信任游戲被廣泛應用于信任研究中,游戲以個體在游戲中對伙伴分配或投資的錢數作為信任的指標。關于上述兩種測量方法之間測量的信任結果一致性仍存在一定爭議。例如,有研究對比了信任博弈游戲與問卷法測量的信任一致性,結果表明兩種方法測量出的信任水平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Glaeser,Laibson, Scheinkman, & Soutter, 2000)。而 Capra,Lanier和Meer (2008)的研究發現,采用GGS綜合社會調查測量出的信任得分對于信任博弈游戲中的投資行為具有較好的正向預測作用。
綜上所述,不同效價的情緒是否會對個體的信任產生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會受到情緒誘發方式、信任測量方法以及信任目標信息(如信任對象的熟悉度)等因素的調節,尚待進一步探討。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對情緒與信任的關系進行探討,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信任對象的熟悉度、情緒的誘發方式以及信任測量方法等因素的調節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搜集
本研究全面搜索了相關研究的中文與英文文獻。中文文獻使用了CNKI數據庫、萬方數據庫、中國科技期刊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以及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以“情緒”、“情緒狀態”、“情緒效價”分別與“信任”、“信任行為”、“信任傾向”、“合作行為”、“合作傾向”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此外,也在Google學術中對相應關鍵詞進行了搜索。英文文獻使用了PsycINFO,Springer,Elsevier以及ProQuest博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以mood,emotion,feeling 分別與 trust,trust behavior,trust intention,trustworthiness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同時也在Google學術中對相應關鍵詞進行了搜索。對于搜索到的,但沒有報告結果內容的文獻記錄,盡量通過可以尋找到的聯絡方式給作者發送電子郵件以獲取全文或研究結果部分。
2.2 文獻納入的標準
對于搜索到的相關研究,按照以下標準決定是否將其納入元分析:(1)必須是報告了數字結果的實證研究,排除綜述性、純理論性的研究。(2)研究中探討的因變量必須是信任領域的,非信任領域的實證研究將被排除。(3)研究中被試的效價情緒必須是在一定條件下誘發產生的,非誘發情緒的相關研究將被排除。(4)如果僅僅只報告某一種效價情緒(積極/消極)對信任的影響,沒有進一步與基線控制組(前后測不屬于控制組)進行比較的研究將被排除。文獻檢索、納入及排除流程如圖1所示。最終,我們得到符合元分析要求的文獻21篇,中文文獻13篇,公開發表的文獻13篇。其中,來自何曉麗的兩篇文獻(何曉麗, 王振宏, 王克靜, 2011; 何曉麗, 2013)雖然出自同一課題組,但兩個研究分別采用了不同的被試群體,同時在研究方法與變量的選擇上也并不相同,因此最終用于元分析的數據并沒有重疊。
2.3 變量編碼

圖 1 文獻檢索、納入及排除流程
對納入元分析的文獻進行如下編碼:文獻信息(作者名+文獻時間),情緒的誘發方式(直接書寫任務、視頻誘發、文本材料誘發),信任對象的熟悉性(熟悉、不熟悉),信任測量工具類型(問卷測量、行為游戲)。對每一個獨立樣本,計算得到一個效應量。如果一篇文獻中包含多個獨立樣本,則對應進行多次編碼。由于部分文獻可能包含多項實驗,而部分實驗有可能包含多種不同條件,為了避免單篇文獻生成過多效應量而占用過大權重,從而可能產生一定的結果偏差。我們對部分文獻的條目進行合并處理,合并條目的具體原則是:若一項研究同時報告了多種條件下的信任水平,且這些條件(如被試年齡、測量項目)并非本研究關注的調節變量,則將其平均為一個合并效應量(pooled effect size);但如果該變量為本研究關注的調節變量(如信任對象的熟悉性、情緒的誘發方式等),則不進行合并。最終共得到70個獨立的效應量。其中,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獨立效應量有47個,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獨立效應量有23個,具體見表1、表2。

表 1 元分析中納入的原始研究(積極情緒對信任的影響)

(續表1)

表 2 元分析中納入的原始研究(消極情緒對信任的影響)
2.4 元分析過程
2.4.1 效應量計算
元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將已有研究進行綜合統一,獲得一個客觀的平均效應量(effective size)。為了考察情緒對信任的影響,需要比較積極(或消極)情緒條件與中性情緒條件下,信任水平的差異。因此,在效應量計算時采用Cohen's d作為效應量,對于研究中報告了樣本量、平均數、標準差的原始數據,采用Cohen's d的公式進行計算。針對研究中報告原始數據r值、F值、t值、χ2值等則根據相應的公式進行效應量的轉換。
2.4.2 模型的選定
元分析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或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這兩者最主要的區別在于權重成分的不同。固定效應模型假設元分析中所有研究背后只存在一個真效應量,而每個研究效應量的不同是由抽樣誤差引起的。隨機效應模型則認為每個研究的真效應量都是不同的,每個研究效應量的不同是由真效應量的不同和抽樣誤差共同引起的(Borenstein,Hedges, Higgins, & Rothstein, 2009)。兩個模型的不同假設會導致元分析中平均效應量的顯著性檢驗、區間估計以及調節變量的顯著性檢驗方法不同(Hunter & Schmidt, 2000)。在模型的選定上,Borenstein等人建議主要考慮元分析的研究是否擁有一個共同的效應量以及元分析的目的。具體來說,如果認為元分析中的研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而元分析得到的總效應量只是針對包含的研究所涉及的總體,不推廣到其它總體,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相反,如果元分析中包含的研究中被試群體、測量工具不同,并且有理由相信這種不同會影響結果時,使用隨機效應模型更加合理(Borenstein et al., 2009)。
在最終確定的21篇研究文獻中,情緒與信任的測量工具不同,被試的樣本涉及到不同的文化群體,不適合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此外,本研究的元分析也將探討情緒誘發方式、測量方法以及信任對象的熟悉性的調節作用,因此隨機效應模型更適合本元分析。在后面的元分析中,將進一步采用異質性檢驗來驗證我們的模型選擇。
2.4.3 發表偏差
當發表的研究文獻不能系統性地代表該領域已經完成的研究總體時,就認為產生了發表偏差(Rothstein, Sutton, & Borenstein, 2005)。發表偏差會導致某一領域的研究文獻不完整,這會嚴重影響元分析的結果,因為它可能會導致最終得到的效應高于真實值(Kuppens, Laurent, Heyvaert, & Onghena,2013)。針對發表偏差的問題,我們首先在文獻搜索階段盡可能獲取沒有發表的文獻。在后面的元分析過程中,我們還會采用漏斗圖(funnel plot)、Egger's檢驗以及剪補法(trim and fill method)來評估本元分析的發表偏差。
漏斗圖可以從主觀的角度初步檢查發表偏差,若漏斗圖的效應量左右分布均勻,則說明元分析無發表偏倚性,反之則有發表偏倚性(Rothstein et al., 2005)。Egger線性回歸檢驗采用線性回歸法檢驗發表偏差,一般先求出線性回歸方程的截距(Egger's intercept)及其95%CI,再對該截距是否為0進行假設檢驗,如果不顯著,則表明不存在發表偏差(Egger, Smith, Schneider, & Minder, 1997)。剪補法主要通過先剪后補的方式使得各研究在平均效應量的左右兩邊盡量對稱分布,并重新估計合并效應量的真實值(Duval & Tweedie, 2000),若剪補后的效應量未發生顯著變化,則可認為不存在發表偏差(吳鵬, 劉華山, 2014)。
2.4.4 數據分析及處理程序
應用Excel進行前期的文獻整理與編碼,通過R語言的Metafor程序包進行元分析效應量的計算、發表偏差檢驗以及調節效應分析(Viechtbauer, 2010)。
3 研究結果
3.1 異質性檢驗
分別對積極情緒以及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元分析數據進行了異質性檢驗(heterogeneity test),Q檢驗表明,積極情緒(Q(46)=290.09, p<0.001,I2=84.35%)與消極情緒(Q(22)=84.12, p<0.001,I2=74.05%)各項研究中的效應量是異質的。根據Borenstein等人(2009)對I2的解釋,說明在本研究中有84.35%(74.05%)的觀察變異是由兩者關系中真正差異所造成的。異質性檢驗的結果表明,選定隨機效應模型來進行元分析是準確的。
3.2 發表偏差檢驗
首先,通過漏斗圖來檢查本元分析的發表偏差,如圖2所示,橫軸是效應量d,縱軸為其標準差。從漏斗圖來看,涉及本研究的元分析文獻基本均勻分布于總效應量兩側,這一分布特點表明,本研究的元分析數據存在發表偏差可能較小。為了更準確的檢驗發表偏差,我們進行了Egger's檢驗。Egger's檢驗表明,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元分析存在發表偏差的可能性,z=3.06,p=0.002。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元分析不存在發表偏差,z=0.15,p=0.881。
進一步采用Duval和Tweedie提出的剪補法檢驗發表偏差對元分析結果造成的影響(Duval &Tweedie, 2000)。結果發現,剪粘研究文獻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對積極情緒以及消極情緒影響信任的元分析進行總體效應檢驗,兩個元分析的總體效應依然顯著(積極情緒: 剪補前z=4.59, p<0.001, d=0.41, 剪補后 z=1.97, p=0.049, d=0.19; 消極情緒: 剪補前 z=–2.08, p=0.037, d=–0.23, 剪補后z=–2.08, p=0.037, d=–0.23)。此外,最終進行元分析的文獻中,未發表的文獻占38%,這一比例已經很大。綜合以上結果表明,本研究的元分析存在發表偏差的可能較小。

圖 2 涉及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研究的漏斗圖
3.3 主效應
分別對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影響信任的研究進行主效應檢驗,結果發現,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主效應顯著,z=4.59,p<0.001,效應量為0.41。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主效應顯著,z=–2.08,p=0.037,效應量為–0.23。根據Cohen (1992)的標準,當效應量d為0.2,0.5,0.8時,分別對應效應量小、中、大的界限,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效應量基本屬于中等效應量(見圖3),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效應量基本屬于較小的效應量。

圖 3 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效應量分布圖
3.4 調節效應檢驗
對積極情緒影響信任的隨機效應模型進行調節效應分析。結果發現情緒誘發方式(QB(2)=2.87, p=0.238)、信任對象的熟悉性(QB(1)=2.35, p=0.125)以及信任測量工具(QB(1)=0.90,p=0.343)的調節效應均未達到顯著,見表3。

表 3 積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調節效應檢驗(隨機效應模型)
對消極情緒影響信任的隨機效應模型進行調節效應分析。結果發現情緒誘發方式(QB(2)=3.41, p=0.182)、信任對象的熟悉性(QB(1)=2.00, p=0.157)以及信任測量工具(QB(1)=0.60,p=0.438)的調節效應均未達到顯著,見表4。

表 4 消極情緒對信任影響的調節效應檢驗(隨機效應模型)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討了情緒對信任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情緒的誘發方式、信任的測量方法以及信任對象的熟悉性的調節作用。元分析的結果表明,積極情緒對個體的信任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呈中等效應量;而消極情緒對個體信任則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較小效應量。
總體而言,本元分析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心境一致效應”(Winkielman et al., 2007)。積極的情緒傾向于使個體對他人與社會事件做出更積極的判斷,增加對他人的信任;而消極情緒狀態更容易使個體對他人做出消極的評價,從而降低信任水平。以往很多研究也支持了上述觀點,如有研究發現,高興、感恩等積極情緒可以促進合作行為與利他行為的產生,提高對親密他人的一致感,并且能夠增加對他人的信任;而消極情緒則會增加個體對風險的敏感性與規避行為,降低對他人的合作傾向與信任(Forgas,1998;Bartlett & DeSteno, 2006; 韓香香, 2013; 李常洪, 高培霞, 韓瑞婧, 宋志紅, 2014)。雖然有研究提出在積極情緒狀態下,會促使個體更多地運用環境中的信息,并影響他們隨后的社會判斷,從而可能削弱積極情緒的直接作用(Bodenhausen, 1993)。但后續的研究發現,在積極情緒條件下,被試可能并不會過多考慮他人的信息,而更多的依賴他們在情緒效價影響下的“第一感覺”對他人進行評價(Bodenhausen, Kramer, & Süsser, 1994)。因此,在本元分析中,積極情緒對個體的信任水平整體還是呈現促進的效應。
消極情緒對人際信任影響的結果也對“心境一致效應”提供了一定支持,即在消極情緒狀態下,個體對他人的信任會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但其效應量小于積極情緒下的效應量。相比積極情緒,消極情緒對信任的影響可能會更加復雜。在消極情緒狀態下,個體在進行社會判斷時更加謹慎,往往會對情境中的各種信息進行比較深入的思考與分析,更少的借助已有的知識經驗(Fiedler, 2001; Bless & Fiedler, 2006)。此外,消極情緒對個體的優勢認知加工具有抑制作用(金靜,胡金生, 2015)。優勢認知加工是大腦中指向當前任務的、主導的、可及性最高的信息加工過程(Huntsinger, Sinclair, Dunn, & Clore, 2010)。如當信任方初始對受信方產生“可信任”的印象作為優勢認知加工時,消極的情緒狀態會抑制這種印象,從而減少個體的信任;但如果信任方對受信方產生“不可信任”的印象作為優勢認知加工時,消極情緒同樣會抑制這種印象,從而可能增加個體的信任水平。而在眾多有關消極情緒與信任關系的研究中,信任雙方的初始優勢認知加工很少作為可能存在的干擾因素被控制。因此消極情緒在雙方信任建立過程中所起作用的正負性具有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影響其效應量的大小。
雖然,從整體來看,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對信任有一定的促進或抑制作用,但也有一些研究并沒有發現上述效應(Lount, 2010; 鄭信軍, 何佳娉,2011)。回顧已有文獻,我們發現有關情緒與信任之間關系的研究在變量的操縱上存在一定差異。比如情緒與信任的測量方式、信任目標線索的類型等,為此我們對這些可能存在的調節因素進行了探討。首先,調節效應檢驗發現,情緒誘發方式的調節作用不顯著。直接書寫任務與材料啟動是當前兩種主要的情緒誘發方式。其中材料啟動又劃分為圖像材料與文字材料兩種,具體包括如情緒圖片啟動法(Lang & Bradley, 2000)、Velten情緒啟動法(情緒語句啟動法)(Velten, 1968)等。以往的情緒相關研究中發現,個體在不同誘發方式下產生的情緒效價水平存在差異(袁婉秋,2010)。雖然本元分析中情緒誘發方式的調節作用不顯著,但相對于直接書寫任務,兩種材料啟動誘發方式下積極情緒對信任的促進效應有更好的趨勢。這表明在相同的實驗情境下,不同情緒誘發方式可能會導致被試情緒狀態產生差異,進而影響其信任水平。因此在研究情緒對信任的影響時,情緒的誘發方式是需要嚴格控制的重要實驗條件之一。
其次,信任的測量方式的調節作用不顯著。當前,對信任的測量方式主要包括問卷法與行為游戲法兩種。問卷法主要通過問卷測量個體的信任傾向與信任信念,是針對個體對他人或特定對象是否值得信任的一種心理期待的評估(何振芬,2014),其中Mayer和Davis (1999)設計的信任量表被研究者們廣泛認可,該量表從能力、善意和正直三個維度對信任進行測量。行為游戲法主要以被試在游戲中的合作行為為信任的指標,目前以Berg等(1995)設計的信任游戲應用最為廣泛。從已有的實證研究來看,無論是采用行為游戲法還是問卷法,對不同信任維度的測量都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Kim, Ferrin, Cooper, & Dirks,2004; De Cremer, van Dijk, & Pillutla, 2010; Thomson,Adams, Filardo, DeWit & Flear, 2012; Haesevoets et al.,2016),因此測量工具類型的調節作用不顯著。但也有研究者發現,信任游戲與問卷法測量的信任存在不一致性(Glaeser et al., 2000)。行為游戲法是以被試在游戲中的合作行為作為信任的指標,因此通過該方法測量的信任更多的是一種狀態性的信任,更可能會受到情境信息的影響;而問卷法則是測量個體對于社會中某類特定人群的信任傾向與信任信念,其測量結果更傾向于一種相對穩定的特質性信任。兩種信任的測量方式雖然針對同一種心理活動,但原理與適用的研究范圍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也提示我們在以后研究中,對于信任的測量方式需要謹慎選擇。
最后,信任對象熟悉性的調節作用也不顯著。根據情感滲透模型的觀點,情緒對社會判斷的影響會受到目標線索的干擾,面對不同的目標信息,個體會采取不同程度情感注入的認知策略(Forgas, 1995)。以情緒與信任的關系為例,當受信方的背景信息暗示其信任時,積極情緒會增加信任;當背景暗示不要信任時,積極情緒反而可能會降低信任水平。以往研究表明,當被試面對熟悉的受信者時,感知到的目標信息線索更多的傾向于積極的、可信的,積極情緒對信任起到了促進作用;而面對陌生的受信者時,他們感知到的目標信息傾向于未知與不確定,因此積極情緒與信任之間的關系并不明確(Dunn & Schweitzer,2005; 何曉麗等, 2011)。本研究并沒有發現信任對象的熟悉度對積極情緒與信任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可能的原因如下:(1)從以往研究來看,情緒對信任影響的線索效應還會受到信任情境信息、群體信息等多種因素的影響(Lount, 2010; 何曉麗, 2013)。多數情緒與信任關系的研究都未對這些變量進行嚴格統一的控制,進而可能使兩種線索下的信任水平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擾。(2)從本研究來看,選取的文獻樣本中,多數研究以陌生人為信任對象(n=38/n=19),使得兩種條件的樣本量失衡,從而導致兩種線索下的信任水平差異不顯著。
本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情緒與信任之間的關系,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在最初的文獻篩選過程中,由于許多文章提供的數據不足,導致部分相關研究無法用于元分析而被剔除;其次,不同效價的情緒的具體類型也可能會影響情緒對信任的作用。比如有研究發現,憤怒與悲傷同屬于消極情緒,但他們對信任的影響程度是有差異的(李常洪等, 2014),這可能是由不同類型情緒之間其他維度的差異(如強度、指向性、確定度等)所導致。但由于只有少部分文獻對情緒的具體類型進行了劃分或闡述,在本元分析中無法將其作為調節變量進行考察。因此有關情緒類型在情緒與信任關系之間的作用,未來研究中有待進一步探討。最后,本元分析中關于信任線索調節作用的檢驗只局限于信任目標的熟悉度,然而從已有的相關研究來看,信任線索還包括如情境信息以及受信方的可信度信息等,這些線索都有可能影響情緒與信任之間的關系。因此,對信任線索在情緒與信任關系中起到的調節作用還有待深入探討。
信任作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心理契約,是合作關系的起點、前提和基礎,也是人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的研究發現,信任不僅受到認知的影響,也會受到情緒與情感的影響。積極的情緒體驗會使個體更多的感知到外界與他人積極的信息,從而提高個體對他人判斷的積極性,增加人際信任;消極情緒則會使個體更多的感知到外界與他人消極的信息,從而削弱個體對他人判斷的積極性,降低人際信任。然而從已有研究來看,上述過程可能會受到如目標信息、情境背景信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此外,研究中實驗的具體操縱如變量的誘發與測量方式等也可能會影響到情緒與信任關系結果的一致性。未來研究需要繼續拓展與情緒和信任相關的實驗范式,盡量減少實驗因素對最終結果的影響;同時要明確各種可能存在的干擾變量并加以控制,更加嚴謹、系統地探索情緒對信任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
5 結論
本元分析發現積極情緒對個體的信任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呈中等效應量;消極情緒對個體信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呈較小效應量。調節效應檢驗發現,情緒的誘發方式、信任對象熟悉性以及信任測量方式的調節作用均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