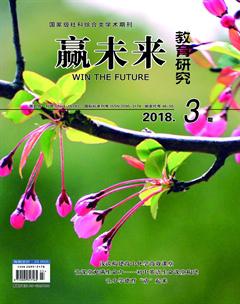宗法家庭婚姻倫理下的婦女命運探微
摘要:《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快嘴李翠蓮》和《江城》是三部表現(xiàn)宗法家庭婚姻的作品,在三部作品里的女性無論是符合婦德要求還是奮起反抗,都不約而同地有被休的經(jīng)歷。本文試圖以相對公允的態(tài)度對這三部作品進行分析,既不以婦德的森嚴(yán)為婦女的無德開脫,也不以婦女的無德寬恕婦德。或許在婦德約束普遍為人多接受的文化環(huán)境里,宗法家庭婚姻倫理下的婦女命運都無可奈何地走向悲劇。
關(guān)鍵詞:《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快嘴李翠蓮》;《江城》;婦德
在宗法倫理道德貫穿的中國社會,婚姻有“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的功能,它是影響家庭倫理秩序的活躍因素。《顏氏家訓(xùn)》卷一說:“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婦,有夫婦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而在家庭倫理秩序中,婦女是影響家庭和諧的核心,因之婦德成為禮教的焦點。《禮記·昏義》對婦女提出了“四德”的要求:“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更是在《女誡》中對“四德”做出了更為詳細(xì)的解釋。這些要求成為歷代婦女言行舉止的準(zhǔn)則,違背者會被冠以“不守婦道”之罪名。
隨著時代對婦女言行舉止進行新的釋義的同時,文學(xué)作品對婦德的描寫、對宗法家庭婚姻倫理下婦女命運的探尋也從未止步。《山海經(jīng)》已經(jīng)記載了療妒之方,《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早期表現(xiàn)宗法家庭婚姻倫理的文學(xué)作品,《齖?新婦文》、《江城》是對婦德進行描寫的代表。這些作品都不約而同把我們引向?qū)@樣一個問題的思考,即在宗法家庭婚姻倫理下婦女的命運如何?
一、歇斯底里江城
《聊齋志異》中,以愛情婚姻為題材、涉及婦女問題的作品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在這種題材的故事中,蒲松齡主要塑造了兩種女性形象:一種是才貌德皆具近乎完美的正面女性形象,另一種則是性格上有嚴(yán)重缺陷的悍妒婦形象。而《聊齋志異》中“悍妒婦”的最佳代表當(dāng)屬《江城》里的江城和《馬介甫》里的尹氏。在這里本文以《江城》篇中的江城為代表,對蒲松齡筆下的悍妒婦形象進行分析。
江城“明眸秀齒”生得美麗,與高蕃兩小無猜。婚后“夫妻相得甚歡”,但江城性格善怒,“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因之責(zé)怪高蕃被江城所聞,江城于是變本加厲“懲罰”高蕃,后被夫家遣歸。
縱觀全篇,江城這一形象的優(yōu)點表現(xiàn)在:美麗(“明眸秀齒”)、聰明(以己巾易高蕃之巾)、能干(“又善居積,三年翁媼不問家計”);缺點體現(xiàn)為:善怒和殘忍。善怒的性格來源于過度的自尊,不允許別人對自己的行為有任何的“非議”。前有聽到翁媼對兒子的逆來順受進行責(zé)備后,用更加嚴(yán)厲的“懲罰”施加在高蕃身上。后有用惡語反詰父親的教導(dǎo),樊父發(fā)誓與江城斷絕關(guān)系,以致在父母相繼去世時,江城也不去吊喪。如果說之前公婆的話具有一定的挑唆意味,那么樊父苦口婆心的勸導(dǎo)換來的卻是江城的惡語反擊與死生不復(fù)往來,這不能不看作是過度自尊的表現(xiàn)了。江城善怒性格的另一個來源是別人對自己發(fā)起的挑戰(zhàn),如江城將二姐打得“齒落唇缺”也是起因于二姐操杖打了高蕃。這一情節(jié)與其將之歸為江城對高蕃的感情,不如歸結(jié)為對他人踐踏自己“威嚴(yán)”的反擊更為恰當(dāng),江城不也自己坦言“人家男子,何須他撻楚耶!”關(guān)于江城殘忍的性格特點,篇目中隨處可見,其中表現(xiàn)最突出的莫過于“剪腹間肉互補”的情節(jié)了。因疑高蕃與彼女有私,乃“以酒壇囊婢首而撻之”,并對二人進行殘忍的“懲罰”。
誠然,即使跨越時代的鴻溝,具有江城這樣性格特點的女性在如今的婚姻中也會讓人避之唯恐不及。《聊齋志異》中江城的結(jié)局像眾多同類女性一樣,她悔過自新,完成了由悍妒婦向賢婦的轉(zhuǎn)變。清初悍妒婦現(xiàn)象已經(jīng)比較嚴(yán)重,蒲松齡在小說中想出各種各樣的手段,希望借小說之力對悍妒婦提出警示,引導(dǎo)她們往賢婦的方向發(fā)展。而對于悍妒婦身邊男性的缺點則沒有進行反思,如《江城》中高蕃見異思遷,先是與李云娘有染,繼而愛陶家婦雙翹,又鐘情謝芳蘭。作者將江城描寫為“胭脂虎”,對高蕃的行為不僅沒有進行反思,反而順其意為之安排了納謝芳蘭于閨中的情節(jié)。在這里蒲松齡是以丈夫為中心,為理想中的賢婦設(shè)定道德標(biāo)準(zhǔn),這種“文士化的男權(quán)意識”[ 1],忽略了女性本身的個性、主體尊嚴(yán)和感情。所以,江城即使自尊、充滿自我意識,歇斯底里地面對身邊的“非議”與挑戰(zhàn),最終也還是歸與夫權(quán)的統(tǒng)攝之下。
二、多言善辯李翠蓮
鄭振鐸最早指出,《齖砢新婦記》是宋元話本《快嘴李翠蓮》的祖本。它們反映了宗法婚姻倫理下婦女的悲劇。李翠蓮是員外之女,“姿容出眾,女紅針指,書史百家,無所不通”,不足之處即是口嘴快。篇目之中對李翠蓮口嘴快的描述可以分為兩部分:出嫁之前和出嫁之后。出嫁之前李翠蓮的多嘴善變并非無道理:“觀二親滿面憂愁,雙眉不展”便道出“男成雙,女成對,大家歡喜要吉利”的勸導(dǎo);爺娘擔(dān)心翠蓮不被公婆喜歡,為人恥笑,翠蓮說出“從小生得有志氣”以寬慰爺娘;與隔壁張?zhí)慕煌芯渚湓诶恚矎膫?cè)面顯示出李翠蓮成熟懂事的一面。如果說出嫁之前翠蓮的言語不無道理,重在“多言”的話,那么出嫁之后翠蓮的言語則更多的顯示出“善辯”的特點。對母家兄嫂的挖苦、對媒婆與撒帳先生的辱罵、與夫家親屬的據(jù)理力爭都體現(xiàn)了李翠蓮的“善辯”,前二者雖有無理的傾向,但也是翠蓮自我意識的反映。因不滿兄嫂的行為,進而直言挖苦;媒婆行為的前后不一,引起了李翠蓮的反感;而撒帳先生的那句“河?xùn)|獅子吼”更是觸犯了李翠蓮的尊嚴(yán),故而對之謾罵。
班昭《女誡》中對婦言要求“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后說,不厭于人”,“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司馬光在《家范》中表示“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這些都顯示出宗法家庭婚姻倫理對沉默婦德的欲求。在多言眾所忌的文化背景里,即使李翠蓮生長在中國封建社會轉(zhuǎn)型期的兩宋,市井婦女享有一定的經(jīng)濟地位,即使她“挑描刺繡能績紡”、大裁小剪漿洗縫聯(lián)全都會,也無法阻擋“夫家、娘家著不得”的悲劇命運。與江城相較,翠蓮只是口嘴厲害些,對他人并無造成人身上的傷害。她的性格特點已經(jīng)接近現(xiàn)今的尋常人了,但最終還是要與青燈古佛共余生。簡言之,在當(dāng)時的社會里,一個多言善辯的女子是不能得善終的。
三、溫柔敦厚劉蘭芝
如果說江城的被休是因其悍妒的個性,李翠蓮的被休是因其多言,那劉蘭芝的被休則是無緣由。她既能誦詩書亦能彈箜篌,織素裁衣不在話下,吃苦耐勞無怨無悔。即便“夜夜不得息”,可大人還是故嫌遲。最后終于禁受不住君家的為難,提出了及時遣歸的要求。
儒家詩教強調(diào)“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注重含蓄蘊藉、以理節(jié)情的中和之美。孔穎達(dá)《禮記正義》對此解釋為:“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2]作為一個在封建社會里成長起來的女性,劉蘭芝是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的。雖然主動要求遣歸是不堪忍受阿母的為難,蘭芝在離開夫家之際還是以禮待之,并囑托小姑“勤心養(yǎng)公姥”;雖然與焦仲卿有不相負(fù)的誓言,但面對阿兄“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的責(zé)問時,并未與兄長辯駁,而是道出“處分適兄意”,劉蘭芝的言行舉止處處體現(xiàn)著以理節(jié)情的中和之美。雖然《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的主旨在于抒發(fā)一種愛情理想,處于弱勢地位的劉蘭芝得到了讀者的同情,但也無法掩蓋對其悲劇的命運。《大戴禮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溫柔敦厚的劉蘭芝并未觸犯“七去”里的準(zhǔn)則,然而只因焦母的“久懷忿”而不得已離去。
小結(jié)
歇斯底里的江城因悍、妒被休,多言善辯的李翠蓮因善辯被休,而劉蘭芝則因不得焦母歡心被休。仔細(xì)分析這三位被休婦女的經(jīng)歷便能發(fā)現(xiàn):過分宣揚自我意識對他人造成一定的侵害會被休,只是彰顯自我意識并未對他人造成侵害也被休,更甚者即便溫柔敦厚滿足婦德的要求,但因得不到宗法婚姻里長輩的肯定也會被休。無論是在理學(xué)禁錮的清代小說里,還是婦女享有一定經(jīng)濟地位的宋元話本里,亦或是反映現(xiàn)實的漢樂府民歌里,婦女的命運并沒有因折中、妥協(xié)而得以有所好轉(zhuǎn)。或許在婦德約束普遍為人多接受的文化環(huán)境里,宗法家庭婚姻倫理下的婦女命運都是悲劇的走向。
參考文獻:
[1]郭黎.論《快嘴李翠蓮記》的雙重解構(gòu)意義.黃石高等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2002(12)
[2]黃大宏.沉默的婦德與宗法家庭婚姻倫理.山西師大學(xué)報,2005(3)
[3]肖燕憐.人物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快嘴李翠蓮記》言語沖突淺析.新疆財經(jīng)學(xué)院學(xué)報,2005(3)
[4]王菊花,李敬文.從宋話本的角度還原快嘴李翠蓮形象.邊疆經(jīng)濟與文化,2008(8)
[5]文美容.《聊齋志異》中的妒悍群像研究.首都師范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4(5)
注釋:
[1]劭吉志:《志異》到“俚曲”——蒲松齡新解,濟南:齊魯書社,2008版,第36頁。
[2]黃海寧:對《葉普蓋尼·奧涅金》中達(dá)吉雅娜形象的再認(rèn)識[J].沈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2008(6)
作者簡介:
楊利平(1991-)女,漢族,籍貫:河南周口,學(xué)歷:碩士在讀,單位:天津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