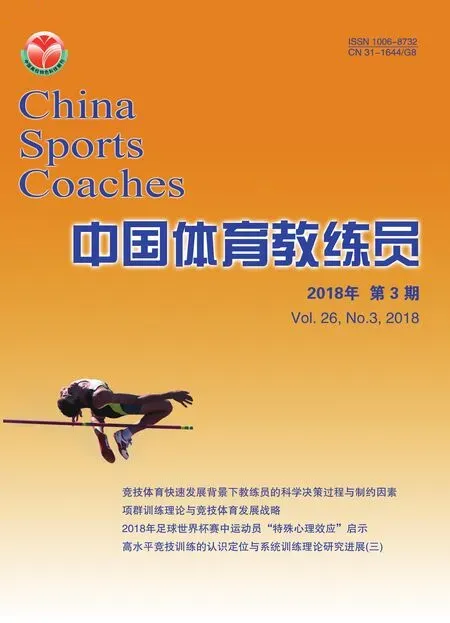項群訓練理論與競技體育發展戰略
田麥久
(北京體育大學,北京 100084)
戰略,是為實現全局性目標所做出的指導全局工作的總體規劃。競技體育的主要社會產品是運動成績,競技體育發展的首要目標即是賽出高水平的運動成績。因此,一個國家的競技體育發展戰略必然應圍繞在國際賽事中取得理想的參賽成績這一目標予以制訂。
運動競賽是分運動項目進行的,重大的綜合性國際大賽通常包含許多運動單項比賽。近幾屆夏季奧運會均設立了300個左右的小項,人們通常依綜合性大型運動會金(獎)牌榜排名對各參賽國家(地區)的綜合實力進行比較和評價。這一指標雖非完全精確,但具有較高的效度,并已成為國際體壇的普遍共識。所以,我們制訂國家競技體育發展戰略,就要圍繞如何在奧運會等大型綜合性賽事的金(獎)牌榜上獲得更好排名這一全局性目標做出全面的謀劃。項群訓練理論中關于競技運動項目的分類,關于各個項群競技特點的解析和訓練要求的歸納,關于一個國家(地區)地域學、人類學特點的揭示,以及關于國家(地區)訓練參賽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認知,都為制訂發展戰略決策提供重要的認知基礎及可靠的理論依據。
1 項群訓練理論與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科學鏈接
1.1 項群分析是競技體育發展規劃的戰略思維
在制訂國家(地區)競技體育發展戰略時,建立戰略目標是一項重要的內容。而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目標的制訂與具體的運動項目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首先要對不同項目的發展水平進行評價,解析各個項目的競技潛力,進而對不同等級運動項目未來可能達到的競技水平進行預估,據此確立在未來大賽中的參賽目標,由此便可對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水平做出決策。
對一個國家(地區)運動項目的競技水平排序,可清楚地發現,某些高水平的競技運動項目,常會在某個或某些重要的競技特征上(或在競技能力的結構上,或在技術動作的結構上,或在比賽結果的判定上)高度相似;而競技水平較低的運動項目在上述幾方面的特點常常也會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一現象表明,不同國家(地區)運動項目競技水平發展的等級差別,常常有著明顯的項群屬相(表1)。

表1 競技體育發展地域性差異的項群特征
項群分析提示我們,一個國家(地區)的某些優勢項目很可能存在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在這些項目之間,集束性地存在相似的競技特點和訓練要求。人們應主動揭示這些特征,發展這些特征,規劃不同群組運動項目發展的目標、方法和途徑,從而全面地把握一個國家(地區)競技運動的整體態勢,確立適宜、有效的項目結構。
1.2 項群訓練理論搭建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研究的新平臺
在三層次運動訓練學理論體系中,關于所有競技運動項目訓練規律的闡述稱作一般訓練理論,關于一個競技項目訓練規律的闡述稱作專項訓練理論,分別屬于宏觀的和微觀的層次,項群訓練理論則是在2個理論層次之間建立的中觀層次,搭建了新的理論平臺。在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項目結構研究中,同樣也是如此。人們基于一般訓練理論,進行面對所有運動項目的戰略設計;基于專項訓練理論,為一個運動項目設計發展戰略;而基于項群訓練理論,則為一組運動項目設計發展戰略。總體發展戰略若由許多單項發展戰略直接綜合構成,優點是具體、詳盡,但整體把握則會感覺吃力;若輔以項群發展戰略,則明顯有利于簡潔而明確地做出全局的描述和判斷。
對任何一個由多個單體組成的群體進行綜合分析時,引入分類解析都是非常必要的。在綜合性大型賽事的備戰規劃中涉及到競技項目的配置,當然也需要對競技項目進行分類并給予科學的闡述。例如,在奧運會參賽戰略的制訂與實施中,既要做出國家(地區)綜合競技水平的評估與發展設計,又要對300多個競技項目逐個進行精確的評價和解析。同時,在項群這一中間層次,對于不同類別運動項目戰略價值的判定,明顯有助于戰略發展重點的選擇和戰略組織的實施。既能幫助決策管理層更清晰、簡潔地統觀包括所有競技運動項目的全局,又可在中觀層面明確對不同項群參賽的競技期待,實施對不同項群備賽組織的分類管理。
對所要開展的運動項目進行項群分類,會促進許多訓練理論和方法的拓展。如同一項群中不同項目訓練理念的溝通與互補,訓練方法的相互借鑒或移植,訓練安排的交流與比較。優勢項群中暫時落后的競技項目,有成功的“模板”可以效仿和借鑒,因而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從項群視角觀察發展滯后的項群,則常常能以較為開闊的視野揭示落后的原因,尋找改變落后狀況的途徑。項群訓練理論所搭建的新理論平臺,對于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制訂與實施無疑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2 項群訓練理論與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研究與應用
項群訓練理論創立以來,得到了業界高度的認同,并被廣泛地應用于多個體育領域,在國家、地域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制訂與實施中,也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2.1 項群訓練理論視角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研究開展活躍
項群訓練理論的創立,喚醒和強化了業者的項群意識,使人們的競技體育戰略思維更加活躍。其中,從項群視角進行競技運動項目發展戰略研究,成為一種被普遍采用的解析路徑。眾多學者將項群訓練理論應用于國家或地區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研究中。例如,冷永強的《第24~26屆夏季奧運會體能主導類項群獎牌歸屬的地理分布特征研究》;楊波的《中俄技能類難美項群優勢項目的比較研究》;王廣楠的《奧運會男子短跨項群發展軌跡與動力因素考究》;張建華的《我國歷屆奧運會金牌獲得項目的項群特征》;陳最新的《從奧運表現論中國競技體育項群的發展》;陳亮的《多維度項群視野下的中國夏季奧運項目成績結構與發展演變》等。楊小帆的《我國“命中類無設防型”項群優秀人才流動性分析》一文中,探討了我國“命中類無設防型”項群優秀人才的分布和流動情況,指出計劃經濟時代優秀人才資源的流動以“垂直流動”為主,缺乏“平行流動”,“國際流動”具有選擇性,“職業變動”呈現單一性;改革開放以后,優秀人才資源是在“垂直流動”基礎上加快了“水平流動”,“國際流動”頻繁,“職業變動”多樣;并提出該項群進一步發展的建議[1]。
在我國省市層面,也有許多學者從項群理論的視角,嘗試對不同省市的競技體育發展特點加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適合各省市的競技體育發展戰略。例如,羅智在《全運會優勢項群的板塊構造及其時空漂移學說》一文中,研究了第4~9屆全運會期間,各地區各優勢運動項群的時空變化。文中還對廣東省的競技實力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第4~9屆全運會競技中,體能主導類各項群及表現難美類亞項群是廣東省的傳統優勢運動項群,其中體能主導類項群的競技表現是構成整體競技實力的基架,也是廣東競技實力提高的重要保障;長距離游泳和射擊項目競技實力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點,而長距離跑、乒乓球和柔道只能排在可持續發展的第2位。高鴻輝在《我國全運區域競技實力發展的非均衡歷程與對策》一文中,探討了第6~10屆全運會期間各項群競技實力區域發展態勢的均衡性問題[2]。
2.2 積極推進優勢項群率先發展
在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制訂和實施中,特別是在積極推進優勢項群的率先發展方面,項群訓練理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1985年第1次全國體育發展戰略研究會上,田麥久做了題為《我國1986—1988亞運會、奧運會重點項目的選擇與確定》的研究報告[3]。報告中談到,“對不同等級項目的項群特點的分析表明,我國運動員在技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技心能主導類表現準確性項群及技戰能主導類隔網對抗性項群中的許多項目均達到世界水平”,與“男子田徑跳躍項目和輕級別舉重項目”一起,組成了我國競技運動的優勢項群集。
繼而,在國家體育總局1989年1月召開的全國體育布局工作會議上,田麥久、朱章玲等做了《我國重點項目設置與布局的宏觀決策》的主題報告。報告中談到,“將近年來在世界大賽中2次以上進入前3名的項目列入優勢項目。從中看出,我國大多數優勢項目都歸屬于以下3個集合:其一,技能類中表現難美性、準確性及隔網對抗性3個項群;其二,女子同場對抗性、格斗對抗性、力量性項目及部分周期性競速項目(包括速度性與耐力性);其三,男子輕體重級別舉重、速度力量性項目(曾經名列前茅的部分跳躍項目)[4]”。進而提出以下建議:“對優勢項群中的先進項目(如體操、乒乓球、女子排球)應列為頭等重點,但需注意提出實事求是的參賽期望。”“對優勢項群中暫時落后的項目(如藝術體操、網球),應充分利用主客觀有利的發展條件,投入較大力量,求得競技水平的迅速發展,力爭盡快進入獲獎行列。”“對競技強度相對較低的新項目(如蹦床、帆板),應給予密切關注,及時了解和預測競技項目的發展趨向,力求盡早進入競爭者的隊伍。”“對獲獎效益較高的落后項目(如田徑、游泳),需下決心大力投入,加強早期選材,訂好長遠規劃,保證系統訓練,以求盡早實現我國競技運動主體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對獲獎效益較低的落后項目(如足球、曲棍球),可取穩步發展態勢,需注意從領導上和宣傳上不可要求過急,切忌拔苗助長。[5]”
上述解析與建議得到了國家體育管理部門的肯定與采納,并付諸于實踐。今天我們回顧30年前提出的戰略建議,大部分已變成了現實。技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中的體操、技戰能主導類隔網對抗性項群中的乒乓球、女排等先進項目繼續保持國際一流水平;優勢項群中的潛優勢項目藝術體操、網球,已有長足的進步;蹦床、帆板等有較大競技潛力的新開展項目多次摘得奧運會金牌;經過多年規劃、科學選材、系統訓練,體能主導類中的田徑、游泳涌現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優秀選手;而技戰能主導類同場對抗性項群的代表性項目中國足球,發展道路依然艱難。競技體育發展的歷史清晰地表明,項群分析是競技體育發展戰略決策的有力武器。
2.3 基于項群解析為建設競技體育大國進行目標設計
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以28枚金牌首次進入金牌榜前3位。其后,中國體育管理層立即著手進行新的戰略設計。在2001年全國體育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田麥久、蔡睿、劉大慶、張英波等做了《2020年我國競技運動水平發展目標定位及實現策略》的大會報告[6]。認為,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遠期目標應定位于有重點、全面發展的競技體育大國。面對我國不同項群競技水平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狀況,對建設全面發展的競技體育大國進行了深刻的解析。報告指出,美國、俄羅斯、德國3個世界競技體育大國的金牌項目都廣泛地分布于12~15個運動大項,并幾乎涉及所有項群。這表明有重點而又相對均衡的項目布局,是競技體育大國實力結構的重要特征之一(表2)。

表2 世界競技體育大國奧運會金牌項目的項群歸屬[6](第24~27屆奧運會合計) 枚
與這3個國家相比,我國選手在第24~27屆奧運會上獲得的金牌集中在較少的運動項目上。第24屆為3項,第25~27屆,則為7~9項,與美國、俄羅斯及德國強盛期的12~15項相比,少5~6項。顯然,奧運金牌項目分布面狹窄是我國與美國、俄羅斯、德國等體育大國的主要差距之一。
面對這一現實,提出將“同群優先發展策略”作為實現2020年我國競技運動水平發展目標的一項重要行動策略。表現難美性、表現準確性及隔網對抗性3個項群是我國最具優勢的項群,同項目訓練理論與方法的借鑒和移植,使得這3個項群中暫時水平不高的項目與其他落后項目相比,具有更好的發展條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曾預測,我國蹦床、藝術體操、花樣游泳和花樣滑冰更有可能比其他落后項目更快地得到發展和提高。十幾年后的今天,我們已經有了花樣滑冰、自由式滑雪的世界冠軍,花樣游泳和藝術體操的競技水平也提高明顯。許多事例表明,實施“同群優先發展策略”,有助于我們以更快的步伐擴大我國優勢項群的隊伍構成,進而促進我國總體競技水平的提高[6]。
“同群優先發展策略”在我國全面發展的競技體育大國的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例如,網球(雅典奧運會女子網球雙打冠軍,“大滿貫”賽事女子雙打、單打冠軍)、蹦床(北京和倫敦奧運會3項次冠軍)、射箭(北京奧運會女子個人冠軍)等項目紛紛取得優異的參賽成績,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發展策略的合理性與有效性。
3 結束語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項群訓練理論被成功地應用于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的制訂與實施中,提高了我國競技運動發展全局謀略的科學性與時效性。我們預期,在建設體育強國的新征程中,項群訓練理論能更好地展現出其科學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