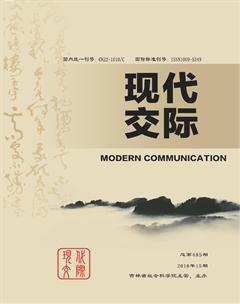淺析天津趙春華案
王晨暉 杜鐘浩
摘要:天津趙春華案曾引發了輿論界一片嘩然,也有不少專家學者試圖通過刑法理論分析,找到為趙春華出罪的理由。本文以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理論為視角,對非法持有槍支罪和趙春華的行為進行分析,盡可能找出最為適當的脫罪理由。
關鍵詞:規范性構成要件 犯罪故意 構成
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8)15-0054-03
2016年8月至10月間,趙春華在天津市河北區李公祠大街海河親水平臺附近擺設射擊攤位進行營利活動。同年10月12日22時許,趙春華被公安機關巡查人員查獲,當場收繳槍形物9支及配件等物。經天津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鑒定,涉案9支槍形物中的6支為能正常發射、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因此檢察機關以涉嫌非法持有槍支罪對趙春華提起公訴,一審宣判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二審考慮到趙春華非法持有的槍支均剛剛達到槍支認定標準,其非法持有槍支的目的是游藝活動的經營,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主觀惡性程度相對較低。二審庭審期間,其能夠深刻認識自己行為的性質和社會危害,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等情節,因此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一、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理論
犯罪構成要件要素分為記述的構成要件要素和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前者是指不需要經過解釋、經驗法則和價值判斷就能理解的構成要件要素,往往由法律直接規定,在法律中出現的用詞最直觀的解讀,即是這種構成要件要素的含義,如“未滿16周歲”。而后者是指需要經過法律規定、司法解釋,或者按照社會經驗法則和價值判斷才能理解的構成要件要素,如“槍支”“淫穢物品”等。
不同的構成要件要素所要求的行為人的認識程度是不一樣的。犯罪故意要求行為人具有實質的故意,實質的故意包括構成要件故意與不法意識,通俗點說就是意識即將發生的結果并且期待或放任結果的發生。如果行為人欠缺構成要件故意,則會發生構成要件錯誤,或者說叫事實認識錯誤。事實認識錯誤又可以被細分為消極的認識錯誤和積極的認識錯誤,前者是指沒有認識到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后者是指錯誤地認識了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而消極的錯誤,可以阻卻主觀故意。
有學者認為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認識,只需要認識到構成該要件要素的基本事實即可,即在認識“槍支”這一因素時,只需要認識到:一,槍的外形;二,以火藥或氣壓為動力;三,發射金屬彈丸或其他材質;四,具有一定殺傷力。但如果一定要細化下去的話,就會發現,對于趙春華而言,在殺傷力的認知上是完全不具有可能性的。
在筆者看來,本案中趙春華的行為完全符合消極的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錯誤,她完全沒有認識到自己所持有之物在刑法上是被評價為“槍支”,是作為一種犯罪的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而存在的,她所認識到的僅僅是這種物品,這種槍型物,可以作為生活中游藝活動的玩具而已。
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這種根源于它需要法律解釋或者價值評價才能被認識的特性,而這種價值評價便賦予了法官在司法實踐中一定的、解釋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權利。可是法官的這種解釋的權利并不是靠他的個人獨裁或者心證得來的,而是需要結合各方面因素,如鑒定意見,證人證言等,法官在對其進行確證的時候,所代表的應當是一般市民之意見,而絕非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工作者,或者擁有精深的法學知識的人。當然這種開放性并不是針對法官這一角色開放的,同時也是針對整個社會、全體公眾開放的。法律具有預測性和指引功能,它需要讓公眾在作出某個行為之前,能預測到該行為會帶來的后果,并且指引公眾選擇適法的行為。公眾對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理解與解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在行為時所作的選擇。
其實在立法中,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這源于其一,立法者的水平有限,縱然他們已經是我國法律工作領域的佼佼者,但畢竟也是常人,而非圣賢,難以事無巨細地規定到位;其二,規范性要素可以克服單純描述客觀事實的局限,從而進行一種類型化的規定,而罪名之下所保護的法益,便是這種罪名的核心要素。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在立法時沒有出現過的情況如果出現在了日后的社會生活中,縱然當時立法者并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但是若侵犯了相同的法益,與這種規范性的罪名有著相同的核心,那么這種新情況也依然可以被涵攝進該罪名之下;其三,人的行為很難不具有社會價值和意義,換言之,沒有哪種行為是純粹的客觀的,而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中所具有的社會規范和價值評價的內容,實際上是在對一個行為進行更為準確的界定。
縱然承認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其開放性的對面,規范性要素也不能脫離其明確性。明確性是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刑法的預測性得以存在的前提。法律畢竟是法律,不是能隨著法官或者行為人的主觀好惡去解釋的東西。明確性與預測性息息相關,法律的明確性,是指引人們選擇適法行為的準繩,是限制法官裁量恣意性的底線。
二、槍支與其相關管理規定
回看趙春華案,“槍支”作為一種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是毋庸置疑的,而法律也試圖對其進行解釋和明確,刑法中對于槍支的規定是“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私藏槍支、彈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實嚴格來說,這一條規定中有很多的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比如“違反槍支管理規定”“持有”“槍支”等。而所謂的“非法”,筆者認為是與前文違反槍支管理規定的同義反復。因此,在本案中,最需要被認識,或者說最需要被明確的兩個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就是“槍支”和“違反槍支管理規定”。
(一)“違反槍支管理規定”
筆者在司法解釋中并沒有找到有明確的對“槍支”的范圍和定義作出規定的條文,僅對什么是非法持有作出了規定。而目前我國相關法律中,與槍支有關且效力位階最高的法律,就是《槍支管理法》。根據《槍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槍支,是指以火藥或者壓縮氣體等為動力,利用管狀器具發射金屬彈丸或者其他物質,足以致人傷亡或者喪失知覺的各種槍支。第四十七條規定,單位和個人為開展游藝活動,可以配置口徑不超過4.5毫米的氣步槍。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公安部門制定。
這兩條規定充分說明了槍支的威力標準,即達到何種威力的是被槍支管理法所規制的,被刑法所禁止的槍支,以及對槍支更細化的管理應當由誰來完成,即國務院公安部門。于是國務院公安部門出臺了《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定》,其中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對不能發射制式彈藥的非制式槍支,按照《槍支致傷力的法庭科學鑒定判據》(GA/T718-2007)的規定,當所發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這里出現的《槍支致傷力的法庭科學鑒定判據》(GA/T718-2007)也是由公安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行業安全標準。
以上筆者列舉了在本案中所涉及的所有的認定槍支的標準,以及可能是“違反槍支管理規定”中所說的“規定”。不難發現,“違反槍支管理規定”在本條中是一個空白的構成要件要素。它需要其他的法律進行填補。空白的構成要件要素是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一種。空白的構成要件要素具有其自己的填補規則,對填補空白構成要件要素的規范中的客觀要素的認識錯誤,是構成要件錯誤,對于填補空白構成要件要素的規范的認識錯誤,是違法性認識錯誤。
也即是說,以上所有的規定如果都是用于填補“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這一構成要件要素的,那么如果趙春華對這些規定產生了認識錯誤,即是違法性認識錯誤,而如果趙春華對于這些規定中的客觀要素,如“壓縮氣體動力”“金屬彈丸或其他物質”等產生認識錯誤,則是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的錯誤。
而事實上,公安部所制定的《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定》和《槍支致傷力的法庭科學鑒定判據》這兩份文件,其屬性都是“國家標準”的“參考性”文件,換言之,在司法實踐中,這兩份文件不具有“非用不可”的效力,因而在對“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這一空白的構成要件要素進行填補時,不應當這兩份文件同樣作為填補的規范,而僅有《槍支管理法》能作為填補空白的規范。
前文已述,趙春華本人的認識錯誤主要是集中在對于槍支的認識上,而非規定的認識上,事實上,對于以上那些復雜的規定,趙春華確實不具有認識的可能性。但對于本案中規定的持有槍支的行為,按照社會一般人的認識程度而言,趙春華也是會有基本認識的,起碼她能認識到,持有槍支是違法的行為,只是她認為自己所持有的物品不是“槍支”而是“玩具槍”罷了。
(二)“槍支”
通過上文探究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存在的必要性可知,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下的罪名,其實是類型化的擁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核心的罪名,該核心即所保護的法益。而我們要探究行為人的對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是否產生認識錯誤時,也很難要求行為人對該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有一個極為準確的,合乎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認識,我們一般只要求到,行為人認識到該概念所包含的與犯罪性相關的意義或價值特征即可(江溯)。
以本案為例,按照本案中對槍支的鑒定標準,槍支是指“以火藥或氣壓為動力,利用管狀器具作為發射工具,發射金屬彈丸或其他物質,槍口比動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的槍型物”。
這里有個問題是《槍支管理法》中對于槍支的定義是“足以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喪失知覺”。而1.8焦耳/平方厘米的槍口比動能的槍,其致傷力遠低于“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喪失知覺”。換言之,縱然趙春華對于“槍支”有所認識,她能認識到的也是那種“足以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喪失知覺”的槍支,而1.8焦耳/平方厘米的槍口比動能,是完全不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者喪失知覺,據其制定者季峻表示,1.8焦耳/平方厘米的槍口比動能的槍,能對人體最脆弱的部位——眼睛造成傷害,但是經試驗證明這種致傷力甚至無法對人體的皮膚造成出血性傷害,僅僅能在人體表皮留下一個紅點。
如果如此低的致傷力能被認定為刑法上的槍支的話,那么趙春華對此不具有認識,實屬正常,因為這已經遠遠高出了社會一般人的認識范疇。同樣的,這種致傷力的槍支,確實不具有真正的社會危害性,不具有抽象危險性。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當小孩子在玩最普通的玩具槍或者彈弓的時候,大人都會囑咐說不可以對著小伙伴的眼睛開槍,但我們并不能由此強推說,大人們認識到了這種“槍形物”具有打傷人眼睛的殺傷力,認識到了公安部文件中所規定的殺傷力,從而認識到了這就是刑法規定的槍支。這實在是荒謬至極。
(三)外行人領域平行評價標準
為了判斷行為人對于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認識,我們借鑒了德國的外行人領域平行評價標準。該標準是指,行為人是否認識到法條中的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要以外行人領域的平行評價為標準。這里的外行人指的是社會一般人,平均人的標準,也即是說,如果行為人對于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理解,與社會一般人對于該構成要件要素的理解相符,但是與刑法意義上的該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含義存在顯著差別,則不能認定為犯罪嫌疑人對該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存在主觀明知,阻卻故意。
但是結合前文所述我們也會發現,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是一種較為抽象的、類型化的要素,其核心是所要保護的法益,所以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所規范的犯罪行為的核心就是法益侵害的性質及其程度。所以事實上,就算行為人無法完全精準地理解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但只要理解到了其核心意義,即其背后所蘊含的法益侵害的性質和程度,即可認為行為人已經對該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達到了明知的地步。換言之在本案中,如果非法持有槍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社會公共安全,那么趙春華只要認識到自己所持有之物會對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脅,那么便認為她對“槍支”有了一定明知。
但事實上,歸結到本案,趙春華對其所持之物連這一重意義上的認知都沒有。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槍支認定的標準實在是過低。根本達不到對社會公共安全產生危害的程度,這種認定標準之下的槍支,不符合刑法中所規定的“槍支”這一規范構成要件要素背后所蘊含的核心意義。其二,如前文所述,持有型犯罪是一種堵截性的罪名,趙春華持有這些槍型物時,主觀上沒有威脅社會公共安全的惡意,槍型物的來源也不是威脅社會公共安全的行為的結果。
綜上,趙春華對于“槍支”這一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不具有主觀明知,應當阻卻故意。
參考文獻:
[1]李翔.立場、目標與方法的選擇——以趙春華案為素材刑法解釋論的展開[J].東方法學,2017(3).
[2]劉艷紅.“司法無良知”抑或“刑法無底線”?——以“擺攤打氣球案”入刑為視角的分析[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
[3]陳志軍.槍支認定標準劇變的刑法分析[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5).
[4]高巍.論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之主觀明知[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11(3).
責任編輯: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