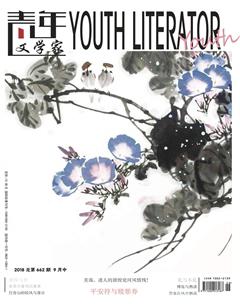佛教下劉禹錫的詩學
賈璐娜
摘 要:劉禹錫是我國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也是重要的哲學家、文學家,在詩壇上素有“詩豪”之稱。縱觀其一生,他與佛教高僧的交往貫穿他一生的各個時期。同時在佛教發展相對穩定的中唐時代,文人士大夫階層與僧尼的頻繁交往使得文人們在多方面都進行著促進儒釋交匯的努力,而劉禹錫正是其中典型。他受佛教思想及禪宗認識思維方式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因此,本文也主要通過追溯劉禹錫與佛教的淵源關系來探討他的詩學主張。他把自己對佛教禪意獨特的領悟和理解融合進詩作,為我們能夠對劉禹錫的詩歌創作特點、詩學主張以及他與佛教關系的形成契機和原因有一個詳細的認識,以期了解那個時代唐朝思想家們與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并能夠客觀看待劉禹錫創作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劉禹錫;佛教;詩學主張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6-0-02
一、劉禹錫與佛教的淵源
佛教自東漢傳入至唐代中期,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直接對東方的經濟政治生活、人文心理、文明文化有著不可忽視且深遠持久的影響。我們知道佛教一直在唐朝盛行,是因為唐代實行開放的文化政策,物質及精神文明都極其繁盛。唐朝有一種包容的心態,在其早中期各類宗教都很繁榮,諸如佛教、道教、摩尼教等等,使得長安城成為了一座國際大城市,海納百川,包容萬教。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影響下,使得唐人的思想較開闊不受束縛,精神也相當活躍,出現了詩風雄奇飄逸的李白,關注民生的杜甫,也有玄奘大唐取經等一批為法不怕犧牲、勇敢前行的人,為唐朝佛教打下了根基,注入了能量和活力。而劉禹錫生活的德宗、順宗、憲宗都是熱心崇佛的皇帝,一些文人們步入了仕途并和僧人們交往,信奉佛教也是當時普遍的現象。和劉禹錫同時期的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都信奉佛教,和佛教高僧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有開放和交流,才會讓學術更加繁榮發展,他們也為當時的時代添加了異樣的色彩。
劉禹錫與佛教高僧交往眾多。少年時的劉禹錫就十分好學,加上他本身出身于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熟讀儒家經典,瀏覽諸子百家。在其19歲時就游學長安,上書朝廷。21歲時與柳宗元同榜考中進士,同時又考中了博學宏詞科,還曾經到吳興陪侍詩僧皎然、靈澈吟詩,因而與兩位大師結識,成為好友并得到他們的指點。兩位大師非常喜歡這位聰明好學的少年,且當時的劉禹錫十分懂事,謙恭有禮,在兩位大師吟唱揮毫的時候,他就恭敬地捧著筆硯在旁邊伺候,非常虛心,絲毫沒有不耐煩,因此兩位高僧曾稱贊他“孺子可教”。這樣的一段經歷使他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為他后來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機。俗語曾說“知音難覓”,可想一生中能遇到幾個良師摯友、把酒言歡是多么慶幸的一件事,這樣的經歷在自己的生活經歷中是多么難能可貴。
貶謫時期的劉禹錫與高僧來往也頗多。第一次被貶在唐憲宗即位,由于藩鎮和宦官集團的壓力,王叔文改革宣告失敗,劉禹錫被貶為連州刺史。行至荊南又改授朗州司馬,當時被貶的共有八人,史稱“八司馬”。在其貶為朗州司馬后,慧則出行宣教,一路游歷到達朗州后會見劉禹錫,在離別時劉禹錫作詩贈慧則。詩中云:“休公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可以想到當時被貶的劉禹錫心中是多么復雜。遇見好友該是喜極而泣,可是自己因為被貶,在他鄉遇故知,心中百感交集,為自己而悲。但被貶后仍有好友來探望,這份友情怎能不讓人珍惜呢?所以劉禹錫與詩僧廣宣、慧則兩位大師的友誼相當深厚。此外在朗州期間,還有很多高僧到朗州拜訪劉禹錫,劉禹錫也專程前往朗州武陵縣的枉山拜訪會禪師,并作詩曰:“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沉痗”、“吾詩得真如,寄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覺路明證路,便門通懺悔”等一些有哲理的話語,來表明自己當時被貶謫痛苦的心情。仕途的不順,希望能得到大師的指點,為自己指點迷津,與會禪師在一起交談佛理的感受過程使自己對佛產生愈發濃厚的興趣。元和九年,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一起被召回長安,欲任南省郎。但是劉禹錫在游覽玄都觀時,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又名《玄都觀桃花》),諷刺時政招來禍端,不久之后又被貶為播州刺史。又一次被貶,又一次陷入困難境地,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因為思想的極度壓抑,心中的苦悶無處排泄,劉禹錫更加開始將佛教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與僧人更是來往甚多,因為自己之前一直接觸佛理,所以并未使自己消極、怠慢。
晚年時期的劉禹錫還與著名高僧華嚴宗第五祖宗密有過交往。劉禹錫非常欣賞宗密大師少通儒書,有政治抱負,還盛贊大師累世修行,得到了很高的智慧,對佛教理論更是堪稱一絕。劉禹錫還將宗密大師介紹給白居易認識,而白居易還與宗密大師師叔洛陽神照禪師熟識,這大概是佛緣吧。所以這樣看來劉禹錫是幸運的,一生中遇到這么多對自己有幫助的人,即使遭遇被貶,面對生活依然樂觀。
劉禹錫的一生都是與佛教相聯系的,從未斷過和高僧的往來,加之當時開放自由的社會風氣,使他的經歷離不開與僧人們的交往,從而影響了他的哲學思想和詩學思想。
二、劉禹錫的詩學主張
1.境生于象外說
劉禹錫一生交往過的僧人非常多,尤其是貶謫時因為政治仕途的不順心,常常和高僧們寄情于山水之間,談禪論道,賦詩唱和,探究天文地理,和僧人們產生佛理上的情感共鳴,讓佛學研究和自己的學術發生關系,加之共同的政治傾向使處于逆境的劉禹錫能夠得到心靈的慰藉,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面對現實,達到一種恬淡的人生境界。出于對佛教禪理的濃厚興趣,著力以禪學與詩學相溝通,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詩學理論,為后來的詩歌研究也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
劉禹錫早年就受師僧皎然的《詩式》影響,認為詩學和禪學有很多相通之處,同意“論詩如論禪”的說法,明確認識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詩者,其文章之蘊也。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認為詩的意境來自于詩人獨特的內心領悟,是要超越于語言的,而且領會詩的意境也不能完全立足于形象本身,鑒賞者也需要有內心的情感共鳴,自己的獨特想象才能夠這種“意象”融合在一起,才能走進詩人為我們創造的情景中去,而領略到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和所要向我們傳遞的情感。他認為物象、形象是實,而意境、詩味是虛,寫物象,塑造形象就是為了創造一種意境,但要準確理解意境的意義又必須跳出形象的圈子靠自己的內心去把握,所以他不僅善于創造意境,還常常調動讀者的審美思維,使主客觀和諧地融為一體。
這種在禪學啟迪下而產生的意境論影響很大,看似重在詩歌審美形象、創作規律的探討,卻沒有忽視詩歌的社會功能。這種理論主張體現了劉禹錫好學善于創新的精神,而且具有實用性,易于被接受,對詩歌發展相當有益處,也能多方面去調動讀者敏感的心理,產生心靈共鳴。
2.虛靜成詩論
劉禹錫提出要靠自己的內心領悟去領略意境,還認識到當詩人進入類似佛門禪定的虛靜狀態時,萬千景物都可以返照于心,即所謂的“虛而萬景入”。少了欲念、凡念的牽掛,便自然可以捕捉到生動的物象,快速地進入藝術構思,從而創作自己想創作的東西。其實我們仔細想想是很有道理的,我們心中的雜念多了,欲望多了,自然更多的是胡思亂想,讓我們的思緒止步不前,當把所有不必要的雜念拋開之后自然眼前一亮,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該從哪里著手。只有心中無物,萬事萬物才會進入自己的腦海中,創造一種空靈清幽的美感,這是一種特殊的審美需要,會給我們帶來心靈的愉悅,這也是創作需要。
綜上所述,劉禹錫與僧人們交往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是在政治仕途不順心、不如意的時候尋求精神寄托,事佛信佛;其二是學習佛學方法,豐富發展儒家學說,并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提出自己的主張,為后人學習提供了方法。這樣的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體現了劉禹錫身上的戰斗精神、求知精神,同時也顯露出唐、宋詩慢慢過渡的征兆。不僅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文學作品,還讓我們的思想開闊,為更好地做研究積累經驗。
參考文獻:
[1]肖瑞峰.論劉禹錫謫守朗州期間的詩歌創作[J].浙江社會科學學報,2013(10).
[2]皎然.詩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3]唐·劉禹錫·瞿蛻園校注.《劉禹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