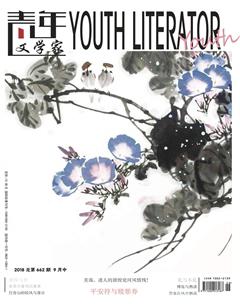德國小說《馬販子米歇爾?科爾哈斯》和《水滸傳》之比較
段云
摘 要:德國作家克萊斯特的中篇小說《馬販子米歇爾·科爾哈斯》講述的是一位商人由于法律不能維護(hù)自己的正義而選擇起義的故事,這和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有很多相似之處。本文從創(chuàng)作來源、起義原因、起義理由、招安過程和結(jié)果等方面比較其異同。
關(guān)鍵詞:克萊斯特;《水滸傳》;起義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26-0-01
德國作家海因里希·克萊斯特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馬販子米歇爾·科爾哈斯》和我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都是講述起義的敘事作品。本文從創(chuàng)作來源、起義原因、起義合法性以及招安等方面比較其異同。由于《水滸傳》人物眾多,本文只選取宋江作為比較對象。
1.創(chuàng)作來源
《水滸傳》的成書,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在宋王偁《東都事略·徽宗記》可以找到宋江起義的記載,還有其他史書如《宋史》也對此做了記載。不過,水滸傳雖然取材于歷史,但大部分都是虛構(gòu)的故事。這和克萊斯特中篇小說相似。《馬販子米歇爾·科爾哈斯》也取材于歷史上真實(shí)事件。主人公科爾哈斯以科恩商人科哈澤為原型。科哈澤1532年途經(jīng)薩克森境內(nèi)時以偷馬的罪名被容克地主的家奴斥責(zé),所騎馬匹也被奪走。后來容克地主雖然愿意歸還馬匹,但馬匹遭嚴(yán)重虐待。科哈澤提出的賠償要求被容克地主拒絕。科哈澤求助于薩克森和勃蘭登堡選帝侯也無功而返。憤怒的科哈澤于1534年宣告武力自衛(wèi)。可以看出,兩部小說都以歷史事件加工而成。不同的是,施耐庵在參考正史以外,還有對民間故事的梳理和總結(jié)。而克萊斯特則以史實(shí)為基礎(chǔ),完全憑借作家想象虛構(gòu)大部分情節(jié)。
2.起義原因異同
就起義原因來說,兩部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被逼無奈走上反抗的道路,但存在更多不同。宋江為躲避法律懲罰上梁山,他私放晁蓋,殺閻婆惜,寫反詩等行為都觸犯了當(dāng)時法律。而科爾哈斯則不同,他在“武力自衛(wèi)”之前都沒有逾越法律。科爾哈斯是“良民的楷模”,即使遭遇勒索,兩匹馬和仆人被殘酷虐待,也沒打算采用武力,而是希冀通過法律求得正義。但是容克地主使他的官司不了了之。在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情況下,他才決定用自己的力量去求正義。另外,為妻子復(fù)仇是科爾哈斯行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科爾哈斯在妻子臨死時就以決定“絕不寬宥容克”。后來薩克森選帝侯愿意給他生命和自由來換取對于選帝侯很重要的紙條,科爾哈斯卻說:“毀滅他們,這正是蘊(yùn)藏在我心底的最大愿望。”可見,復(fù)仇心理是另一個重要的起事動機(jī)。
3.起義合法性理由異同
《水滸傳》中宋江反抗政權(quán)所提出的口號是“替天行道”。儒家知識分子將理想社會稱為“王道社會”。他們主張,“道”作為最高的政治原則要優(yōu)先于作為最高政治權(quán)勢的君主,即“道高于君”。君主究竟有道或無道,其行為和權(quán)位是否具有合法性必須接受道的檢驗(yàn)。北宋年間統(tǒng)治階級倒行逆施,民不聊生,他們便行動起來,為實(shí)現(xiàn)王道而斗爭。
與《水滸傳》中以傳統(tǒng)的中國儒家思想來為起義做辯護(hù)不同,科爾哈斯以天賦權(quán)力來辯護(hù)自己行為的合法性。他在起事前的判決書中根據(jù)天賦權(quán)力要求容克賠償損失。在馬丁路德譴責(zé)他的行為后,他對天賦權(quán)力進(jìn)行闡釋。他認(rèn)為自己被人類社會逐出懷抱,是被逐出了集體的人。法律若拒絕保護(hù)公民,公民就可以拿起自我保護(hù)的棍棒。科爾哈斯的辯護(hù)有兩個思想來源。一是在中世紀(jì),在得不到獨(dú)立法庭時,武力自衛(wèi)被視為是實(shí)現(xiàn)正義的合法手段。其二是受到現(xiàn)代啟蒙思想影響,特別是英國哲學(xué)家約翰·洛克的思想。洛克在《政府論》中寫道:“國家權(quán)力是受人民委托來實(shí)現(xiàn)某種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個目的的限制,當(dāng)這一目的顯然被忽略或遭受打擊時,委托必然被取消,權(quán)力又回到當(dāng)初授權(quán)的人民手中,人們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能保衛(wèi)自己安全的人。當(dāng)政府已經(jīng)開始禍害人民,統(tǒng)治者的惡意已昭然若揭,或他們的企圖已為大部分人民所發(fā)覺時,人民就將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們的統(tǒng)治了。當(dāng)立法機(jī)關(guān)被變更時,當(dāng)握有最高執(zhí)行權(quán)的人玩忽和放棄職責(zé),當(dāng)立法機(jī)關(guān)或君主在行動上違背他們的委托,人民的這種最高權(quán)力就能體現(xiàn)出來,政府就將解體。”可以看出,科爾哈斯為自己做的辯護(hù)和洛克所闡釋的思想是一致的。
4.招安異同
兩部小說中,主人公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接受招安的。但是條件的性質(zhì)不一樣。科爾哈斯提出,只要給他通行權(quán),將曾被拒絕的狀子呈遞到侯國法庭,他就解散隊(duì)伍。也就是說,只要法律保證公民權(quán)利,他就可以放下武器。而宋江接受招安的條件是封官加爵。
另外,兩位作品中接受招安的原因也是不同的。科爾哈斯是在宗教人士馬丁·路德的干預(yù)和斡旋下實(shí)現(xiàn)的。科爾哈斯信仰宗教,馬丁·路德是“他認(rèn)識的最最德高望重的人”。經(jīng)過路德的勸說和允諾后,他答應(yīng)解散隊(duì)伍。他接受的原因是一旦法律保護(hù)個人權(quán)利,個人就得回到集體中去,也就沒有了造反的理由。而宋江尋求招安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既有隊(duì)伍壯大之后的前途考量,也有統(tǒng)治階級的利誘,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招安可以滿足宋江早已有之的建功立業(yè)心理。
參考文獻(xiàn):
[1]施耐庵.水滸傳.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
[2]約翰·洛克.政府論.商務(wù)印書館.1964.
[3]趙蕾蓮.論克萊斯特中篇小說的現(xiàn)代性.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2010年4月 S8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