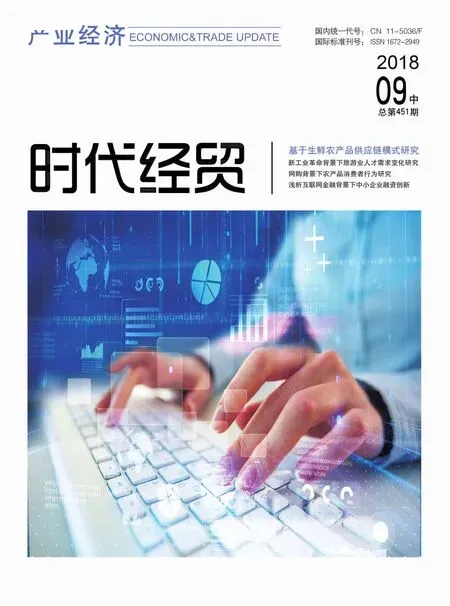國內外盈余質量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孫金平
一、影響盈余質量的企業內部因素綜述
(一)股權結構
股權結構作為公司治理的基石,對企業的經營與財務行為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從而進一步對盈余質量產生重要作用。國外研究認為,對管理者持股(Warfield etc,1995;Yeo etc,2002)、機構投資者持股(Do-brzynski etc,1986;Coffee,1991;Jiambalvo,2002)和盈余質量的關系有不同的甚至是互斥的結論,但都認為股權集中程度越高盈余質量越低的結論(La Porta etc,1998;Fanand Wong,2002)。喻凱、徐琴(2010)對我國上市公司股改后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后得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盈余質量的結論。張正國(2010)提出以控制權競爭度來衡量前五大股東股權的均衡度,認為股權集中度與盈余質量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股權集中度相對集中且分布較為均衡的企業具有更高的盈余質量。王化成、佟巖(2006)也認為,第一大股東以外的其他股東的制衡能力越強越能夠提高企業盈余質量。
(二)董事會
作為企業的決策機構的董事會,毫無疑問在公司治理中十分重要。Deehow,Sloan&Sweeney等(1996)認為,兩職合一以及董事會規模的擴大會導致盈余質量的下降。Beasley(1996)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例的提高以及任期的延長可以提高公司盈余質量。Biao,Wallace&Peter(2003)認為董事會會議次數的增加會降低企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而董事會中增加具有財務背景的專業人員也可以有效制約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為。楊繼偉、卜華白、劉純(2011)指出,不同的最終控制者導致董事會相關因素對盈余質量產生不同的作用效果,要區別是否是國有企業。從屬董事會、負責財務信息披露及內部控制的監督的審計委員會與盈余質量存在重要聯系。Ronald,Mansi&David(2004)、李昊(2010)認為設立審計委員會的公司其盈余質量更高,因為審計委員會發揮了其監督與規范的作用。而Beasley(1996)研究后得出,審計委員會的存在不會顯著影響財務舞弊的可能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外部董事比例也是如此。洪劍峭、方軍雄(2009)發現盈余質量本身較高的公司更傾向于設立審計委員會,但反之的作用效果還有待討論。
(三)經理層
由于代理問題的存在,經理層可能由于受到業績壓力或出于自利動機進行盈余管理。Yeo,Tan&Ho(2002)認為管理者持股與盈余質量存在非線性關系,這與管理層持股比例有關。武曉玲、杜國柱、翟明磊(2010)認為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激勵以貨幣激勵等短期方式為主,導致高管通過盈余管理提升業績,完善激勵方式可以減少高管的盈余操縱行為。毛洪濤、沈鵬等(2009)認為CFO薪酬與企業盈余顯著正相關。另外,也有學者發現公司高管特征也會對盈余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高層管理者在年齡(Donald&Phyllis,1984)、性別(Krishnan&Parsons,2008;張會麗、張然、林景藝,2010)等方面的異質性導致對盈余質量產生影響,影響程度與方向和公司所處的國家、地區等背景因素有關。
(四)內部控制
強化內部控制不僅可以提升公司經營活動效率,也是資本市場對公司的必然要求。Chan,Farrell&Lee(2005)發現內部控制薄弱的公司會通過提高其操縱性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張龍平、王軍只、張軍(2010)認為,內部控制鑒證可以提高注冊會計師對內部控制的關注,減少管理當局利用內控漏洞進行盈余操縱的機會。Ashbaugh,Collins&Kinney(2008)指出,審計師對內控存在缺陷的公司進行內控的指導和矯正后,這些公司的盈余信息質量有所提高。佟巖、徐峰(2013)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內控效率與盈余質量之間相互促進與影響,內控效率的提高可以顯著減少會計信息錯報和盈余管理行為。
二、影響盈余質量的企業外部因素綜述
(一)相關政策、法規

Phillips,Pincus&Rego(2003)指出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之間存在的差異(如遞延所得稅等)可能給管理當局留下盈余操縱的空間。周中勝(2009)的研究也支持以上結論,認為這種差異的存在使得盈余持續性下降,降低了盈余信息的相關性。Watts(2003)認為會計管制是提升盈余質量的重要力量,美國FASB的會計管理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穩健性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貢獻。另外,普通法國家的盈余質量要遠遠高于大陸法國家(Ball、Kothari、Robin,2000)。葛家澍(2002)則認為,高質量會計準則并不一定能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但會計準則在防范盈余管理方面起著重要的角色。劉曉華、王華(2010)通過研究我國會計準則向國際會計準則趨同后,得出這種趨同使得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質量得到了提高。
(二)政府干預行為
在我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比較普遍,地方官員也可能出于對政績表現的考慮對企業的會計信息產生干擾。Bushman,Piotroski&Smith(2004)研究認為,公司對外公布的財務信息透明度與政治經濟行為有關,政府官員會促使信息透明度下降以掩蓋其干涉行為。朱茶芬、李志文(2009)和翟華云(2010)對我國上市公司數據的實證研究支持Bushman等的研究結論,認為減少政府干預可以保證盈余信息質量的提高。張傳虎(2011)從政府行為研究得知,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等對一些上市公司進行了操控,對企業盈余信息和盈余穩健性造成了負面影響,降低了盈余質量。
(三)機構投資者
相較于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更有動力介入企業管理,對被投資單位進行監督。但現有研究認為,機構投資者選擇“用手投票”還是“用腳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對盈余質量產生影響。Chung,Firth&Kim(2002)認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可以抑制管理者對企業的應計利潤的操縱。而楊繼偉(2010)認為目前我國情況則恰恰相反,因為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目的更多的是出于短期獲利或戰略聯盟而并非長期合作的考慮,因此其持股比例的提高反而導致企業盈余質量的下降。黃郡(2006)、Mangenacal(2008)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盈余質量的相關性并不明確。
(四)外部審計及其他因素
有效的外部審計能夠有效限制企業管理者的不規范行為,從而提高企業盈余質量(李仙、聶麗潔,2006;陳朝龍、李軍輝,2013)。但唐妤、鄭婷婷(2010)則認為審計費用對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并不顯著。Erickson&Wang(1999)發現,在并購前公司會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而這種對收入調增的盈余管理程度與其并購的相對規模呈正比。Gordon和Henry(2003)通過大樣本數據也支持這一觀點。洪劍峭、方軍雄(2005)則發現盈余的價值相關性隨著關聯銷售比重增加而顯著表現為一種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關聯交易的存在往往對盈余質量產生消極的影響。(鄭國堅,2009)
三、小結
從上述綜述來看,對企業盈余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可謂內外結合、多方面入手,并且得到了有效的研究結果。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視野將會不斷被開拓出來,如地方政府官員作為影響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其個人特征是否會對企業盈余質量造成影響?這些都有待后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