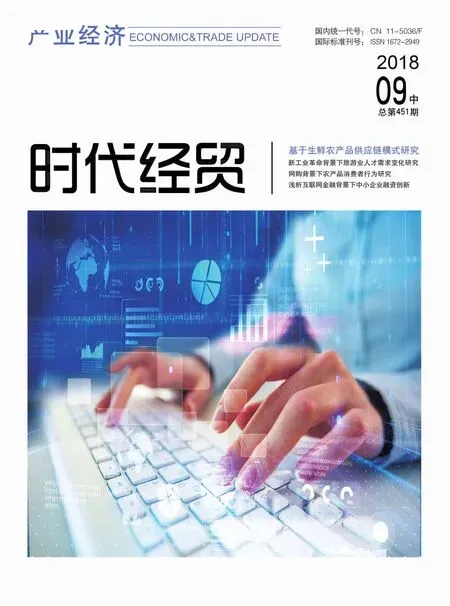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劣勢的原因及對策
朱雪萍 王炳才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服務業快速發展,已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進出口總量逐年上升,但貿易逆差較大、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產品多以輸入為主等貿易結構性缺陷卻愈演愈烈。[1]2016年服務貿易總逆差達2409億美元,其中生產性服務貿易的逆差約占20%左右,是服務貿易結構不平衡的突出部分。因此本文對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的原因進行研究,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對我國實現貿易高端化提供一點幫助。
二、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競爭力水平分析
劉榮欣[2]提出用某種商品的進出口與貿易總和之比,即貿易競爭指數(TC)分析出口競爭力的方法,計算公式如下:TC=(EX-IM )/(EX+IM)
其中,EX代表我國生產性服務的年度出口額,IM則表示年度進口額。當TC 指數> 0時,表示我國生產性服務處于貿易順差,越接近于1,貿易競爭優勢越大;反之TC < 0時,則表示競爭力較低,處于貿易競爭劣勢。
由下圖可以看出,我國生產性服務的貿易競爭優勢在2000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出現了快速上升的過程(2000年到2008年),主要是由于加入世貿后國家極力主張以出口拉動經濟發展,生產性服務出口的增長率遠超過進口的增長率水平。但由于金融危機的發生,全球性的需求進口減少,國內的出口數量下降,導致2009年我國貿易競爭指數大幅度降低。此后數年,我國依靠進口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向其他國家學習并創新來促進計算機信息技術方面的發展,以知識和技術為基礎的生產性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出口額快速增長,貿易逆差減少,貿易競爭優勢隨之上升。但總體而言我國的生產性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是非常薄弱的,近十幾年來的TC指數一直處于小于0的水平,處于完全的競爭劣勢。

圖1 2000-2016年我國生產性服務進出口額及貿易競爭優勢的變化過程
三、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劣勢的原因
(一)服務貿易結構失衡,生產性服務出口規模較小
相對于我國高度發展的工業制造業貿易來說,服務業,尤其是知識技術密集的生產性服務業貿易起步較晚,增長緩慢,出口額占比較小。出口規模與競爭力的變動是一個雙向的關系:出口規模的擴大會通過規模報酬、技術溢出效應等途徑降低比較成本,提升我國生產性服務的比較優勢;相反,競爭力的提升說明我國生產性服務具有比較優勢,即比較成本較低,出口增加。對比不同國家的數據來看:2016年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3.5%,競爭力水平為-0.2,處于競爭劣勢。同樣作為亞洲新經濟體的韓國與新加坡則發展的較為迅速,生產性服務的出口規模分別為7.9%、17.6%,貿易競爭指數分別為0.11與0.10,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而在發達國家里兩者正相關的關系更為明顯。美國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占比約為11%,TC指數約在0.06的水平。競爭優勢最明顯的則是英國:生產性服務的出口占比23.5%,TC指數則高達0.46,顯示出較高的競爭優勢。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生產性服務的出口額占比與競爭力顯示出強烈的正相關關系,即貿易規模越大,國際競爭力越高。
(二)我國生產性服務產品技術含量低,出口復雜度較弱
出口復雜度是指某一類出口的產品中所包含的技術含量,是產品質量的度量指標。[3]出口復雜度的提升可以顯著地正向推動我國貿易競爭優勢增加,對于提高生產性服務的出口比例,改善貿易逆差,優化我國高端貿易結構的意義極為重大。總的來說,出口規模從出口數量角度解釋了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水平較低的原因,而產品的出口復雜度則是從出口服務質量方面對競爭力進行研究。2001年我國生產性服務的出口復雜度約為17286,2016年增長到32360,年增長率為3.1%,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對于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性服務行業的出口而言,“質”與“量”的同期和諧發展才是改善我國出口結構、提升產品附加值的最佳途徑。
(三)服務業市場開放水平較低,國外直接投資相對于工業制造業而言少之又少
從全球服務業發達的國家的數據可以看出,影響服務業開放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國外直接投資。[4]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各國建立分公司、進行直接投資的寵兒,但是事實上我國的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制造業等成熟領域,流入服務業的投資又集中在房地產業,高端生產性服務的外資投入占比極低。僅就2016年的數據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使用金額約為1260億美元,其中投入制造業的金額約為355億美元,占比為28.2%;而新興的生產性服務業卻只占用了20%,抑制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及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高。
四、提高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的建議
隨著勞動成本上升和資源稟賦減少,我國傳統服務貿易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優勢正在逐漸消失,為了促進服務貿易結構升級和產業優化,必須大力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因此,本文分析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競爭力低下的原因后,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一)積極應對服務貿易結構失衡的問題,有針對性地促進生產性服務的出口,減少服務貿易逆差
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刺激著生產性服務的更新,我國應緊緊抓住信息時代帶來的機遇,擴大服務業的貿易規模,降低平均成本。鼓勵國內生產性服務企業勇于創新,開發新產品,加快技術研發成果向實用商品的轉化,為企業提供必要的資金幫助和優惠政策,保證我國生產性服務的出口增速穩定健康地增加。同時應積極推進全球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服務貿易壁壘,促進世界服務貿易分工,擴大出口市場。因此我國應謹慎對待,加大對服務業的扶持,促進我國服務業出口,尤其是新興的生產性服務穩步增長。
(二)提高生產性服務技術含量,發展高精尖型服務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追求出口額快速增長的“粗放型”貿易模式,使得新型服務行業的技術水平發展緩慢。我國應鼓勵服務業“質”與“量”同時增長,吸引海內外的高機能人才,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合適的環境與條件,提升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的可貿易性。理論上,出口復雜度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生產性服務的出口占比和我國人均GDP兩種方式實現。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增速保持穩定地中高速增長水平,甚至超過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我國經濟投入的重點依然是工業領域,考慮到生產性服務的高附加值低污染等特點,國家應加大對其經濟投入及技術支持,提高生產性服務產品的技術含量,使其成為新的經濟發展熱點領域。
(三)放寬部分生產性服務的外資準入條件
相對于工業和制造業領域,我國服務市場的開放程度較低,外資實際使用值占比少,無法充分發揮國外資本和先進技術的紅利。我國應逐步有計劃地放開部分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服務行業,如金融、保險等領域,提供相應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有目的地投入到生產性服務行業,促進資源有效率利用。
(四)促進相關產業的聯合發展
生產性服務作為制造業的中間投入,關系著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共同發展,貨物貿易的增加必然會引起相應中間投入的服務貿易量。而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失衡以及不夠聯動的格局制約著生產性服務的發展。以交通運輸業為例,作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三大支柱產業之一,運輸服務越繁榮,越容易通過規模效應降低生產成本,貨物貿易的競爭力增加,促進貨物的出口;相輔相成地,貨物貿易越發達,則作為中間投入的交通運輸服務需求增加,生產性服務出口規模隨之上升。政府應該做好管理與服務工作,為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協同發展提供合適的環境與幫助,鼓勵具有高比例生產性服務作為中間投入的貨物貿易出口,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