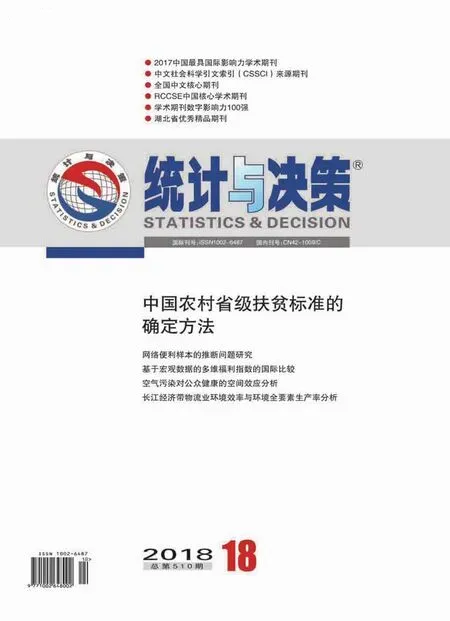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對縣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
何 燕
(湘潭大學 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0 引言
湖南作為農業大省,城鎮化發展一直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部地區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湖南省總面積21.1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2.2%,居中部第1位;有漢、土家、苗、侗、回等50多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0%。2016年湖南省人均GDP為45063元,城鎮化水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52.75%,二者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由于中部地區多為農業大省,縣域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湖南省縣域經濟發展中城鎮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與教訓可以為中部地區崛起提供參考和借鑒。因此,本文選取2010—2015年湖南省124個區、縣級市、縣的縣域面板數據對城鎮化、產業結構與縣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
1 研究方法
面板數據(Panel Data)模型是建立在面板數據之上、利用平行數量分析變量之間相互關系,并對其變化趨勢進行預測的計量模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αit表示截距項為k×1維參數向量;yit表示被解釋變量,為1×k維解釋變量向量;t表示不同的時間,i表示不同的個體,μit為隨機擾動項,且獨立同分布 μit~IIDN(0,σμ2)。面板數據模型包括混合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
混合模型模型定義為:

其中,α 表示截距項,β=(β1,β2,···,βk)'為 k×1維參數向量;yit表示被解釋變量,為1×k維解釋變量向量;t表示不同的時間,i表示不同的個體,μit為隨機擾動項。
固定效應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包括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個體時間點雙固定效應模型三種類型。
時間固定效應模型是指對于不同的時間截面存在不同截距的模型。時間固定效應模型的定義為:

式中,yit表示被解釋變量為1×k維解釋變量向量;αt是隨機變量,表示對于T個截面有t個不同的截距項,且其變化與有關;β=(β1,β2,···,βk)'為 k×1維參數向量,對不同的個體回歸系數相同;μit為隨機擾動項。

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定義為:
其中,yit表示被解釋變量表示1×k維解釋變量向量;αi是隨機變量,表示對于i個個體截面有i個不同的截距項,且其變化與有關,β=(β1,β2,···,βk)'為k×1維參數向量,對不同的個體回歸系數相同;μit為隨機擾動項,滿足經典計量經濟模型的基本假設,μit~IIDN(0,σμ2)。
個體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定義為:

式中,yit表示被解釋變量,表示1×k維解釋變量向量;αi是隨機變量,表示對于i個個體有i個不同的截距項,γt是隨機標量,表示對于T個截面有t個不同的截距項,二者的變化與有關;β=(β1,β2,···,βk)'為k×1維參數向量,對不同的個體回歸系數相同;μit為隨機擾動項。
隨機效應模型的定義為:

其中,yit為被解釋變量,為1×k維解釋變量向量;αt是分布與無關的隨機變量,β=(β1,β2,···,βk)'為k×1維參數向量,對不同的個體回歸系數相同;μit為隨機擾動項。
對于給定的面板數據,應該用Hausman檢驗來確定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如果豪斯曼檢驗結果接受原假設,則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如果拒絕原假設,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面板數據估計。
2 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
根據傳統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經濟增長決定于資本(Capital)和勞動力(Labor)投入以及技術進步(A)。為構造計量模型經驗分析城鎮化進程(Urbanization)、產業結構(Structure)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假定規模報酬不變,建立如下擴展模型:

目前,中國仍處于體制轉型過程之中,除城鎮化水平將引致經濟增長外,同時考慮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加入政府的干預程度(Expenditure)作為控制變量構建計量模型。為估計城鎮化進程對于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用人均GDP(perGDP)代表水平經濟增長,引入控制變量向量,并對擴展的生產函數兩邊同時取對數,得到如下計量回歸模型:

其中,i表示湖南省124個區、縣級市和縣,t表示時間,β為待估參數。ui及vit分別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差異和表示隨機擾動項。變量的選取的定義見表1,所有變量取自然對數。

表1 變量選取及定義
經濟增長(perGDP),用人均GDP來表示縣域經濟增長情況,反映個縣域經濟發展及增長質量情況;勞動力投入(Labor),用全社會從業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資本投入(Capital),由于官方發布的數據沒有提供湖南省各地區的資本存量數據,本文采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資本投資規模越大表示GDP中用作物質資本積累的越多,從而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城鎮化水平(Urbanization),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以年末常住人口統計口徑)的比重來表示。產業結構(Structure),本文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以各區、縣級市、縣的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Secondary)、第三產業總產值與第二產業總產值之比(TRY/SEC)兩個變量作為產業結構指標來反映產業結構的優化程度。工業化會促進人口的空間轉移,是促使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密切聯系的重要方式,第二產業可以有效反映我國的工業化進展情況。在新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第三產業的增長率比較快。因此,用第三產業產值(TRY)與第二產業產值(SEC)之比(TRY/SEC的比值越大,經濟服務化的程度越高)作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度量指標,反映經濟結構的服務化傾向。
為控制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將第一產業和政府的干預程度作為控制變量納入計量模型之中。第一產業(Primary),用第一產業總值占GDP的比重來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第一產業的比重最大。由于湖南是農業大省,此指標主要度量農業在目前縣域經濟中的作用。為控制政府行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政府干預程度(Expenditure)被納入模型中,其數值用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占名義GDP的比重來表示。
本文采用2010—2015年湖南省124個區、縣級市、縣的面板數據對城鎮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湖南省統計局以及《湖南統計年鑒(2011—2016)》。由于2010年湘潭市統計口徑的差異,《湖南統計年鑒2011》公布的經濟增長指標(包括地區生產總值、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GDP增長率(上一年=100%)和人均GDP)匯總為湘潭市總體數據,為統一口徑,需要把湘潭市的經濟增長指標區分為雨湖區和岳塘區,相關數據來自湘潭市雨湖區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和湘潭市岳塘區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為了更直觀地呈現各經濟變量之間的變化趨勢,描述性統計使用取對數前的數據。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從各變量的統計數據來看,一產、二產、三產和政府干預的均值、中值的結果基本一致;人均GDP、資本和城鎮化率的均值大于中位數;而勞動力投入正好相反,這符合湖南作為農業大省的省情,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第一產業,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占比相對較小。湖南省人均GDP最大值193699元,最小值6406元;城鎮化率最大值100%,最小值19.37%。從這兩個變量可以看出,湖南省經濟發展程度和城鎮化水平均存在明顯差異,人均GDP最大值大約是最小值的30.24倍,城鎮化水平最大值是最小值的5.16倍。產業結構指標也存在較大差異,第二產業最大值為87.205%,最小值僅為1.5823%;三產/二產的最大值為94.733%,最小值10.296%。控制變量政府干預程度最大值是67.901%,最小值是1.637%,說明政府資源在湖南省分配不均衡,存在地區差異。

表2 湖南省124區、縣、縣級市各變量描述統計
3.2 回歸結果及解釋
考察城鎮化、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豪斯曼檢驗,模型不符合隨機效應檢驗的估計條件,因此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對湖南省全樣本進行逐步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回歸結果顯示,城鎮化水平、第二產業和產業結構升級(三產/二產)的估計系數均正向顯著,說明城鎮化水平與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都存在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第二產業發展以及產業結構升級(三產/二產)均有利于經濟增長。在逐步添加控制變量的過程中,城鎮化水平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估計系數符號基本一致,說明繼續推進城鎮化進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結論是穩定的。以上結果基本支持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結論。
實證結果表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縣域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會促進社會較快的發展,同時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全國來看,城鎮化對于湖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明顯不足。模型(5)結果顯示,湖南省城鎮化率每提高1%,會促進湖南省人均GDP提高0.9973%;但全國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維持7.1%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加快城鎮化進程對湖南縣域經濟的增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是發展湖南縣域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產業結構指標中,第二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正向顯著,第二產業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促進人均GDP提高0.5434個百分點,說明第二產業的發展是推動縣域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應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促進工業向高端化、高新化、“兩型”化、規模化方向發展。產業結構升級(三產/二產)與縣域經濟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但相比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對縣域經濟的影響較小(0.3047)。第三產業作為未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南省第三產業的比重總體上是呈上升的趨勢,由2010年的39.3%上升至2015年的43.9%,但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然偏低。第三產業傳統行業所占比重偏大以及新興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縣域經濟增長。

表3 湖南省124區、縣、縣級市全樣本回歸結果
模型(3)考察第一產業對縣域經濟的影響,第一產業估計系數顯著為負,第一產業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率偏低。這是由湖南省農業劣勢地位,農業經濟、農業金融等農業本身問題所決定的。隨著產業結構調整,湖南省第一產業的比重明顯下降,由2010年的14.7%下降至2015年的11.5%,但仍高于全國水平。湖南是農業大省,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慢以及農業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弱使得農民增收的步伐緩慢。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較低、現代農業發展緩慢是阻礙縣域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在模型(5)中加入政府干預變量,結果顯示政府干預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目前湖南省縣級政府的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因此,在滿足公共服務需要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應該根據本地區特點采取差異化的財政支出政策,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促進縣域經濟的快速增長。
可以注意到,逐步回歸結果顯示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為正。雖然湖南省農業人口和農業勞動力在縣域總人口和社會勞動力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湖南省屬于勞動力密集型地區,勞動力投入對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突出。此外,固定資產投資和縣域經濟增長水平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十二五”期間,湖南省充分發揮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規模迅速擴大,但投資結構有待進一步改善。對投資驅動過度依賴容易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湖南縣域經濟的增長。
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及產業結構調整將帶動縣域經濟增長,同時經濟增長也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速。如果經濟增長與城鎮化之間存在變量的內生性,將會使上述回歸結果受到質疑。為此,本文將所有變量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運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對上述模型進一步回歸,結果見模型(6)。二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與固定效應模型一致,因此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4 結論及建議
本文以湖南省為例,采用2010—2015年湖南省124個區、縣級市、縣的面板數據分析中部地區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城鎮化進程有助于促進湖南省縣域經濟的增長。產業結構指標中,第二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正向顯著;產業結構升級(三產/二產)與縣域經濟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關系,但相比于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對縣域經濟的影響較小。湖南省第三產業的比重總體上是呈上升的趨勢,但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然偏低。第三產業傳統行業所占比重偏大以及新興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縣域經濟增長。湖南省作為中部地區的典型,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促進中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1)促進人口集聚,有序推進城鎮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拆除城鄉壁壘,加速中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促進中部地區農村人口合理向城鎮流動。同時,促進中部地區城市群的發展,培育新的城市群,促進形成以縣域城鎮為主要載體的新經濟增長極。
(2)優化產業結構,加強自主創新。中部地區經濟主要是粗放型增長方式,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工業化進程推動不足,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向第三產業演進乏力。要加快中部地區工業化進程,促進產業產業結構調整,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先進制造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業整體技術水平;大力發展以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解決服務業市場主體發展滯后、發育不完善等問題,發揮市場對服務業的引導作用。
(3)加強對縣域產業發展的協調和支持。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加強協調指導,支持各類優勢企業進入縣域發展特色產業,對縣域經濟支柱產業、特色產業項目給予專項支持;加強中部地區之間、縣域中心城市之間的經濟合作與交流,支持欠發達地區省級產業集聚區的建設,鼓勵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和勞動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