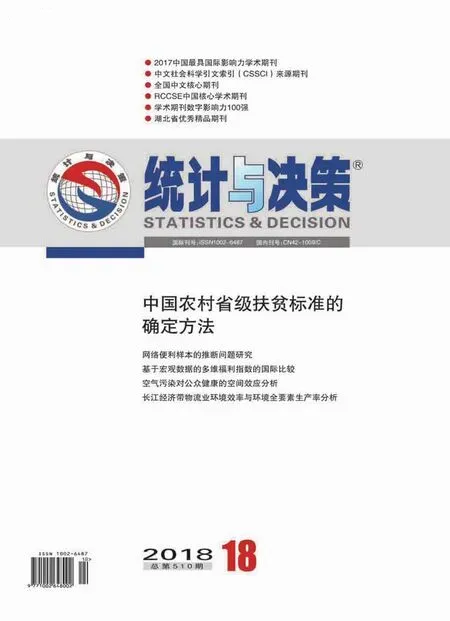貨幣政策與房價波動關系的實證分析
鄭世剛
(湖北經濟學院 物流與工程管理學院,武漢 430205)
0 引言
1998年我國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房價上漲”和“政策調控”始終是房地產市場的主旋律。尤其是200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表現出三大顯著特點:一是與之前相比,不管是調控力度還是政策數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密集使用;二是房價大幅上漲,期間全國商品房平均價格累計上漲了195%(以1998年為基數),房價陷入了“越調越漲”的怪圈之中;三是從70個大中城市以及10大重點城市的月度數據來看,我國房價表現出明顯的波動特征。
對于我國房價的持續上漲和大幅波動,許多學者提出這是政策環境影響的結果[1,2],并認為貨幣政策是其重要原因[3]。國內學者大都認為貨幣政策應對資產價格做出反應[4,5]。自Friedman 開始,經過Svensson(1997)[6]等的發展,貨幣政策建立了包括政策工具和目標函數的反應規則,構成了央行調控的一般框架。但選取哪些政策工具,目前并沒有一致的結論,國內大量學者傾向于利率規則[7,8],而近年來許多學者認為應建立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混合規則[9,10],從而建立“多目標、多工具”的貨幣政策框架及規則體系。
雖然我國房價波動對貨幣政策實施的影響是明顯的,但國內已有文獻中將房價納入貨幣政策反應規則的研究,尤其是我國當前貨幣政策是否對房價波動做出了反應及其立場如何的實證研究是缺乏的。因此,本文將針對這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方面構建引入房價波動的貨幣政策反應規則模型,并推導最優貨幣政策工具反應規則;另一方面實證分析貨幣政策工具對房價波動的反應及其立場。
1 貨幣政策反應規則的模型構建與推導
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房價波動納入貨幣政策規則越來越具有現實性。一是房地產日益顯著的金融屬性,使得房價波動對金融體系以及貨幣政策的實施可能產生重要影響;二是房地產在我國家庭資產中占有較高比例,具有顯著的財富效應和抵押效應,加上房地產業的關聯效應,從而房價能夠通過不同的傳導機制對社會總需求形成影響,并最終影響到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三是房價的不斷上漲引起市場相對價格的變化,導致更多的資源被引入房地產領域,可能帶來資源錯配危機。在如何引入房價問題上,貨幣政策是關注而不是盯住房價對我國而言是較為現實的選擇,即采用間接反應觀的做法。因此本文引入房價波動作為貨幣政策規則目標函數的約束條件,構建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兩種貨幣政策反應規則模型,并推導出含有房價因素的最優反應規則。
1.1 利率反應規則
泰勒規則是最常用的利率規則之一,描述了短期利率對通脹和產出的反應。對于大多數封閉經濟模型,泰勒規則可能是最優貨幣政策,其形式上的簡潔性能夠避免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利率政策的設計還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利率平滑。理性預期假設下,長期利率根據預期短期利率變化而調整,政策制定者無需大幅調整短期利率就能熨平經濟波動。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平滑的泰勒規則能夠更好地擬合各國實際經濟數據;二是規則前瞻性和后顧性。前瞻性基于預期,后顧性則基于當期和滯后數據,雖然許多學者傾向于使用前瞻性規則,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這一規則可能具有重大的理論缺陷。而后顧性能避免自我實現機制導致的宏觀經濟波動,保證價格水平的確定性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將包含平滑的利率規則表示為:

其中,各變量均為偏離值,it、it-1分別為t期和t-1期利率水平與長期均衡利率的偏離,πt-1為通脹率與目標通脹率的偏離,xt為產出缺口與長期均衡產出的偏離,βπ、βx分別為通脹系數和產出缺口系數,ρ為平滑系數,
假設宏觀經濟為封閉型,利率政策以通脹和產出為目標。首先在加速型Philips模型約束(式(2))下,使央行的目標函數最小,損失函數表示如式(1):

δ為央行貼現率,μ為產出與通脹目標的相對權重。其次在總需求方程(式(3))中引入房價,用變化率p表示,借鑒Blanchard和Watson(1982)的理性預期模型,在房價方程(式(4))中引入理性預期刻畫非經濟基本因素b對房價波動的影響,以及房價波動的“自我積累”特征。

νt、ε、η為外部沖擊,均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常數的正態分布,式(1)至式(4)構成了利率規則反應函數模型。
接下來綜合利率規則的約束條件,將房價方程和Philips方程代入總需求方程計算得出:

可簡寫為:

對損失函數(式(1))兩邊取期望值,經過一系列推導計算,得到最優利率反應規則為:

式(5)中,d<0。
從式(5)中可以得到兩方面的解釋,一是假設不考慮房價波動對總需求的影響,即β3=0,則產出缺口、通脹率的系數將變大,意味著利率的變動幅度會增加,并對政策目標的實現形成不利影響。因此可以認為將房價波動納入利率規則,更有利于利率自身的穩定,從而減少對產出和通脹的沖擊;二是利率規則未引入房價波動時,非經濟基本因素b對總產出形成直接沖擊,而房價波動的引入減弱了這一影響。并且由于房價作為中間媒介的緩沖,這些沖擊同樣降低了利率的變動幅度,從而增加了利率規則的可靠性和穩定性。
將最優反應規則代入包含平滑的規則方程,可以得出平滑利率規則的反應函數為:

簡化為:

可以看出,在產出方程中加入房價波動作為損失函數的約束條件,利率反應規則將包含房價波動,利率在對產出和通脹做出反應的同時,也應對房價波動做出反應,并且也應對產出缺口、通脹率以及自身滯后項做出反應。
1.2 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
雖然許多學者主張貨幣政策應從貨幣供應量規則轉變為利率規則,但從我國實踐來看,由于利率市場化滯后,利率規則的基礎條件并不完全具備,貨幣供應量在調控宏觀經濟中仍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5],2008年以來的政策調控軌跡也反映了這一點。類似于利率規則的分析思路和做法,將包含平滑的貨幣供應量規則表示為:

采用與利率規則相同的模型構建方法,經推導計算得到最優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為:

與最優利率反應規則的表達式基本相同,區別在于產出和非經濟基本因素的系數不同,式(7)中b的系數符號與式(5)相反。與利率規則的分析相似,從式(7)中也可以得到相似的解釋。納入房價波動后,產出和通脹的系數變小,更有利于貨幣供應量自身的穩定,同樣會降低非經濟基本因素對總產出的沖擊,從而降低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幅度,不同的是,作用方向相反。
繼而,得到包含平滑的貨幣供應量反應函數為:

簡化為:

同樣可以看出,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將包含房價波動,在對產出和通脹做出反應的同時,也應對房價波動做出反應,并且也應對產出缺口、通脹率以及自身滯后項做出反應。
2 實證分析
2.1 方法選擇
根據上文的分析,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模型的解釋變量中包含了產出缺口、通脹率以及自身的滯后項,可能導致解釋變量的聯立內生性問題以及被解釋變量滯后項與誤差項之間的相關性問題,造成結果有偏和非一致。最小二乘法、極大似然估計法等難以得到可靠的估計結果,相比之下,廣義矩估計法(GMM)允許模型存在異方差和相關性,當解釋變量存在內生性時,可通過工具變量加以解決。因此本文采用GMM模型進行分析。
2.2 變量說明和數據處理
選取2008—2017年的月度數據,涵蓋了過去十年的市場變化,在保證樣本量的同時,也能夠避免周期性因素的影響。由于我國銀行貸款利率調整較少,與解釋變量可能難以產生穩定的關系,因此本文使用7天銀行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并與同期通貨膨脹率相減得到實際利率。貨幣供應量采用名義值除以CPI得到的實際貨幣供應量作為替代變量。通脹率采用CPI定基數據,以2007年12月為基期。
產出和房價分別采用產出缺口率和房價偏離率表示。由于統計局發布的GDP為季度數據,不能直接利用,首先使用X12法進行季節處理,其次利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月環比增速作為GDP增速的替代值,計算出不同月度的GDP。平均房價由商品房銷售額和銷售面積計算得到,同樣需要進行X12季節處理。最后使用HP濾波法分離出潛在GDP和均衡房價,從而求出產出缺口和房價偏離率。另外,貨幣供應量也采用X12法進行季節處理,所有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和中經網。
2.3 統計描述
如表1所示,各變量的均值與中值表明樣本數據并無異常值,被解釋變量呈右偏特征,解釋變量均呈左偏特征。偏度、峰度和JB統計量以及P值均顯示,除貨幣供應量,其他變量都接近于正態分布,表明貨幣供應量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

表1 各變量統計描述
2.4 估計結果與分析
GMM方法在于根據模型和數據得到一系列矩條件,然后求解滿足條件的系數。GMM估計的首要條件是運用工具變量得到相應矩條件方程,通常選取變量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對應于被解釋變量,分別選取一年期貸款利率和M1增長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并選取CPI、產出缺口和房價增長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兩個模型的工具變量。由于模型中只有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階項為內生變量,因此解釋變量自身也可以作為工具變量。GMM分析中,模型的優劣并不取決于R2和F統計量,而是取決于是否存在過度識別,即Hansen檢驗。
首先進行自相關檢驗,由于解釋變量中含有被解釋變量滯后一階項,因此DW檢驗失效。如表2所示,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Q和LM檢驗表明不存在自相關性,ADF單位根檢驗顯示數據是平穩的,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Hansen過度識別檢驗表明工具變量具有較好的外生性。因此,數據具有較好的平穩性,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表2 數據自相關和平穩性檢驗結果
為分析貨幣政策是否對房價波動做出反應,表3以7天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M2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報告了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模型包含房價(模型Ⅰ)和不包含房價(模型Ⅱ)的情況。估計結果表明,4個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表3 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估計結果
第一,表3的結果顯示,不管是利率反應規則還是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納入房價波動的模型Ⅰ與不包含房價波動的模型Ⅱ相比,各解釋變量的系數并沒有發生明顯區別,包括大小、符號和顯著程度。7天同業拆借利率和M2對房價波動的反應系數分別為正和負,但絕對值都比較小,并且均不顯著。如前所述,貨幣政策應對房價做出反應,從而減小經濟增長和物價的波動,但分析結果表明貨幣政策的兩個工具均未對房價波動做出有效反應,即使有,也非常微弱。這與文獻[11—13]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即我國沒有將房價作為貨幣政策直接操作的依據。
第二,7天同業拆借利率和M2均對產出缺口和通脹率做出了顯著反應,2008年以來的10年中,我國貨幣政策仍以傳統調控目標為核心,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為保持宏觀經濟和物價的穩定。但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對通脹率的反應更為充分,即對物價的穩定更為關注,7天同業拆借利率和M2的系數均顯著為負,絕對值分別為0.68和0.94,M2的影響效應更為明顯。從不同政策規則的反應系數絕對值來看,M2對產出缺口和通脹率的反應都要優于7天同業拆借利率。與利率相比,M2對經濟變量的解釋能力高于其他變量,央行更傾向于以M2為貨幣政策的中介工具,這與文獻[5]和文獻[14]的研究結果基本相似。這也比較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雖然許多學者主張貨幣政策應由數量規則轉向價格規則,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仍主要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的信貸渠道,利率規則的傳導機制并不通暢。從政策實踐來看,2008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調整最為頻繁,僅2011年和2012年兩年內,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就高達12次。這一時期也是房價持續上漲的時期,由于房地產的投資收益遠高于貸款利率,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而同期M2在未對房價進行反應的情況下,累計值從2008年的42萬億增至2017年的167萬億,貨幣供應量在充分反應宏觀經濟的同時,也構成了房價猛漲的重要原因。
第三,分析結果中被解釋變量和通脹率一階滯后項的系數也值得注意,不僅顯著為正,且系數相對較大,而對產出缺口的滯后項反應不顯著。這表明貨幣政策的實施具有明顯的慣性效應,并且通脹率的歷史信息構成了貨幣政策反應規則的重要依據。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文引入房價波動作為貨幣政策規則目標函數的約束條件,構建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兩種貨幣政策反應規則模型,并推導出含有房價因素的最優反應規則。結果表明,納入房價波動的貨幣政策反應規則更有利于政策的穩定性和產出、通脹目標的實現,貨幣政策在對產出和通脹做出反應的同時,也應對房價波動做出反應,同時應對產出和通脹以及自身滯后項做出反應。
但利用我國2008年以來數據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利率和貨幣供應量均未對房價波動做出有效和顯著的反應,而對產出缺口和通脹率的反應較為顯著,尤其是對通脹率的反應非常顯著。在兩個政策反應規則中,M2的影響效應更為明顯,對宏觀經濟的解釋力更強,考慮到我國貨幣政策實踐,M2也是我國房價持續上漲的重要原因。
3.2 建議
第一,將房價波動作為目標函數的約束條件納入貨幣政策的框架中。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仍將比較顯著,房價不僅是判斷經濟是否景氣的重要依據,也是實現物價穩定的重要作用力。理論證明當貨幣政策反應規則含有房價波動時,政策的調控效果更好,實證結果也表明貨幣政策主要以通脹率為目標,并未對房價波動做出有效反應,房地產的投資特性使得貨幣供應量大量流入房地產市場,并在推動房價不斷高漲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風險。因此,應盡快完善貨幣政策對房價信息的反應機制,提高政策工具對房價波動的調控效果。
第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完善利率對宏觀經濟和房地產市場的響應機制建設,提高利率市場化程度,使其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2008年之后我國經濟面臨著環境不確定和增長不穩定等問題,利率對宏觀經濟的反饋機制不夠完善,作用渠道不夠暢通,利率政策大多為被動式的突擊和集中性的調整。因此應增加政策調整的主動性和分散性。
第三,繼續實施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價格型規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但實證結果表明在利率無法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顯示了較好的彌補作用。在提高利率反應規則對宏觀經濟以及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和效果的同時,仍需將貨幣供應量作為重要的調控工具。在對房價波動形成積極有效反應的同時,需要加強貨幣供應量反應規則的穩定性,推進其市場化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