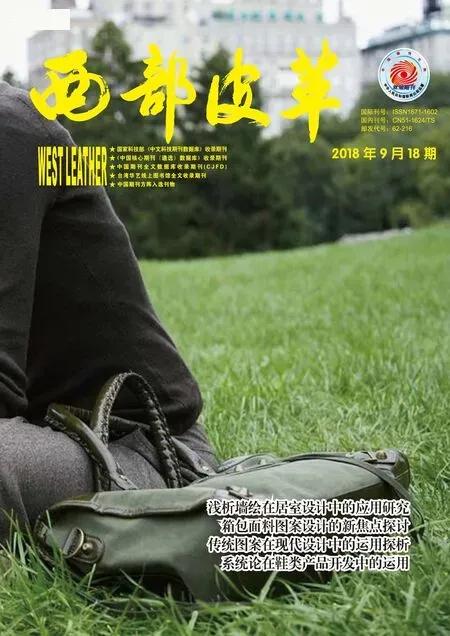對云岡石窟中二佛并坐的造像觀念及造像美學形式的分析
朱宛月
(成都大學中國東盟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曇耀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魏書》釋老志中寫到。魏書中多次提到五州山石窟,北魏的統治者拓跋氏在這里祈雨求福,自北魏遷都平城(今大同)后便在次選址開鑿石窟。明代后名云岡石窟,石窟的絕大部分是北魏中后期建造雕刻,是古代雕刻藝術的寶庫,也是中國佛教石窟造像藝術的一座高峰。
1 二佛對坐的造像觀念
云岡石窟造像題材中,表現最多的就是《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維摩詰經》這兩部經,本文主要探析的二佛并坐造型即是當時北魏流佛教流行《法華經》中的《見寶塔品》的內容。在云岡石窟中約有385個“二佛并坐”龕,幾乎每個洞窟中都有此形象,早期的云岡石窟“曇曜五窟”中將二佛并坐龕中東、西、南壁的不同位置上,有的雕刻于拱門或者門窗上,云岡晚期的二佛并坐作為主像置于了正壁(即北壁),在西部窟群的晚期中心洞窟中有一半的洞窟主像為二佛并坐龕,那么,“二佛并坐”在云岡石窟表現如此突出是何原因?其造像根據和觀念是什么?二佛并坐像的實際意義是什么及它是通過怎樣的佛教藝術體現造型的美學價值的,值得一探究竟。
二佛并坐的佛經依據是《法華經》,《法華經》全是二十八品,第十一品見寶塔品則是《法華經》在早期石窟寺中最常見的表現內容,其形式就是二佛并坐。《法華經第十一見寶塔品》經文摘要如下:
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
爾時佛告大樂說菩薩:“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量千萬億阿僧祗世界,國名寶凈,彼中有佛號曰多寶。其佛本行菩薩道時,作大誓愿:‘若我成佛滅度之后,于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
爾時釋迦牟尼佛,見所分身佛悉以來集,各個坐于師子之座,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虛空中,一切四眾起立合掌,一心觀佛。于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出大聲音,如卻關鑰,開大城門。
即時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于寶塔中坐師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禪定。又聞其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爾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如是說,嘆未曾有。
爾時多寶佛于寶塔中分半座于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摩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跏趺坐。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各作是念:“佛做高遠,惟愿如來以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虛空。”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以大聲音普告四眾:“誰能于此婆娑國土,廣說妙法華經。”
從經文內容可見“見寶塔品”不致力于說明佛法佛理,而是為了宣揚《法華經》,太武帝晚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文成帝在北魏政權搖搖欲墜之時繼位,在其頒布的詔書中寫道“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此及恢復佛教之意,利用佛教徒宣揚皇帝“即是當今如來”的欺騙手段,緩和階級矛盾和人民的反抗,以維持北魏政權。而《法華經》就是當時最受統治者重視的佛教經典,二佛并坐在云岡石窟之所以被塑造的格外突出,一方面是因為拓跋統治者大行“法華”來緩和民族和階級矛盾,利用宗教來麻痹人民,拓跋珪曾于公元398年下詔于京城作五級浮圖,耆阇掘山,須彌山殿以及講堂、禪堂、沙門座等等。《魏書》中也記載了許多北魏統治者崇尚佛法,修建寺廟翎羽等。據《魏書》記載,公元465年,在北魏文成帝去世的25年里,時年24歲的皇后馮氏被尊為皇太后,其作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臨朝聽政,甚至“獨攬大權”,在當時既有皇帝在位又有皇太后臨朝的情況下,許多王權貴胄并稱孝文帝和馮氏為“二圣”。云岡石窟建造了一系列雙龕,對應在當時所建造的佛教石窟寺廟中,以象征“兩個神圣政權的形式”。于此同時,也建造了大量的二佛并坐龕,其象征意義與雙窟如出一轍,用佛教的理論來對照,馮太后就是“現在佛”,而孝文帝年幼,受到馮太后的控制,是確確實實的“未來佛”,二佛并坐像即是“二圣”的時代象征像也是孝文帝與馮太后的社會顯身像。從中也可以看出“二佛并坐”是北魏封建統治在特殊形勢下對藝術表現的要求。
2 二佛并坐像造型美學形式的意義分析
二佛并坐龕在云岡石窟早期并沒有作為主要描繪對象進行雕塑,但在西、南、東三個方位上雕刻了這種造像龕。二佛造像龕造型為長條形,龕中二佛像并排面向正前方,舉右手于胸前,左手握著表示傳承佛法的“法衣”,雙腿呈跏趺坐,與其他早期佛造像一樣,面向豐滿,梳高肉髻,體態豐腴,右肩著袈裟如(圖一),龕內空間樸素干凈,佛像身后沒有雕刻身光,但頭的后背有一不明顯的光圈,整個造像裝飾簡單。

圖1 云岡石窟第十七窟明窗東壁
隨著洞窟形式和裝飾上的變化,云岡中期所造二佛并坐像有了一系列變化,將“二佛對坐”龕作為主像置于正壁,使這種題材的佛造像成為石窟中舉足輕重的重要內容。第七窟后室北壁的二佛并坐龕雖然風化較嚴重,但依然莊嚴巍峨,第九、十窟前室明窗兩側的二佛并坐龕雖然不是主像,但是龕內的兩尊佛像面相慈祥、高鼻柳眉、背光火焰紋內裝飾坐佛和飛天的布置,上面雕刻二飛天的生動造型,下面雕刻有二脅侍菩薩,龕楣飛天裝飾有花紋和肌理,佛龕裝飾變得絢麗多彩,同時為了更加突出二佛像,在雕刻技法上進一步加深了龕的深度,使佛像整體的立體性更突出,也產生了強烈的空間感,極大地增強了藝術感染力。加上特殊的位置優勢,使其成為人們重點的瞻仰對象。從審美角度看,中期的造像注重裝飾,絢爛綺麗、佛像給人以雍容華貴之感,其雕刻緊密,工藝精湛,令人嘆為觀止。(圖二)

圖2 云岡石窟第九窟窗前
“秀骨清像”是云岡晚期造像的最大特點,在造型方面,晚期的二佛并坐遠不如中期造型婀娜豐腴且畫面豐富、雕刻精髓,似乎又返還到早期二佛并坐龕古樸天然的狀態。在佛像造型的服飾上和形態上,二佛并坐像與其他同時期佛像一樣,溜肩并且面容消瘦,出現了褒衣博帶式袈裟,即衣服為對襟,露出內部的僧祗支,胸前有帶系結,右襟向左披向左肘上。五官產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嘴角上揚,鼻梁直峭、雙眼細長,笑容滿面,和藹可親。
在麥積山石窟、莫高窟、龍門石窟等其他中國重要石窟中均未見到石窟造像記載中有像云岡石窟的“二佛并坐”形象類似的場景。“二佛并坐”的形象在審美形式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對稱性。對稱是中國古典美學中最重要的理論成果與美學形式,也是人們長期審美活動形成的美的形式的總結。“二佛對坐”造型是云岡石窟藝術中極為重要的的藝術現象和藝術特征。對稱在審美視覺上,產生出均衡、穩定、和諧、完整的視覺特點與個性特點。因此會使人產生親切的感覺,也就容易被人接受。左右成雙,對稱互補,這就構成了云岡石窟“二佛”造像審美文化的本體性特點和主要的視覺特點。再聯系“二佛”所處之處:《妙法蓮華經》,只有將多寶佛和釋迦牟尼佛組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出統治者通過“二佛”現身說法宣揚《法華經》的目的,使人民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佛教義理與現實政治、社會生活就通過“二佛”有機融合在了一起,北魏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方法面面都借用石窟藝術的雕造和刻畫這種獨一無二的藝術手法傳達給了大總,也是給后人留下了復原北魏歷史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是人類歷史上宗教與藝術、政治與世俗堪稱經典的完美創造。中國的石窟造像藝術博大精深其造型語言及審美追求更是不斷傳承并演變,創新并發展。在歷史的更迭下、在時間的流逝中、在空間的變換里,感悟石窟造像藝術的內在精神和神動明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