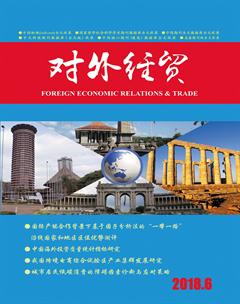國際產(chǎn)能合作背景下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測評
劉敏
[摘 要]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對選取的 3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與我國開展國際產(chǎn)能合作的區(qū)位優(yōu)勢進行測評,研究結(jié)果顯示,區(qū)位優(yōu)勢排名前十的國家依次為韓國、俄羅斯、日本、烏克蘭、土耳其、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哈薩克斯坦和匈牙利。按次級區(qū)域區(qū)位優(yōu)勢情況看,東北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韓國和日本,中東歐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俄羅斯和烏克蘭,西亞北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土耳其和以色列,中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哈薩克斯坦,東南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新加坡和泰國。
[關(guān)鍵詞]一帶一路;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優(yōu)勢測評
[中圖分類號]F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8)06-0006-03
Abstra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national advantage of 30 countries cooperate with China from “the Belt and Road”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t can be found that South Korea, Russia, Japan, Ukraine, Turkey, Singapore, Israel, Czech, Kazakhstan and Hungary were the top ten national advantage countries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Judging from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location advantage in the secondary region, it shows that the top two countries with the greatest national advantage in Northeast Asia are South Korea and Japan, the top two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re Russia and Ukraine, the top two countries in Western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 are Turkey and Israel, the top one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are Kazakhstan and the top two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are Singapore and Thailand.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Evaluation on National Advantage
一、引言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fā)以及隨之而來的發(fā)達國家“再工業(yè)化”浪潮,使得“一帶一路”沿線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陷入“困境中(佟家棟、劉程,2017)[1]。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開展多時空、多領(lǐng)域以及多維度的國際產(chǎn)能的合作構(gòu)想,迎合了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借助外力實現(xiàn)突破式發(fā)展的需求(吳福象、段巍,2017)[2]。
隨著我國制造業(yè)發(fā)展取得長足進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開展產(chǎn)能合作的規(guī)模也逐年增加,但多集中于新加坡、俄羅斯等少數(shù)國家。這種集中度較高的區(qū)位分布潛藏著較大的風險,也限制了中國開展對外產(chǎn)能合作的潛力(邸玉娜、由林青,2018)[3]。因此,科學測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逐步增加我國開展對外產(chǎn)能合作的對象,對深入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開展產(chǎn)能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回顧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選擇的相關(guān)文獻發(fā)現(xiàn),目前對于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并無定論(王培志等,2018[4];劉曉鳳等,2017[5];李建軍、孫慧,2017[6])。鑒于此,本文選取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將錯綜復雜的產(chǎn)能合作影響因素變量綜合為幾個核心因子加以解釋,提高準確性。
二、區(qū)位選擇評價指標選取
本文指標體系的構(gòu)建參照科學性、可行性、可比性和全面性原則,選取GDP(X1)、R&D;研究人員數(shù)量(X2)、航空運輸量(X3)、貨柜碼頭吞吐量(X4)、勞動力(X5)、高等院校入學率(X6)、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X7)、物流績效指數(shù)(X8)、營商便利指數(shù)(X9)、人均 GDP(X10)、企業(yè)注冊的啟動程序(X11)、創(chuàng)辦企業(yè)所需時間(X12)、總稅率(X13)、通貨膨脹(X14)、貨物和服務進口(X15)和貨物和服務出口(X16)共16個指標。
三、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選擇評價
運用SPSS軟件對2016年3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區(qū)位優(yōu)勢進行測評,涉及的數(shù)據(jù)均來自聯(lián)合國UN COMTRADE數(shù)據(jù)庫。
(一) KMO和Bartlett檢驗
通常用KMO和Bartlett檢驗來評價變量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林海明,2009)[7]。通常認為KMO統(tǒng)計量的值大于0.6時,適宜構(gòu)建因子分析模型。經(jīng)軟件計算得到,KMO統(tǒng)計量值為0.70,表明適宜構(gòu)建因子分析模型。
(二)提取公共因子
計算公因子方差發(fā)現(xiàn),除X5、X7、X11和X14這4個變量共同度略低外,公共因子包含了其他12個原始變量至少80%的信息。進一步計算特征值與方差貢獻率,前5個公共因子的特征根累計貢獻率為82.18%,所以將前5個因子視作公共因子予以保留(詳見表1)。
(三)因子旋轉(zhuǎn)
公共因子在部分原始變量上的載荷不存在顯著差別,則進一步進行因子旋轉(zhuǎn)。旋轉(zhuǎn)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明:第一個因子在X2、X3、X8和X4這4個原始變量上有較大載荷,反映出產(chǎn)能合作國家的科技發(fā)展水平和交通基礎設施水平間具有較高的相關(guān)性,把此類因子命名為技術(shù)及交通因子;第二個因子在X1、X10和X5這3個原始變量上有較大載荷,把此類因子命名為國家財富因子;第三個因子在X16、X15和X7這3原始變量上有較大載荷,把此類因子命名為對外開放因子;第四個因子在X6、X9和X11這3原始變量上有較大載荷,把此類因子命名為營商有利條件因子;第五個因子在X14、X12和X13上有較大載荷,把此類因子命名為營商不利條件因子。
(四) 測評結(jié)果
選用回歸算法得出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優(yōu)勢的因子得分函數(shù),具體如下所示:
進一步用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綜合評價的權(quán)重,加權(quán)得到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優(yōu)勢綜合評價得分,具體如表2所示:
四、結(jié)論與啟示
由以上分析可知,選取的“一帶一路”沿線樣本國家和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排名前十的國家和地區(qū)依次為韓國、俄羅斯、日本、烏克蘭、土耳其、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哈薩克斯坦和匈牙利 。從次級區(qū)域?qū)用娴膮^(qū)位優(yōu)勢得分情況看,東北亞地區(qū)開展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為韓、日二國,中東歐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依次為俄羅斯和烏克蘭,西亞北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依次為土耳其和以色列,中亞地區(qū)開展國際產(chǎn)能合作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是哈薩克斯坦,東南亞地區(qū)區(qū)位優(yōu)勢最大的國家則為新加坡和泰國。
我國應在繼續(xù)維護與新加坡、俄羅斯等東盟和歐洲國家產(chǎn)能合作關(guān)系的基礎上,與其他區(qū)位優(yōu)勢顯著的國家進一步挖掘產(chǎn)能合作的潛能,讓更多的國家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在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產(chǎn)能合作的同時,也要充分防范我國與這些國家開展產(chǎn)能合作可能面臨的匯率、政治、法律等多種風險。中國企業(yè)在開展國際產(chǎn)能合作前應對可能遭遇風險給予重視,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開展國際產(chǎn)能合作過程中善于采取保險公司信用證、第三方評估機構(gòu)風險預警等方式進行及時、妥當?shù)娘L險管控,以降低產(chǎn)能合作中的風險,推動國際產(chǎn)能合作順利開展。
[參考文獻]
[1]佟家棟,劉程.“逆全球化”浪潮的源起及其走向:基于歷史比較的視角[J]. 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2017,(06):5-13+59
[2]吳福象,段巍.國際產(chǎn)能合作與重塑中國經(jīng)濟地理[J].中國社會科學,2017,(02):44-64+ 206.
[3]邸玉娜,由林青.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動因、距離因素與區(qū)位選擇[J].中國軟科學,2018(02):168-176.
[4]王培志,潘辛毅,張舒悅.制度因素、雙邊投資協(xié)定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qū)位選擇——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面板數(shù)據(jù)[J].經(jīng)濟與管理評論,2018,34(01):5-17.
[5]劉曉鳳,葛岳靜,趙亞博.國家距離與中國企業(yè)在“一帶一路”投資區(qū)位選擇[J].經(jīng)濟地理,2017,37(11):99-108.
[6]李建軍,孫慧.全球價值鏈分工、制度質(zhì)量與中國ODI的區(qū)位選擇偏好——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J].經(jīng)濟問題探索,2017(05):110-122.
[7]林海明.因子分析模型的改進與應用[J].數(shù)理統(tǒng)計與管理,2009,28(06):998-1012.
(責任編輯:張彤彤 劉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