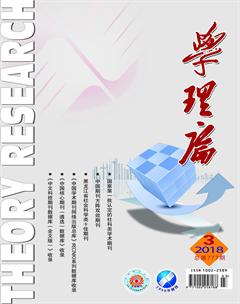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再審視
惠霞
摘 要: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重要探索和理論創新,是無產階級革命觀的新發展。葛蘭西認為國家政權的奪取與鞏固離不開對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的領導。歷史性集團的獲取與鞏固必須首先占有文化領導權,通過奪取和加強對市民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導,進而開辟出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文化領導權理論為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提供了一定思考,我們要加強黨對文化的領導,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多途徑、多方法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
關鍵詞: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3-0037-02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思想認為,對于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而言,應先奪取文化領導權,之后再奪取政治領導權,奪取整個國家,最終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即便是革命取得成功,也要繼續牢牢抓住文化領導權。“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其中政治社會涉及國家的核心政權,它以強制力和暴力方式進行統治;而市民社會的內涵是文化、倫理、價值觀、意識形態等,以認同或同意為基本實現方式。對應的國家領導權也有兩種:政治領導權和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文化領導權對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途徑有一定意義。歐洲革命失敗后使葛蘭西開始關注西方國家與俄國革命的差異性,他嘗試努力尋找和建立適用西方革命的戰略作為思考的中心。
一、創新黨的文化領導職能
政黨領導權的實現不僅構筑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領域,文化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有機構成。葛蘭西認為政黨在文化方面“所負的責任是把某一集團的有機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政黨在完成該職能時嚴格地依賴于其基本職能,即培養自己的組成部分——一個作為經濟集團生產和發展起來的社會集團所具有的那些成分——并且把他們轉變成合格的政治知識分子、領導者以及一個完整的社會所固有的一切活動與職能的組織者”。無產階級政黨歷來重視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文化領導權建設,并進行無產階級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當前世界面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融合等新問題、新情況,使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建設面臨著解構和重建的風險和困境,一方面面臨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主導的“意識形態終結論”“普世社會價值論”浸染,另一方面面臨國內社會思潮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取向多樣化沖擊。中國共產黨必須高度重視文化領導權建設,必須認清國內外的形勢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激烈性,要善于分析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新特征,有效地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
當下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變革,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改革進入了深水區。開放與包容的環境中,傳統與現代的價值沖突、本土與外來價值沖突、經濟與道德的價值沖突、集體和個人的價值沖突,主導文化在各種意識形態沖突、交融過程中不斷被消融,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對文化領域的領導,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立統一的國家戰略價值體系,搞好頂層設計,加快構建充分反映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全國范圍內的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良好氛圍,全面提高社會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掌握價值觀念領域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二、多種方式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
葛蘭西贊同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過程中的非自發革命論,但是他反對對廣大工人采取的一系列社會主義灌輸教育手段。對文化領導權的實現,葛蘭西主張一是通過認同、同意等民主方式,二是宣傳、引導的方式。他認為無產階級雖然致力于建立新型意識形態,但在革命中要奪取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后鞏固文化領導權,都要采用類似認同、同意等民主方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的場域發生了巨大變化,泛社會化的文化培育系統是當下面臨的境遇。葛蘭西指出:“‘領導權的每一種聯系必然是一種教育,而且不僅是發生在一個民族內,發生在組成這個民族的各種不同力量之間,也發生在國際的和世界的范圍內,發生在各種民族的以及各種大陸的文明復合體之間。”作為被領導者還是領導者抑或是參與者都將以全新姿態參與到這場文化領導權的斗爭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環境與民眾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眾的思維結構重新進行了構建,以認同和共識為特點的文化領導權越發凸顯其重要作用。我們必須批判地對葛蘭西提出的認同、引導思想進行選擇性使用。除此之外,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全面步入信息社會,大傳媒格局已然形成,新時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困難是空前的,大眾不再是單純的被傳播對象,他們的參與意識空前提升,他們的話語權力被賦予新的高度,話語權不再是少數精英群體所有,所以以認同和共識為特點的文化領導權越發凸顯其重要作用。
但同時“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我們要發揮灌輸教育的優勢,灌輸教育不僅在社會主義國家革命與建設中適用,安東尼·奧羅姆指出“任何社會,為了能存在下去,必須緊密地圍繞保持其制度完整這個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輸進每個成員的腦子里”。文明發展,尤其先發文明具有較強的聚合力,裹挾著自己的意識形態對后發文明進行擠壓、滲透乃至同化。任何社會、任何時期,要想很好地生存、發展都必須對社會整體成員的思想觀念進行強化,凝聚價值共識,盡量降低各類失范和越軌行為對社會的破壞力,而灌輸教育成為最直接、簡單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加強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建設
葛蘭西非常重視有機知識分子的作用,他提出通過培養“有機知識分子”建立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新的領導權和“歷史聯盟(historical bloc)”的政治難題。葛蘭西將大力傳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人稱為有機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是文化的精英群體,他們是掌握知識財富并在社會結構中參與領導上層建筑的人,是文化領導權的組織者和傳播者。葛蘭西認為不僅資產階級需要知識分子,無產階級也需要知識分子,尤其無產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相對于一般民眾,有機知識分子具有豐富的知識儲備體系和一定專業能力,具有高度自覺性和主動性。正如葛蘭西所說:“只有知識分子把群眾在其實踐活動中提出的問題研究和整理成融貫一致的原則的時候,他們才和群眾組成為一個文化的和社會的集團。”運用文化生產在市民內部建構并傳播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使廣大人民群眾認可并接受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意識,進而把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成為新知識分子的方式不再取決于侃侃而談,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的暫時的動力,要積極地參與實際生活,不僅僅是一個雄辯者,而是要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堅持不懈的勸說者。”對于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而言,不僅僅是“專家”,更應該是“專家+領導者”。他認為,知識分子應當“依賴于‘不停地堅信事業——不僅是夸夸其談,而且是提高到抽象——數學精神的作為建設者、組織者和實踐生活積極的融合;必須從勞動活動形式的實踐,推進到科學活動的實踐以及歷史的人道主義的世界觀”。
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知識分子作為首先覺悟的部分,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義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新時期,國家確立了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重要地位,他們是工人階級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的一部分,是人類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創造者,是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骨干核心。其觀點和思想在民眾心目中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對意識形態方面具有較高的敏銳性和前瞻性。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和培育過程中,知識分子應充分利用其知識和專業上的優勢,積極參與對國內問題的分析與評判,對大眾的情感和認知進行引導。第一,要堅持“四為”,即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第二,堅持“兩用”,即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對待我們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務必立足國情,立足時代,避免走兩個極端,一味否定或者盲目崇拜都將不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第三,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社會文化的引領,積極引導民眾正確地分析各類社會現象并合理地進行文化選擇,不斷向民眾傳播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善惡觀。第四,知識分子當保持文化自信和自覺。不斷創造本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斷為“同化和戰勝傳統知識界而斗爭”,努力探究社會現實狀況、社會矛盾和社會發展規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智力支持。第五,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隊伍的培養,將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在教育教學全過程。培養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人始終是培養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時時刻刻謹守的原則和底線。“學校是培養各級知識界的手段”,要實現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血液更新必須強化學校的培養和教育,抓住學校這塊陣地,更新社會群體已有的知識結構,引入新的知識體系并進行反復熏陶和持續引導,形成認同和共識。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認真解讀馬克思主義真諦,將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我們的信仰,做到真學、真懂、真信。同時還要做到真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充分與具體工作生活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教育人民、服務社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全國各族人民需要凝心聚力,必須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貫穿國民教育和我國各項工作的各個環節,推進新的偉大戰略布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1]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姜麗,張跣,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0.
[2]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3]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17.
[4]陳越.領導權與“高級文化”——再讀葛蘭西[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5).
[5]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M].曹雷雨,姜麗,張跣,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