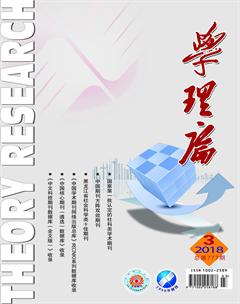西方環境話語的建構及啟迪
何修猛
摘 要:環境話語是試圖明確環境價值承諾、定位環境制度、引導環境利用和改造活動、形塑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話語實踐。西方環保主義基于話語框架理論特別是話語即權力與權利的理念,把環境問題裁定為危機、困境、災難,進行歸因分析,然后從倫理修辭、政黨規訓、儀式話語和全球動員多個維度,探討環境問題的消解,建構了包含環境問題性狀話語、歸因話語和路徑話語于一體的環境話語體系,是我國環境話語建構的有益養料。
關鍵詞:環境問題;西方環境話語;話語建構;啟迪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3-0092-04
環境問題源自工業革命。西方國家工業革命時間早于我國,發達程度高于我國,歷史上遭遇的環境問題先于我國,環境治理實踐也早于我國。承載環境憂患意識和保護路徑設想的西方環保主義話語,引領著西方國家環保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方向,是我國環境話語建構的有益養料。
環境話語是試圖明確環境價值承諾、定位環境制度、引導環境利用和改造活動、形塑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話語實踐。人類利用和改造環境的活動是環境話語存在和發展的根源。環境話語的主體有三種,即環境開發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環境開發主義者主要是“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1],認為人類是環境的主宰,環境僅僅是具有資源價值和應用價值的附加對象,衡量環境價值唯一的尺度是人類的需求,人類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和消耗環境;現在人類掌握了“人定勝天”的工業技術,“科學控制自然”成為可能,正是充分開發環境的好時光。顯然這屬于環境領域的資本性“霸權獨白”,傷害了環境話語的公正性與開放性。生態主義者認為“生態本身就是目的,任何進犯環境的作為都是邪惡甚至是罪惡的”,以增進人類福祉為使命的工業文明是環境問題的肇事者,保護環境的唯一出路是去工業化,拒絕工業技術。這屬于環境領域典型的“無責漫談”,雖然具有反抗資本權力的骨氣,但卻缺乏責任擔當意識和共識追求精神,妨害了環境話語的有效性。環保主義者既反對主張恣意進軍自然的環境開發主義,同時也認為生態主義“去工業化”的主張是因噎廢食,并不足取,它聲稱:人類擁有基于自身福祉開發和利用環境的權利,但也須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應該抑制過度開發環境的蠻蠢舉動;必須以合作姿態對待環境。環保主義者建構環境話語的旨趣在于解釋、定義和評價工業文明破壞環境的“事實”,既顛覆“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的“霸權獨白”,又跳出環境問題空談者的“無責漫談”藩籬,從而贏取環境話語權力,實現環境話語權利,并構建公共環境話語秩序,促成環境共識,引導大眾共同回應環境問題。
話語框架理論認為分析特定事件的話語包含性狀、緣由和路徑三方面,即是什么、為什么和怎么辦。目睹工業文明帶來的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和大眾不斷高漲的環保熱情,西方環保主義秉承話語框架理論特別是米歇爾·福柯“話語即權力”的思想,出于責任信念和變革思慮,借助主體間性哲學思維與實證研究工具,從環境問題性狀話語、歸因話語和路徑話語三個方面,醞釀并建構了自己的環境話語體系,試圖運用話語反對資本環境權力的壓制,更改環境權力的歸屬。
一、環境問題的性狀話語建構
人類是否遭遇環境問題,存在分歧。環境開發主義者崇尚主體性哲學,高揚人的主體性,頌揚人對自然的征服與占有,斷定人類統治自然、利用環境、改造環境是天經地義之事,何來環境問題?環保主義者認為主體性哲學必然帶來人類與自然的對抗與分離,主體性的人類與客體性的自然必然陷入對立狀態,環境問題已成既定事實。一般地說,化解分歧達成共識的話語策略有兩類:“一類是以協商和妥協為主的平和性的話語策略,另一類是以論辯和批判為主的批評性的話語策略”[2]。環保主義者的話語策略顯然屬于后者,把描述環境問題的性狀話語定位于災難話語、危機話語,運用揭丑策略和恐懼訴求策略,用激烈的話語對抗觸及環境問題的本質,使環境問題的制造者和普通大眾聽到“良心的聲音、責任的聲音”,達成環境性狀共識。
(一)西方環境災難性狀的呈現
起初,西方環保主義主要采用田野調查的方式呈現環境災難話語。田野調查是獲得常識、激發思維活力的研究范式,無論是鄉土化(家鄉化)研究、參與式觀察還是跟蹤式考察,均能直接接觸環境實踐中鮮活的人,體驗揪心的環境惡化事態,因此可以豐富環境政治的常識,糾正環境政治的常識性錯誤。西方環保主義田野調查的一般做法是:記錄親身觀察甚至切身經歷,通過個案實證研究,借助“確切性和可靠性”的事實和數據,運用文學修辭手法,以感性、個人化的、煽情的筆法,細節性、繪聲繪色地敘述危險化學品、工業開采、商業垃圾在食物鏈和傳導鏈作用下先污染某地食物、空氣和水體,最終殃及其他地方的可怕事實。一份份撕扯疼痛的環境檔案,因為裸露般展示了人類對自己所忠貞的泥土和自己的“背叛”,而觸動了大眾的心靈,讓大眾認識到如果再不采取斷然措施,環境問題將日趨惡化:“這些都是嚴重的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等待越久,風險越大”[3]5。環保主義者選用災難話語描繪環境問題性狀,采取底層敘事范式敘述親人離奇故去或莫名畸形的悲慘,描摹越來越多的動物與植物再也無跡可尋的無奈,用意相當直白:讓生態災難、環境風險成為社會的共同關切,修復大眾因為追求奢侈生活和過度消費而一度失衡的心理,使環保成為社會的認同聚合。
后來,西方環保主義更傾向于采用議題建構方式來呈現環境災難話語。“議題建構是一個過程,焦點在媒體如何與社會上其他機構互動,共創大眾關心的議題。”[4]當建構的議題成為媒體議題后,就能更廣泛、更深刻地影響大眾,進而成為公共政策。西方環保主義看到了議題建構的作用機制,于是刻意發掘各種廓開環境問題的消息來源,建構議題,讓媒體感到環境問題的發現與識別非常重要,看到基于人類中心主義而誕生的開發環境資源合法性隨著時間段延長而持續損耗的現實,形成媒體輿論,以此閉合人性欲望的空間。環境災難話語建構的本意在此。環保主義者運用新聞搭乘策略,開發環境事件的新聞內涵,成功地建構了風險社會、環境惡化與毒害、生態困境、環境污染、土壤污染、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化學污染、重金屬污染、核能破壞、有毒垃圾、生態退化、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耗損與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蔓延、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危險性廢物越境轉移、物種滅絕加速、大雨林趨于消失、過度開發、奢侈消費、浪費主義社會、粗魯的物質主義、資源枯竭等議題,用以描述和譴責工業污染與城市化給環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傷害甚至危機。這些環境災難議題的建構,有效地制造了環境焦慮感、恐慌感,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環境和人類已經處于兇險的危崖,環境風險因此成為大眾共同的關切,人類與環境相互融合遂成共同夢想。
(二)我國環境性狀定位:突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在快速發展中也積累了大量生態環境問題,成為明顯的短板,成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5]當前我國確實面臨能源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污染嚴重、環境退化等環境問題,百姓已經從“求生存”轉向“求生態”,從“盼溫飽”轉向“盼環保”,環保成果和人民群眾對生態文明美麗中國的熱切期待存在差距,環境陡然升格為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之一,環境問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各級政府應該在保護環境方面交出人民滿意的答卷。因此,黨的十九大順應百姓要求,明確提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6]。黨中央明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為基本國策,明確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施政方針。這些都表明我國中央政府具有敏銳的環境問題意識,并著手制定環境政策。但是有些基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嚴峻性和緊迫性缺乏警醒,存在難免論、短痛論等認識誤區,以致環保工作不得力、配合不主動。為了貫徹綠色發展理念,仍然需要建構環境問題的性狀話語,在不妖魔化的前提下,不遮丑不護短,客觀描畫、呈現當下某些地區、某些領域的環境問題,實事求是地將其定性為“明顯短板”“突出問題”,講透環境風險,培養居安思危、居危思危的環境警醒意識,提高“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5]的認識。
二、環境問題的歸因話語界定
對環境問題進行災難話語定性后,西方環保主義便開始追問環境問題的病灶緣由,得出三種結論。
(一)資本家的貪婪
起初西方環保主義把環境災難歸因于資本的本性,認為正是資本家“環境是為人類而存在”的自私觀念和沒有節制的欲望,“把毒害環境的行為當成既精明又經濟的實用主義”[3]229,讓他們做出“犧牲長遠福祉,獲取短期利益”的舉動,一手制造了蕾切爾·卡遜所說的“死亡之河”,田地、牧場、河流中潛伏了巨大的危險,地球變成災難場域。
(二)工業技術的副作用
批判了資本家的自私與貪婪后,目光更加深邃的環保主義者基于科技威脅論,把環境問題歸因于工業技術,指出工業技術為人類“蒙昧的觀念”“配置了最新的、最可怕的武器”,對自然無須謙卑甚至“控制自然”這樣妄自尊大的想法似乎接近可能,但結果卻是“無數的城鎮失去了春天的聲音”[3]229,工業技術的出現本就給環境帶來“巨大的破壞性”。烏爾里希·貝克的分析則更加系統,他在《風險社會》中指出:工業革命的改造浪潮使得當今社會成為危機四伏的風險社會,風險的誕生往往是“與文明程度和不斷發展的現代化密切相關的”,工業主義對技術神話的膜拜,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懸崖,工業社會制造了環境風險,卻不能有效應對環境風險。
(三)資本主義制度的衍生品
浸潤于新制度學派的環保主義者把環境問題歸因于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有兩種觀念。
一種觀念認為環境惡化是資本主義制度偏差的產物,其所崇尚的“帝國式的”或“奢靡性的”生活方式,導致消費異化,引發環境危機。因此只要實施“綠色新政”,推行“綠色增長戰略”,走綠色資本主義道路,在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性結構的前提下,不僅可以擺脫當前的經濟發展困境,而且可以實現綠色未來。顯然這是在維持資本主義政治根基不變的前提下,尋找溫和或激進、變更性或替代性的環境政治表達,提醒資本主義在環境問題上要“相對仁慈”,屬于自我審視、自我譴責、自我修復的范疇。
另一種觀念認為,環境惡化是資本主義制度基因性的產物,走向“社會主義”是消除生態危機的最佳選擇,這就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的關系注定是矛盾的或破壞性的,資本的“效用原則”和“增殖原則”,決定了其本性是無止境地掠奪自然中的一切資源,漠視環境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特征,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資本邏輯是環境危機的根源。貝拉米·福斯特據此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反生態的本質,“這種生產方式正朝著與地球基本生態循環不相協調的方向發展”,因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需要專心致志、永無休止地積累,不可能與資本和能源密集經濟相分離,因而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也會出現產能過剩、勞動力富余和經濟生態浪費”[7]。因此綠色資本主義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必然陷入詹姆斯·奧康納所提出的“第二重矛盾”: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與自身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資本擴張的無限性與自然界自身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本·阿格爾甚至認為“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8]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主要危機。因此,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路徑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徹底改造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構建新型的社會自然關系,促進社會公正與可持續有機融合,促進環境和人類社會協調發展。
上述觀點表明西方環保主義具有鮮明的政治取向。今天我們建構環境話語,也應該站穩政治立場。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因此,研究環境保護,應該借鑒西方環保主義的現實觀照與實踐取向秉性,自覺地把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環境保護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過程進行思考,在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的總格局中,系統籌劃環境保護,做到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銘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5]的指示,既要摒棄以犧牲環境、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又要反對放棄工業文明回歸原始的靜態環境保護和零增長環保主張,積極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的道路。
三、環境問題的路徑話語選擇
伴隨工業革命的進一步發展,西方環保主義看到大眾雖然為保護環境做出了努力,但環境呈現的格局依然是“憂多于喜”,特別是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工業革命浪潮的興起,制造出了更大范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驟然成為世界問題。西方環保主義把環境問題裁定為危機、困境、災難,進行歸因分析之后,便從倫理修辭、政黨規訓、儀式話語和全球動員多個維度,探討化解環境問題的路徑,引領環保運動向縱深方向發展。
(一)倫理修辭
資本之所以能夠“從環境污染中獲利”,根源在于大眾追求奢侈生活和過度消費。保護環境,需要所有人的道德自覺。西方環保主義看到,越來越多的大眾認同了環保議題,但卻存在明顯的知行不一現象,原因是環境理念沒有發展為道德覺醒與自律,因此必須發起倫理勸喻甚至道德審判。于是他們除了在政治領域和公共管理領域為環保著書立說外,還創立環境倫理學,不斷向大眾灌輸以下環境道德理念:固守人類中心主義,必然導致無休止地掠奪自然,人類具有環境原罪;人類應該養成“沒有超越其他物種特權”的意識,并進行生態贖罪;全世界20%的工業社會人口享受大部分財富、消耗大部分資源、產生大部分污染,而其余80%的人卻在惡劣環境中受苦受難,這是缺乏道德的;人類沒有殺害與剝削其他動物來追求自己經濟和社會目的的道德權利;當代的倫理責任是確保有充足的資源保留給未來的世代;簡單生活、簡樸生活是美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資源過度開發、粗放利用、奢侈消費造成的。”“生態文明建設同每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都應該做踐行者、推動者”[5]。今天我們建構化解環境問題的應對話語,強化公民環境意識,當然要有道德倫理的規勸:一是從道德層面引導大眾正確認識人類與環境的關系,樹立正確的環境信仰,克服人類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關切環境惡化問題,以此推動大眾環境道德意識覺醒;二是倡導適度消費的生活方式,重提“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道德主張,重申“開發環境有底線,消費商品有上限”的倫理命題,引導大眾牢記梭羅的教誨:“大部分奢侈品,以及許多所謂生活中的舒適品,非但不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必定阻礙著人類的崇高向上”[9],崇尚節儉,拒絕奢侈消費,做有環境良心的消費者。
(二)政黨規訓
西方環保主義發現,面對龐大的“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和工業技術的轟鳴,自己的呼喊是孱弱的,只有組建強大的政黨,才能爭取話語權,于是探索政黨化道路。他們摒棄分歧,從松散聯合走向綱領化的團體組織,組建了以促進環保為宗旨的高級組織形態——綠黨,環保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得以成型。綠黨運用環境理想、環境信仰、環境綱領、環境治理、環境制度、環境權利、環境權力等政黨話語,強調給予環境價值承諾,在公共管理層面定位環境制度,思慮環境政策,以此謀取環境權力,保障環境權利,并發揮規訓大眾的作用。綠黨的出現,標志環保經過學者呼吁與抗爭,終于進入“政黨”層面,可以登入“廟堂”議政、參政了。聯合國、歐盟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紛紛發布“綠色新政”“綠色經濟倡議”“綠色增長戰略”和“綠色技術轉型”年度報告,探討“綠色經濟”“社會生態轉型”等議題,提出了多種力圖實現人類綠色發展的環境政治理論。環保話語社團試圖創造“威權”話語,實施“支配人體的政治技術”,管約或者役使著大眾發展成為“合格”的環境公民。雖然綠黨在綠色政治信條上囿于選票而與資本的壓力有所妥協,但其政黨話語在推動環境議題轉化為公共議題、規訓大眾兩方面確實已卓有成效。
今天我們建構環境話語,同樣需要環保專業組織做堅強后盾。為此,應該進一步提升各級政府環保職能機構的行政地位,賦予更大職權和話語權;同時積極發展環保社團組織,引導它們發表環保時事報道與評論,發布環保公益影音,組織環保志愿者服務和環保主題宣傳活動,促進環保國際交流,發布環保事件真相與社會呼吁,提起并支持環保維權訴訟。這樣,借助環保社團話語,不斷強化環保話語背后所代言的制度意識,使之成為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強勢話語甚至“威權”話語。
(三)儀式話語
西方環保主義熟知儀式乃培育大眾環境素養的最佳載體,于是不斷設置環境主題節日,建構儀式話語。1931年意大利生態學家提議每年10月4日為世界動物日。1970年美國環保主義學者蓋洛德·尼爾森和丹尼斯·海斯提議每年4月22日為世界地球日,得到廣泛認同。此后,世界濕地日、世界森林日、世界水日環保主題日得以確立。在環保主義者引領下,這些環保主題日每年更換宣傳主題、標語和標識,創作主題公益廣告,開展路演推介,借助專題紀念活動,演示看似簡單實則內涵豐富的主題儀式,富有定力地開展環境焦慮營銷,使大眾“把視覺轉向環保的環境影像政治和生態情景劇”,核心用意就是向社會傳播環保意識,倡導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引導大眾端正對自然環境的態度,糾正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同時也表達了人類對美好環境的向往和追求。
西方環保主義運用儀式話語成功地進行了環境價值訴求。環境價值訴求著眼于大眾的身份化呈現和品質化生活愿景,使環境保護與大眾所崇尚的社會價值、精神理念、生活感悟、生活方式達成等同,使環境傳播演化為價值代言,“環境話語”成為“文化話語、文明話語”,由于借助了儀式化的敘事視角與方式,加上注重“國際權威利用”和“場域利用”的超邏輯化設計,環境主題日成為時尚價值演展的過程,環境保護成為具有優勢地位感的社會亞文化。
今天我們建構環境話語,也需要借鑒環境儀式話語的范式。具體而言,就是以環境儀式話語為抓手,策劃、組織環保主題日傳播活動,演繹環保經典儀式,借此培育良好的公民環境意識,引導大家牢記恩格斯當年的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真正理解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的內涵,使全社會把關于環境資源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手段這種片面認識轉變為環境本身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的科學認識,確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價值理念,發展和保護相統一的價值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理念,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價值理念,讓大眾意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建設生態文明就是造福子孫,從價值觀層面夯實保護環境的社會基礎。
(四)全球動員
西方環保主義最早提出“地球是我們共同的小村莊”,需要大家共同的善待與呵護。為了向世界喊話,進行全球動員,他們組建了多個國際性環保NGO,以全球動員為邏輯出發點,通過非政府組織機制,開始了聲勢浩大的環境話語傳播,以喚醒全球大眾的環保意識。他們堅持NGO的公益秉性,發揚“蚍蜉撼大樹”的無畏精神,砥礪前行,推動、協助聯合國多次召集國家元首會議,專項研討不同的環境問題,敦請各國政府簽署《蒙特利爾議定書》《斯德哥爾摩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性環保公約,指導各國制定環保政策,共同挽救岌岌可危的地球,雖說不上碩果累累,但也是成就喜人。經過他們的持續努力,當初被視為“異端邪說”的環境話語成為人類共識,各種意識形態論者都認同環保議題。
今天我們建構環境話語,既要突出富有中國特色的環保實踐新理念新實踐新成就,也要映現全球環保事業的公共話語譜系,呈現中國的人類環境命運共同體觀念和責任擔當精神;既要以包容的態度善待國外環保主義者的批評甚至指責,又要理性、客觀地反駁和陳述我國環境事件的真相。在扎扎實實推進環境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地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建設的基礎上,開展國際環保傳播,大力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等觀念和當下環境治理實踐,講好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故事,讓全世界了解中國正視環境問題并勇于應對的景象,知曉我國的環保承諾,知曉我國的國際環保貢獻,如伸張國際環境正義,倡導權利與義務相平衡原則,公正承擔與國情相匹配的環保國際責任和義務,簽署環保國際公約,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環保規則制定,尊重國際環保規則,推進全球環境治理體系變革,承接國際環保會務,勇于回應氣候變化,等等。通過這些展現中國主流環境敘事的影像文本,建構國際環保話語秩序,形塑中國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并已經“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的大國形象。
參考文獻:
[1][美]阿爾·戈爾.紀念《寂靜的春天》出版25周年[EB/OL].[2017-10-17].http://blog.com.cn/s/blog_637312a80101br.
[2]張鳳陽.政治哲學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354.
[3][美]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M].許亮,譯.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5.
[4]李華君.政治公關傳播[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17.
[5]習近平.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為人民群眾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N].人民日報,2017-05-28(1).
[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人民日報,2017-10-28(5).
[7][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耿建新,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38,127.
[8][加]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M].慎之,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486.
[9][美]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M].杜先菊,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