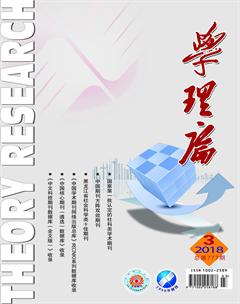試論自我意識的辯證結構
肖超
摘 要: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是統一意識的兩個不同方面:它們處于同一個意識折返運動的兩端,并且通過辯證運動把一方的特性帶到另一方,雙方接受彼此的“饋贈”從而實現交互作用。所以,不但意識到的自我是自我的對象,同時意識到的對象也包含著自我。但這并不意味著對象意識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就是對象意識。雖然它們都屬于“同一個意識”,但是在認識論上我們必須將其區別開來——把它們當作性質不同的兩類意識,并且把自我意識看作更高層次的意識。
關鍵詞:對象;自我;對象意識;自我意識;辯證結構
中圖分類號:B516.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8)03-0101-02
以往的哲學在探討意識的結構時,思路一般有兩種:一種是以生理或生物學為依據,根據意識生成的時間階段來探討意識的結構,這種思路按意識發生的自然順序把意識的最初始形態當作最根本、最本質的部分,因為這一環節決定了意識發展的軌跡和最終形態,是意識自由發展的邊界。另一種思路或是根據意識的不同功能分為理論自我與實踐自我的意識(康德),或是以意識的不同認知層次把意識分為意識、自我意識和理性(黑格爾),這種思路將意識所發揮的最大作用或意識發展的最高形態當作意識的本質部分。在黑格爾的精神哲學里,我們是根據現成的意識形態,認識到意識已經潛在地是它所是的東西了。
一、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的區分和關系
(一)對象意識
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在邏輯層面上將意識分為兩種類型:“意識一方面是對象意識,另一方面是自我意識”[1]。所謂“對象意識”,是指向對象而不直接指向自我的意識。但黑格爾直接談論“對象意識”的地方并不多,多數時候他都是在談“意識”和“被意識到的對象”這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對象意識”本身首先關乎的是一種邏輯關系,這是對象意識能夠存在的前提。
另外,就關系的一方即對象意識自身的構成部分而言,被意識到的對象以及對對象的意識這兩者在黑格爾那里與在康德和謝林那里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康德說“我思必能夠然伴隨著我的一切表象”表明了意識主體和認識對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即:一方面直觀雜多的感性材料經過意識的先天統覺形成經驗,另一方面,邏輯的認識前提即認識的先天結構必須能夠應用于感性經驗材料。滿足了上述兩個條件,知識才具有某種確定性。謝林在《先驗唯心論體系》中雖然也聲稱“意志活動原初必然是以一種外在對象為目標”[2],但這種對象只是“絕對同一”外化為客體的對象,意識和對象之間本來就是直接同一的。與康德和謝林不同,在黑格爾看來,對意識而言,他者不僅為著意識而存在,而且在這個關聯之外也存在著,是一種自在的存在,此時,他者的“自在存在”已經不同于康德實踐哲學領域里不能被認識主體把握為思想本質的自在之物了,而是作為知識的對象,作為還沒有被主體認識為真理的一種潛在的本質和真相的存在。在黑格爾那里,對象意識的矛盾需要通過自我意識的自否定來克服。這是對象意識能夠向自我意識過渡的內在原因。
(二)自我意識
所謂自我意識,簡而言之就是意識主體對自身的意識。意識在意會到自我、識別出他與對象的不同時,他不再單純地以為自己是純粹意識活動的旁觀者,而是自覺到自身并不在這一“旁觀活動”之外。自我意識自始至終都在積極地參與著他為著別人謀劃的活動中,因此這個活動其實也是為他自己謀劃的,只是起初他并未意識到這一點。關于自我意識和意識這兩者之間流行的區分,喬治·H·米德有一個經典的概括:“意識符合某些經驗如疼痛和愉悅的經驗,自我意識指的則是作為一個對象的自我識別和出現”[3]。也就是說,意識通過轉向意識的背后,而意識到了他自身,他識別出了與對象不同的自我,同時意識到對象就是自我。
想要談論“自我意識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我意識難以被直接把握的特性,使得自我意識揚棄對象的差別而向同一的自我回歸的過程中,需要借助“揚棄了的對象”和揚棄的活動本身而被認識。所以,自我意識是一個運動,但它又不是簡單的向上或向下的線性運動,而是借助對象折返自身的辯證運動。在運動的過程中他者被揚棄,差別不復存在,而顯現出來的差別只是自我意識的內在環節,差別本身成為“那個純粹的內在運動之單純的、流動的實體”[4],它反映了自我意識的內在本性。可見,在自我還未回到自身時,對象意識那里已經潛藏著超越自身的因素了,雖然還只作為轉瞬即逝的流動的本質和作為個別確定性的本質,但它依然是事關本質的意識。
二、自我意識的認識論起源:從對象意識到自我意識
通常情況下,意識只指向對象而不指向自我。因此,這就有一個從對象意識過渡到自我意識的問題。那么,意識為何沒有停留在對象意識階段而是向上進了一步呢?
上面談到,對象意識是“物—我”矛盾在自身內的一種對立形式的表達,但實際上這是一種表面的、淺層次的矛盾,更深層次的矛盾源于“自我”本身即生命的矛盾。“有生命之物要死亡,因為生命就是矛盾……族類的過程乃是它的生命力的頂點”[4]。生命中一個絕對不可被超越的否定是死亡。但也就是在同時,意識到死亡的不可被超越性之后,自我才能毫無牽掛、自由自在地展開自己的本質。在自我意識辯證展開的過程中,對象已經不再單純是對自己的否定,而是與自身合一的。此前費希特理解為自我局限性的那些方面,在黑格爾看來便是自我超越性的原因,正是有局限、受圍困,所以才會有此后精神的突圍。
生命的有限性使意識不斷被削弱的局限性無可避免。而對象意識要和那個純粹的意識,也就是自我意識聯系在一起并且上升為自我意識,就必須通過一個中介環節,這個環節就是“欲望”和“勞動”。“生命之多種多樣的、內在分化著的廣袤領域,還有生命的各別情形和復雜狀況等等,都是欲望和勞動在行動中所指向的對象。”[4]“欲望”和“勞動”作為中項雖然代表著兩端,但它卻是供兩端“差遣來差遣去的一個仆人”[1]。“對于仆從意識本身而言(即對象意識),如下兩個環節——首先,它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對象,其次,這個對象是一個意識,因此是它固有的本質——是分開的”[1]。所以當意識主體身在欲望中和勞動中時,他才感到自己是和諧的統一體,而不再是矛盾的分裂和差別。以往的差別是對象和意識的差別,是情感的欲望和這種欲望的目的之間的差別,而現今的差別只是對象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差別,是揚棄了對象折返自我和等待被揚棄重新返回自我之間的差別,因而它只是“一個直接與我毫無差別的差別”[1]。
三、自我意識的一般結構:對象與自我的關系
自我意識的結構中既有對象又有自我,這個關系就是自我意識的一般結構。
黑格爾在談論感性確定性時,涉及存在的真理時使用的“這時”“這個”和“意謂”,都表明對象在被意識綜合進自我之前的本質易逝性。這就好像是在面對不確定的新生事物時,人們總是習慣拿過去的什么東西做參考,因為已經過去的反而表現為一種真理性。雖然經過“比對”最后發現這一個同那一個不過是同一個,但是自我的真理性卻通過仔細“比對”的活動建立起來了。
所以,自我意識中的對象與自我的關系已經不再是起初的矛盾關系了,它有別于動物與對象之間的關系。自我意識走在尋找他自己的路上,“精神,這個回到自己的誕生地的思維,在它終于發現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絕對知識之前,在它獲得自覺的與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為人類學的、現象學的、心理學的、倫理學的、藝術的、宗教的精神,總還不是自身。”[4]也就是說,雖然意識回到了最初的誕生地,并且自覺到意識活動幕簾之后的那個自我了,但此時的自我仍然是受限于對象的自我,因而還不是純粹的自我。不過,此時的對象已經不是異在了,不是主我需要拼命去克服、消滅的東西,原來“物—我”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消失了,我通過意識到它的存在,通過我的意識中的“為他存在”而又通過勞動的實踐環節,最終變為“為我存在”。最后限制“物—我”關系的不在物,而轉變到了自我身上。自我意識結構過渡到了“我與我”的辯證關系。
四、自我意識的辯證結構:自我與自我的關系
在對象意識的一般結構中,意識中只有對象沒有自我。在純粹自我意識的結構即辯證結構中,則是“被意識到的自我”或“成為意識對象的自我”和“意識到自我存在的自我”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那么,自我意識如何能夠一般地為人們所認識并且具有普遍必然性呢?
康德已經回答了認識的確定性不在對象那里,而是在意識的“本源統覺”亦即是在人的先天認識結構里。黑格爾則根本否認了不可認知的“自在物”的實存,如果它存在,也只存在于人的意識里,并且以空洞、無內容的外殼形式存在。黑格爾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而代之以精神的現象,只不過現象的內容因為有精神來充實,所以它不但必然可以被認識,而且,現象不僅不是超感性世界的表象,相反它是超感性世界的根據。“內核或超感性世界的世界已經產生出來了,它來自現象,現象是它的中介活動。換言之,現象是內核的本質,而且,實際上正是現象使內核得到了充實”[5]。
在“自我—自我”的關系中,前者是作為意識主體的自我,后者是作為意識對象的自我。由此發現,自己在自身中創造一個對立的為它存在在形式上與自己對立,進而又在自身的關聯活動中揚棄自身,發現對立的他者其實就是自我。自我既是原初的自我但又不僅僅是原初的自我。所謂自我意識的辯證結構就體現為作為對象的我與作為自我的我之間的辯證關系。同一個我,因為意識活動的中介而被二重化了。黑格爾的精神辯證法是一個否定的運動,自我意識的辯證結構意味著對自我的意識具有否定自我的特質,只不過這種否定同時也是一種肯定,即通過否定自我在認識自己的知覺活動中的謬誤,最終肯定自我。
參考文獻:
[1]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142.
[2]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11.
[3]喬治·H·米德.自我、心靈和社會[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151.
[4]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401-408.
[5]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