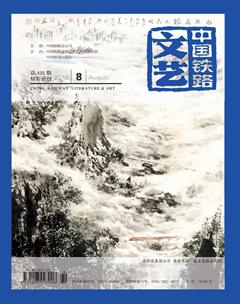買指針的老太婆
王開
那個(gè)夢(mèng)過去很久了,可它無賴似的黏著我,一發(fā)現(xiàn)空隙立刻搶灘登陸,非逼我回憶一遍彼時(shí)情形。
那天下午我就被這么攪得不得安寧。
真是夠了!
我溜出辦公室,穿過馬路到附近超市閑逛。你知道,四點(diǎn)多鐘絕對(duì)不適合回家,電視節(jié)目進(jìn)入垃圾時(shí)段,令人生厭。試試讀書?逮哪兒一歪,沒分清角色眼皮開始打架。更可惡的是,雖然困倦不堪,因?yàn)樯镧姴粚?duì),你又睡不成。干家務(wù)呢,也不行,東一耙子西一掃帚的,什么也沒干明白。逛街景也不在考慮范圍內(nèi),你見過哪個(gè)公務(wù)人員工作時(shí)間跑到外面逍遙?以鞨城的地理空間,倘若膽敢這么干,保證你前腳溜達(dá),后腳上了領(lǐng)導(dǎo)黑名單,輕者通報(bào)批評(píng),重者么,極可能從此走向事業(yè)的斷頭臺(tái)。相比之下,去超市轉(zhuǎn)幾圈,買點(diǎn)菜及亂七八糟的東西,磨蹭到下班直接回家比較妥當(dāng)。
民以食為天,誰能為這事兒較真呢。
我吃得不多,也買不了多少菜,黃瓜、豇豆隨意挑幾根,順帶著瀏覽擠滿商品的貨架,交了款,走出超市。
那個(gè)夢(mèng)繼續(xù)尾隨我,以至于途中遇到一個(gè)熟人,互相頂頭碰了,我尚未反應(yīng)過來。
他說:“你總是低頭走路,想什么呢?”
我笑笑:“壞習(xí)慣而已。”
十五分鐘后,我站在鞨水北路3號(hào)一單元3樓302室門口。
事情就出在我即將進(jìn)屋的瞬間。
我反手準(zhǔn)備關(guān)門,余一乍寬縫隙的時(shí)候,一根朝天椒和幾顆焦黃的玉米粒從門縫貼上來。我大駭,攥緊把手使勁往里拽,可我根本拽不動(dòng),焦黃的玉米粒變成上下兩排根部腐蝕的牙齒,朝天椒擴(kuò)張成一條隆骨突出的鼻梁,我甚至看清一只鼻孔沾著黏糊糊的鼻屎疙瘩,這讓我無比惡心。我松開拎包和裝菜的袋子,來不及管它們掉在地上發(fā)出悶響,騰出另一只手,企圖合力將鼻子和牙齒拒之門外。
——又是六樓的老李太太!
老李太太前幾年從鄉(xiāng)下搬來,她女兒二十郎當(dāng)歲的時(shí)候在日本酒店做小姐,后來嫁給日本人,一口氣兒生仨小鬼子,大鬼子感謝她接續(xù)香火之功,給她一筆錢,加上她自己的積蓄,在鞨城買了房子,給老李太太住,照顧她和前夫生的獨(dú)生兒子。
老李太太人厚道,缺點(diǎn)是話癆,見面老遠(yuǎn)打招呼,追著你聊。她還有個(gè)致命的毛病——走路比貓還輕,好幾回我被她嚇半死。
第一次是早晨,我背朝樓道鎖門的工夫,恰巧老李太太下樓,見我嘩啦嘩啦擰鑰匙,說:“上班呀?”我根本沒防備后面有人出現(xiàn),渾身一激靈,手里的鑰匙掉在地上。“李嬸兒啊。”我撫著胸口,把跳出來的心臟按回去。老李太太滿臉的不好意思:“丫頭,嚇著你啦?不嚇不嚇。”我說:“沒事,是我沒注意。”
最嚴(yán)重的一次是冬天,晚上下班,一開樓門,昏暗中有人忽然朝我齜牙一樂。我只覺有什么東西狠狠撞擊一下心臟,跟著腦子一暈,腿一軟,差點(diǎn)兒癱地上。幸好樓道被破紙盒、礦泉水瓶等占據(jù),我趁勢靠在墻上,半晌才看清,老李太太在歸攏撿來的破爛。老李太太又不好意思了:“丫頭,不嚇不嚇,摸摸毛沒嚇著。”那只老樹根子般的手向我伸過來,越過我的臉,罩在我頭頂上。我往旁邊一偏,躲過她的手,扭身上樓。
如果說,以前的屢屢遭遇我諒解了老李太太,冬天那次簡直就是恨她了:動(dòng)不動(dòng)撿回一堆破爛堵住門口沒法走人。最可憎的是,她的舉止對(duì)我等同邪靈,再這樣下去,我非死她手里不可。
冬天過去之后,老李太太和她不聽話的外孫子均不見蹤影,起初我挺開心,時(shí)間一長,感覺有點(diǎn)兒不對(duì)勁,打聽四樓劉大哥,他說:“老李太太患血栓病,回老家養(yǎng)病去了。”
我的高興勁兒頓時(shí)消散——我再怎么討厭她,也不希望她纏綿病榻呀。
難道老李太太病情緩解重返鞨城了?
我一邊想,一邊兩手摳住門把,不許她進(jìn)來。可是,我馬上明白,這斗爭毫無意義,老李太太的一只手穿過越來越寬的門縫伸進(jìn)來,尖指甲鑲?cè)胛业氖直常鄣梦沂忠凰桑T戶大開。
我倒退兩步,腳踩在地毯墊子旁的藍(lán)色亞麻拖鞋上。
我的屁股落在拎包和裝菜的塑料袋子上,嘴巴張大,一股呼嘯而來的風(fēng)剎那間沖進(jìn)我的脾胃。
入侵者根本不是老李太太。
她后腦勺揪著個(gè)發(fā)髻,別一根雕花木簪子,一端還垂下一串瑪瑙珠子,由于太瘦的緣故,天青色長袍子把她裹得像根腐朽的柴火棍,不過,腿上那條提花真絲黑褲顯出她的闊綽。我瞪著她那張有皮沒肉的臉,沒好氣地問:“你是誰?”
老太婆毫不在乎我的反感,咕嚕著一對(duì)渾濁的眼珠子,討好地朝我笑笑:“姑娘,我剛搬來這個(gè)小區(qū),迷路了,能讓我坐會(huì)兒歇歇嗎?”
原來是這樣。
近幾年,我們小區(qū)的成功人士陸續(xù)買了高檔住宅,騰出空房搬來不少上歲數(shù)的住戶。對(duì)他們而言,這個(gè)喚作鞨水北路的小區(qū)雖然老點(diǎn)兒,但面積適中,臨水而居,配綠地花園,居家養(yǎng)老實(shí)屬不錯(cuò)。
我放軟聲音,指著客廳的沙發(fā):“哦,你坐吧。”
老太婆感激地朝我點(diǎn)頭,蹬掉鞋子,忙不迭朝沙發(fā)那里奔。我一把拽住她,示意她穿拖鞋。我怕她的襪子底下浸透汗臭,一踩一個(gè)印子,污染地板。老太婆低頭看了看,腳伸向藍(lán)色亞麻拖鞋。老天!我暗叫一聲,搶先將藍(lán)色亞麻拖鞋滑到一邊,腳趾勾來酒紅燈芯絨拖鞋給她——這是專門待客用的,盡管一年到頭我家里也沒什么人造訪。老太婆盯了我一眼,挑著專門供給她的拖鞋,踢啦踢啦走到沙發(fā)跟前,不解恨似的一屁股躉下去,身子仰靠沙發(fā)背。
老太婆不拿自己當(dāng)外人的做派,很令我不爽,又不好表現(xiàn),小心拾起那雙藍(lán)色亞麻拖鞋,放進(jìn)鞋柜里。爾后,端起茶幾上的養(yǎng)生壺,為老太婆倒一杯自制酸梅湯。老太婆又渴又累,急不可耐地抓起那只畫滿纏枝蓮的青花瓷杯,揚(yáng)脖喝干濃稠的液體,末了,抬手擦擦腮邊的殘余。“真好喝。”老太婆放下纏枝蓮青花瓷杯,眼睛卻盯著養(yǎng)生壺,決心要鉆個(gè)洞,讓里面的液體自動(dòng)流出來,最好流進(jìn)她的嘴里。
我假裝沒懂老太婆的意思,提起門口的袋子,走到廚房——我打算歇一歇,捱到飯點(diǎn)兒等她走了好做飯。我從廚房出來,發(fā)現(xiàn)老太婆頭枕著沙發(fā)靠背打起盹來,甚至發(fā)出呼嚕呼嚕的聲音。這也睡得太快了吧?我想,她一定為回家吃了不少苦,頂著大太陽到處轉(zhuǎn)悠。那就讓她睡一會(huì)兒好了。我踱到書房,拾起一本讀了很久的書,拉直折角,順勢讀下去。
說是書,其實(shí)就是自印的冊(cè)子,紙張粗糙,設(shè)計(jì)簡陋,內(nèi)容么,云山霧罩但也不是全無道理。書是一個(gè)研究玄學(xué)的老頭兒送我的,之前,他讀了一篇我寫的遠(yuǎn)古女神的文章,認(rèn)為我是個(gè)得道開悟的人,費(fèi)了很大勁聯(lián)系上我,幾次三番打電話,說些神叨叨的事情。有一次我正開會(huì),沒工夫接,他打三遍,我按斷三遍。我以為他就此生氣不再聯(lián)系我,不曾想,幾天后他再次打過來,這回我不好再不接,解釋了上次的原因。他說本想請(qǐng)我一起去棋盤山觀棋,他說觀棋尚在其次,重要的是入定,在那個(gè)特殊環(huán)境下高人幫你入定,引領(lǐng)你的靈魂,你就會(huì)看到現(xiàn)實(shí)之外的,不為大眾打開的世界。我不太喜歡他操著很重的河南口音講那些不著四六的東西,本能地把他與封建時(shí)代橫行宮廷的江湖術(shù)士劃等號(hào)。不過他說的另一部分倒符合我的價(jià)值觀,就是:“你知道怎么到這世上來的,將來回哪里去,你到這世上來,是為了結(jié)賬,別人欠你的,你欠別人的,這一輩子都得還完,了結(jié)這些賬,你也就完成使命了。”
難道所有的濫情都是為了討債或者還債嗎?想到這一點(diǎn),我對(duì)他的話嗤之以鼻。
老頭兒可不知我的心理活動(dòng),誠心誠意給我寄來這本書,叮囑我好好看看。我也改變了主意,覺得不管宣揚(yáng)的什么,有必要了解一下。岡仁波齊不是說么,生命的路沒有白走的,每一步都算數(shù)。
許是天熱的緣故,看幾頁書,我竟也迷迷糊糊睡著了,醒來時(shí),想起陌生的老太婆還在沙發(fā)上睡覺,趕緊去客廳。
沙發(fā)空了,其他房間也沒有老太婆的蹤影。
我愣了一會(huì)兒,斷定她睡醒后,見我也睡著了,沒好意思打擾我,自己開門走了。這讓我有些過意不去,畢竟上了年歲的人,怠慢她顯得失禮。
我打算再遇見面給她道個(gè)歉,但是踅摸好多天也沒見著,打聽一些熟悉的人,描述老太婆的體態(tài)樣貌,皆說沒有這個(gè)人。
她是誰,住哪棟樓,到底回沒回家,真的與我不相干,我犯不著為此糾結(jié)。
接下來的一段時(shí)間如往常一樣,平靜得乏味,乏味中泛著霉?fàn)€的味道。
研究玄學(xué)的老頭兒也毫無聲息,他去五臺(tái)山了,說要收一收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他指的是,讓這個(gè)世界不干凈的東西。他收了那些雜碎,我們的世界就純粹了。
只有那個(gè)夢(mèng)如影隨形,驅(qū)不掉,趕不走。
當(dāng)然,它不在的時(shí)候,我也做別的夢(mèng),那些夢(mèng)在每個(gè)夜晚如期來臨。
夢(mèng)來臨之前,前奏異彩紛呈。
一般說來,關(guān)燈后,它們從餐廳的冰箱那里開始表演,偽裝成冰箱的聲音,像被夾子夾住的老鼠一樣吱吱叫(我知道這不是冰箱,冰箱絕對(duì)不做這種令人心驚肉跳的游戲,何況它白天安分守己,從無過分的舉動(dòng),緣何到了晚上大顛覆呢)。尖叫一陣,它們?cè)诘匕逑赂Z來竄去,咔吧咔吧的聲音如同按響卷曲的手指。它們的演技十分高明,除了尖叫,還模仿粗重的呼吸,邁著自以為輕巧的步子在客廳踱步,其實(shí)它們的每一步都沒瞞過我的耳朵。它們甚至肆無忌憚地跑到臥室墻角,在花梨色實(shí)木衣柜的兩堵墻的夾角攀緣,有時(shí)它們穿墻到隔壁的人家去了,有時(shí)從臥室穿到客廳,逗留一番,再折回來。這種非凡的本領(lǐng)使我欽佩之極,專心致志地側(cè)耳傾聽,乃至無法入睡。
有一段時(shí)間,鞨城下令全城暖氣改造,傳統(tǒng)的水暖改為一戶一閥進(jìn)戶。于是,我們這種老舊的小區(qū)率先拆解,這使我暗自慶幸,之前因?yàn)榕瘹獠缓锰崆案牧说責(zé)幔谶@場空前的浩大工程轟轟烈烈開展時(shí),我只需把進(jìn)戶的管子和地?zé)岬墓茏訉?duì)接一下即可。而鄰居們呢,趁機(jī)給好端端的家扒得只剩下四面墻壁,其狀之慘一如中了戰(zhàn)爭的炮傷。不過我也跟著倒了霉——鄰居們天天連刨帶鑿,我家里成了灰塵場。鄰居們白天拆,晚上也不閑著,大半夜的咚咚咚在屋里折騰,挪東西,搬家具,十一二點(diǎn)也不消停。等我看完書想睡覺,他們還沒完沒了。終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爬起床上樓,打算敲開門告誡鄰居停止擾民事件。但是,我上了樓發(fā)現(xiàn),根本就沒人挪東西,樓道靜得駭人,鄰居們的防盜門關(guān)得死死的。
我回到家里,剛躺在床上,咚咚咚的腳步和挪東西的聲音又來了,我對(duì)其恨入骨髓,真想有根鐵棍子從天花板捅上去,把那只不知疲倦的腳穿個(gè)窟窿,扎在地上耗死它!
這種情況下我只好打開已經(jīng)關(guān)閉的手機(jī),搜索儲(chǔ)存卡里為數(shù)不多的號(hào)碼。這些號(hào)碼背后,隱藏著我的熟人或朋友們,但我必須依靠儲(chǔ)存器才能保證不搞混象征每個(gè)面孔的數(shù)字。不過也有例外,比如一個(gè)早已刪除的號(hào)碼,我不用回憶就能把十一位數(shù)字一點(diǎn)不錯(cuò)地按出來。按出來,又抹掉。再按,再抹。或者,我會(huì)在屏幕上寫下一行字或一段話,發(fā)送,也可能不發(fā)送。我知道一行字或一段話如一艘航船抵達(dá)彼岸,也知其必將像脫軌的流星,消失于茫茫太空,燃燒之后粉身碎骨。
那個(gè)夢(mèng)境,通常也是這種情況下鍵入的。
我詳細(xì)描述了那個(gè)夢(mèng)境,從頭至尾,一點(diǎn)不差,寫完檢查好幾遍,再字斟句酌,確保無誤才發(fā)送出去。
我并不期待流星的返回式運(yùn)動(dòng)軌跡,若它還存有能量,一定會(huì)在某個(gè)時(shí)刻火球般的降落大地,若能量耗盡,那是它的宿命。
由于過多的關(guān)注夢(mèng),我把擅闖民宅的老太婆忘了。
老天保佑,但愿她別患癡呆血栓之類的病灶,找不到家再到我這里來。
一個(gè)周末的傍晚,我在廚房做飯,忽聽外面有人敲門,透過鎖眼一看,竟然又是那個(gè)老太婆。我本想裝作不在家,不給她開門,手卻下意識(shí)地?cái)Q開暗鎖,剛欠開一道縫,老太婆迫不及待地?cái)D進(jìn)來,討好地朝我笑笑。
“姑娘,你看……”老太婆為難地一攤手,表示她登門的迫不得已。
我蹙眉。
老太婆輕車熟路地穿上那雙紫紅色燈芯絨拖鞋,照例把自己躉進(jìn)沙發(fā),仰臉望著我,“你坐呀。”好像她是主人,我是冒犯者。
我的氣莫名其妙升起來。你怎么不告而別啦?我險(xiǎn)些將這句話說出口,到了嘴邊,感覺不妥,立馬咽回去——我這么一說,不是埋怨她,而是包含著深情厚誼希望再見的意思。這根本不可能么。要知道,我從不歡迎別人到家里來,家是能量場,外人來多了,能量場就會(huì)破壞,滲透一些別的雜質(zhì)。
我怎么能讓她產(chǎn)生這樣的誤解,以后頻繁登門,干擾我的生活呢?
可我的廚房里還有沒做好的飯,鍋里燒著菜,沒空和老太婆磨嘰,一時(shí)也想不出合適的借口趕走她。于是,我敷衍道:“你坐吧,我還有事。”
老太婆滿臉堆笑。
她居然氣定神閑地跟我到廚房門口,探頭往里看看,轉(zhuǎn)身退到餐廳,在餐桌旁坐下,順手拎起桌上的養(yǎng)生壺,給自己倒了一杯冰糖菊花枸杞,咕嘟咕嘟喝下去,由于喝得太急,粘稠的液體從嘴角沿著下巴流進(jìn)脖頸,消失在胸口那里。之后,她舔了舔嘴唇,自語道:“真不錯(cuò)呀。”我不知道老太婆說茶不錯(cuò),還是再度來我家里不錯(cuò)。但她像在自家一樣的隨便,引起我的極度反感,我匆匆鏟兩下鍋,重新扣上蓋子,擦擦手,走出來——這期間我已經(jīng)打定主意,爭取晚飯前請(qǐng)她出門,我猜她聞到紅燒雞腿的香味想蹭飯了。
我拉出一把餐椅,坐在老太婆對(duì)面,看著她,表示你為什么又來的疑問。老太婆瞭我一眼,說:“我一出門總是找不到家,我已經(jīng)在附近轉(zhuǎn)悠好長時(shí)間了,只好到你這里來。”我說:“我在小區(qū)打聽許多人,都說沒見過你。”老太婆哼了一聲:“我剛搬來不久。”“那么你的意思是不熟悉這一帶才找不到家的嗎?”老太婆又哼一聲,懶得回答我的樣子。“你有家里的電話嗎?我喊你家人來接你。”老太婆搖搖頭,“忘記了。”“那你家樓下有什么標(biāo)志?”“沒有哇,我不記得有什么標(biāo)志。”“你家里人都在哪里上班,比如你女兒、兒子?”“我家只有患病的老頭子。”
盤問半天,也沒問出有效的信息。
老太婆記性不怎么樣,嗅覺很靈,一邊應(yīng)付我的話,一邊抽了抽鼻子:“雞腿真香啊,快翻翻鍋,別糊底。”
我對(duì)老太婆的討厭成倍增加。
的確,燒雞腿的湯汁即將熬干,我必須鏟出來,盛在盤子里。
這也意味著,晚飯開始了。
我在廚房拖延著時(shí)間,擦灶臺(tái),排油煙機(jī),抹干凈洗菜盆邊緣的水漬,希望老太婆看出火候主動(dòng)告辭。
老太婆果然站起來,我心里一喜。
她走到廚房門口,手一伸,“我?guī)湍愣税伞!?/p>
我哀嚎一聲——沒治了,老太婆賴上這頓晚飯了。
“我自己來,你坐那兒等著就行。”我的語調(diào)溫柔得讓我自己也感到吃驚。
燒雞腿、涼拌苦瓜、一小塊盛在青花開片小瓷碟子里的腐乳,另一只同色瓷碟子裝著幾朵水發(fā)黑木耳。此外,我為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杯子是斗笠形,青花釉里紅的裝飾,古樸的裝飾圖案與琥珀色的酒漿絕配。我喜歡鞨城地產(chǎn)的一種葡萄酒,采小粒冰葡萄和貫穿鞨城的蘇子河水發(fā)酵制作,純度極高,口感也不像昂貴的進(jìn)口紅酒那么怪異,很對(duì)我的審美觀。
老太婆眼上眼下瞅著我倒酒,我豈能看不穿她的伎倆,佯作不知,扣上酒瓶木塞。
“你這酒是自釀的吧?自釀的好,不摻假,喝完不上頭。”老太婆盯著酒瓶念叨著。
“開酒廠的老大哥送的。”
“哦哦,姑娘你心善,人緣好。”老太婆的嘴巴抹了蜜。
我明知她為喝酒誑我,也樂得受用,給老太婆也倒了一杯,“你也嘗嘗。”
老太婆兩眼冒光,手摩挲著膝蓋。
恐怕她年輕時(shí)是個(gè)酒鬼吧。
沒想到老太婆年齡大,食欲驚人,她吃了兩只雞腿,三杯紅葡萄酒,一碗白米飯和一些蔬菜,我納悶她干瘦身體里容納了多大的胃器官,一下子吃掉這么多食物。很明顯,老太婆吃得十分盡興,話也格外多,夸獎(jiǎng)我家里布置得有格調(diào),花花草草茁壯茂盛。她說:“一看姑娘你就是有教養(yǎng)的人,書房那么多書,架子上擺著精致的瓷器,了不得呀。”我受她贊許,禁不住露出得意之色,嘴上言不由衷地謙虛。老太婆洞悉我的心理變化,愈發(fā)沒有底線地恭維我,“姑娘你用的香水肯定不一般,是架子上的那只吧?”她伸出柴棒子手指著博古架上的一瓶迪奧香水,“哎,一看就是好東西呀!”我忍不住笑了,女人么,多老也不失貪戀美的本性,不要命地打扮,作死般的取悅自己,也取悅別人。老太婆見我笑了,情知馬屁拍到正點(diǎn)兒上,“你看,我沒說錯(cuò)吧?我早看出來了,你心氣兒高,書房里擱那么大一桌子,又茶具又硯臺(tái)的,真真不得了……”
老太婆的甜言蜜語源源流入我的耳畔,蒙得我云里霧里,直到很晚才想起,她應(yīng)該離開了。
“你想起住哪棟樓了嗎?”
老太婆黯然,“沒有,我想不起來了。”
“你再回憶一下,想起來個(gè)大概也行,我可以送你。”
老太婆半閉著眼,作思想狀,我抱著胳臂,期待她從記憶中翻騰出住址,我好把她送走。
終于,老太婆睜開眼,一臉無辜地看著我,“我喝多了,什么也記不起來。”
我突然覺得這老太婆是抓在手里的一只刺猬,扔不得,捧不得,打不得,罵不得。我左右為難,非常后悔當(dāng)初讓她進(jìn)來,給自己造成大麻煩——家里有個(gè)陌生人,加上每夜必至的聲音,我那點(diǎn)可憐的覺還睡得成嗎?老年人腎不好,她晚上起夜用我的坐便器怎么辦?想到她一次次去衛(wèi)生間,嘩嘩地撒尿,一股子騷臭味霎時(shí)撲來,熏得我?guī)缀鯂I吐。可是這么晚了,我又不忍心趕她走,萬一她在外面出點(diǎn)什么事,我豈不是間接的兇手,即使沒人知道她出事前在我這里,良知上也過不去呀。
“姑娘,你留我住一夜吧,好嗎?”老太婆抬起頭,哀憐地望著我,眼里竟蓄滿淚水。
我承認(rèn),老太婆的眼淚太有殺傷力了。
“你住小房間吧,雖然小,但是床挺舒服的。”我柔聲說。
誰知,老太婆拒絕了,她指著沙發(fā),“我住它就行。”
“沙發(fā)窄,不利于翻身。”我凝視著老太婆的手指,驚訝于它們的長度。
“我歲數(shù)大了,別弄臟你的床。再說,我這么瘦,沙發(fā)足夠用了。”老太婆堅(jiān)持自己的意見。
老太婆挺知深淺,感染了我,心底攢起一絲暖意。我說:“好吧,隨你。”我將小房間的被褥挪到沙發(fā)上,鋪好,末了用力按了按,覺得不比床的舒適性差,整理完畢,讓老太婆躺下去,關(guān)掉客廳的燈。
我回到臥室,反鎖了門,換上睡衣。
12點(diǎn)鐘之前,不是我入睡的時(shí)間,但是那些聲音汪洋恣肆沆瀣一氣的天堂。我躺在床上,等待它們?nèi)缙诙粒婀值氖牵鼈儾]有來,這使我不太習(xí)慣,我想,它們一定有什么事情耽擱了,那我就耐著性子再等一等。
趁著這個(gè)空當(dāng)兒,那個(gè)夢(mèng)再次重現(xiàn)。
幾個(gè)月前,我到遠(yuǎn)離鞨城數(shù)千里外的西南小鎮(zhèn)出差,當(dāng)晚,我住在一間臨街的民宿里,上半夜聽著窗外天南地北的游客胡亂吵嚷,下半夜和那個(gè)夢(mèng)相遇。
是這樣的:最初的場面非常模糊,遠(yuǎn)景就像一幅反復(fù)洇染的撒過鹽和蜂蜜的寫意作品,完美地銜接中景的山脈,白色的河水把一整片叢林剪輯成兩部分,形成寬闊的山谷,成群的麋鹿在低洼處覓草。在稀疏的槭樹之間,佇立著一個(gè)男孩,因?yàn)榫嚯x的緣故,我辨不清他的容貌。男孩面向山谷,肌肉結(jié)實(shí)的脊背使他看上去那么年輕,那頭濃密的黑發(fā)像極了他的父親,他站成若有所思的姿勢,霸占著那爿風(fēng)光的主角。我走過去,母親一樣拍他的肩膀,問他,“你父親呢,他在哪兒?”我的聲音比山谷的風(fēng)還輕,男孩沒有動(dòng),我想他沒聽見我的話,又問,“你父親在哪兒?”男孩突然一抖肩,甩掉我的手,朝著叢林奔跑起來。他跑得很快,眨眼消失了,不,好像被寫意作品的力量吸進(jìn)去了,化為云彩、水和空氣。
我以為男孩討厭我,故意躲我,不打算說出真相。我傷心極了,繼續(xù)走向山谷深處。
我不知走到哪里,四周如同一只巨大的裝滿黑暗的匣子,我很害怕,想出去,摸索了半天,還在原地打轉(zhuǎn)。焦急與慌亂中,我好像撞上什么,眩暈之后,眼前猛地一亮——我擺脫了黑暗,來到一片荒原,沒有樹,沒有河流,只有衰敗的秋草海浪一樣飄搖。在海浪深處,延展著兩道深深的車轍,它們是剛剛碾壓出來的,車轍里汪著渾濁的積水。而那輛馬車加快速度,一路顛簸著迅疾遠(yuǎn)去……
我望著馬車上的背影嚎啕大哭。
哭醒時(shí),黎明尚在西南小鎮(zhèn)的山脊躑躅,天南地北的客人睡意正酣。
我再度淚流滿面。
臥房外的客廳,老太婆一切安好,沒有出現(xiàn)我想象的糟糕場面——老太婆不起夜,也不打呼嚕。她的安穩(wěn)感染了我,拭平那個(gè)夢(mèng)的折痕,我漸漸睡著了。
奇怪的是,那些聲音,那些死去的人例外沒有潛入我的睡眠,與我百般纏斗。我睡得非常踏實(shí),醒來的時(shí)候,竟然已近七點(diǎn)鐘。好在是周末,不必急三火四爬起來,捯飭捯飭趕點(diǎn)兒上班。我可以賴一會(huì)兒床,閉著眼睛,還原一下昨晚的事情。我想,原來有人做伴也挺愉快的,并不是那么可憎。好比老太婆,表面招人煩,實(shí)際也有可親之處。甚至她讓我想到,她堅(jiān)持睡客廳,就像一位母親守護(hù)孤獨(dú)的孩子。
母親活著的時(shí)候,送我一盆君子蘭,每年開兩次,春節(jié)一次,開春一次。君子蘭長大后,分蘗小苗,我又栽兩盆,三盆君子蘭年年開放,尤其春節(jié)的一茬花,仿佛一大團(tuán)火焰在窗臺(tái)跳躍,使手足冰冷的我也跟著灼熱。母親過世后,燒過三周年,君子蘭幾乎同時(shí)死亡,最大的那一棵最為奇特,早晨還油綠堅(jiān)挺,到了傍晚,全部葉片遭了熱水澆淋似的,轟然坍塌。等我下班回來,看到那樣的情境,心被活生生挖掉一塊。
也許,燒完了三周年,母親的靈魂就不再保護(hù)我,真真正正去了另一個(gè)世界吧。
我應(yīng)該感謝老太婆才對(duì)。
這樣想著,我翻身下床,看看老太婆醒了沒有。
沙發(fā)上空無一人,被褥原樣折疊整齊擱在那里,好像從未有人睡過一樣。看來,老太婆醒來為免打擾我,悄悄離開。
——她想起家住哪里了?不過,我還是為她擔(dān)心,怕她記憶出錯(cuò)走丟。
若她真的走丟,我會(huì)有失去母親的悲傷。
一動(dòng)這念頭,我就覺得老太婆當(dāng)真丟了,一邊收拾房間,不由自主地難過起來。
然而,幾分鐘后我對(duì)老太婆的感激之情蕩然無存——我發(fā)現(xiàn),茶桌上的絲巾不見了,迪奧香水也沒了,這兩樣?xùn)|西很久沒使用,絲巾疊得四四方方封在一個(gè)紫色暗云紋的盒子里,香水只啟開外包裝,擱博古架醒目位置好幾年,平時(shí)我看都不看它們一眼,只是煮茶時(shí),摸一摸,聞一聞,心底發(fā)出悠長的嘆息。
我憤怒老太婆的無恥,原來她和樓根底下曬太陽的愛貪小便宜的老婦人一個(gè)德行,便埋怨自己太不謹(jǐn)慎,以為她年齡大,放松了警惕。
我下決心找到老太婆,讓她歸還我的東西!
我開始梳理小區(qū)所有的老年人,小區(qū)分AB區(qū),A區(qū)一共十棟樓,每棟樓設(shè)三個(gè)樓門,每個(gè)單元12戶,一棟樓36戶,A區(qū)共360戶,加上B區(qū),統(tǒng)共720戶,每天下了班,我假裝散步,繞著小區(qū)觀察,重點(diǎn)是花園、樓頭、健身小廣場,這類老年人愛聚集的地方。
十多天過去,我一無所獲。
你這個(gè)騙子!你這個(gè)該死的老太婆!我狠狠地咒罵她。至此,我相信她跟我說的全是假的,她就為來我這里蹭吃蹭喝蹭住宿,臨走順人家東西的老騙子。怪不得我總感覺她怪怪的,身上散發(fā)著詭異的氣息。
就在我氣急敗壞之際,發(fā)現(xiàn)我們單元出現(xiàn)生人,那是一個(gè)矮個(gè)子的瘦小男人,長著一張和善的面孔,出入見面,一定主動(dòng)打招呼。因?yàn)樵撍赖睦咸牛覍?duì)生人筑架一道藩籬,背地問劉大哥,他和我說:“矮個(gè)子男人是新搬來的,前幾日,老李太太的房子賣給他,老李太太快死了,回不來了。她外孫子呢,那小子的大爺領(lǐng)走了,說再過兩年當(dāng)兵去,上部隊(duì)拘管拘管,也好出息個(gè)人。”“哦,哦。”我連聲應(yīng)著,想起有一次鑰匙插鎖孔忘了拔下來,老李太太下樓看見,不挪窩地在門外一直守到我回來,心里頗不是滋味。
受老李太太離世的沖擊,我對(duì)騙子老太婆的痛恨有所減輕,我想著,興許這也是宿命吧,緣分盡了,上天就設(shè)計(jì)一種方式把它拿走。
若她是來點(diǎn)化我,就認(rèn)了吧。我寬慰自己。
孰料,老太婆消失一陣子之后,又一次毫無道理地闖入我家里。我甚至不知道她怎么進(jìn)來的,我下班時(shí)她正盤腿坐在沙發(fā)上,慢條斯理地嗑著瓜子,喝我剛悶熟的柚子茶。
天哪!
我嚇壞了,懷疑她偷配了鑰匙,如果她這么陰險(xiǎn),我哪里還敢得罪她!我感到非常害怕,因?yàn)楹ε拢也桓业÷炙睦锊粷M意,弄出什么惡毒的法子報(bào)復(fù)我。
我對(duì)她笑臉相迎,閉口不提她怎么來的,更不提丟東西的事。我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熱情有加,特意烤了抹茶面包、做一盤紅燜雞腿等豐盛的食物。吃飯的時(shí)候,我倆還一起喝了幾杯葡萄酒,氣氛十分地融洽。喝到后來,我倆全喝醉了,她握著杯子,細(xì)長的手指凌空點(diǎn)著我,鬼魅地笑道:“你心里怎么想的瞞不過我,你討厭我,惱怒我偷了你的東西,怕我報(bào)復(fù)你,假裝迎合我對(duì)不對(duì)?”
我一哆嗦:“不,不是,你想多了。我真的喜歡你到家里來,你像我母親一樣的慈祥。”
“哈哈。”老太婆爆發(fā)刺耳的大笑,“你撒謊!你不敢承認(rèn)?”
我完全被她的笑聲嚇呆。結(jié)結(jié)巴巴地說:“真的,真的。我沒騙你。”
“我不可能是你母親!”老太婆厲聲喝道。
“那你是誰?你說你是這個(gè)小區(qū)的,可這里沒一個(gè)人見過你,更別提認(rèn)識(shí)你!”我的膽子突然壯起來,氣憤地質(zhì)問她。
“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沒偷你的東西,它們還在。”
“什么?!”
“哼哼——”老太婆一聲冷笑。
我死盯著她。
“你看看,你太緊張了。”老太婆用洞穿一切的目光回敬我。
“沒有,我沒緊張!”我虛張聲勢地提高音量。
“呵呵呵,你的神情泄露了你的內(nèi)心。”老太婆嘲笑我,“你瞧,我知道你那些東西的來歷。”
“你一定是喝多了!”
“藍(lán)拖鞋的碼數(shù)你穿不了,香水放置多年,絲巾沒有一縷系過的褶皺,你認(rèn)賬嗎?”老太婆繼續(xù)嘲弄我。
我縮回去,不言語了。
老太婆不再理我,仰頭望著墻上的掛鐘,吁口氣,“做筆生意,怎么樣?”
我一愣,“嗯?我沒有什么可賣呀,也不想買什么。”
“不。你有。”老太婆晃晃頭。
“什么?”
“喏。”老太婆抬起下巴示意。
“你要買這個(gè)鐘?它很舊啦,不值錢。”
“不不不,價(jià)值大著呢。”老太婆反駁我。
“那你說說看。”
“我只要那根指針,短的那根。”
“呃?它是特殊材質(zhì)的嗎?”我又一次警覺,唯恐老太婆耍什么把戲套取我的東西。
“不。它和別的指針沒有任何區(qū)別。”
“那么它的價(jià)值在哪里呢?”
“要說價(jià)值,嗯,這么說吧,這根指針藏著巨大的秘密。”
“難道這只鐘出廠的時(shí)候就有什么問題?”
“不不不,這秘密與你有關(guān)……”
老太婆停下來,搖晃著她的腦袋,露出戲弄的快感。
我恨得牙根癢癢,又奈何不了她。
老太婆輕蔑地瞟我一眼,“你把它賣給我,我保證你會(huì)終止一場戰(zhàn)爭。”
“根本沒有什么戰(zhàn)爭,我很好!”
“你整天疑神疑鬼,甚至懷疑我這個(gè)老太婆,到處調(diào)查我。可事實(shí)怎么樣呢?”老太婆不搭我的茬兒,自顧自地說。
“我只是想找到你。”
“你把許多事情搞亂了,因?yàn)槟闾谝馑鼈儯m然看起來你毫不在乎。比如說,絲巾和香水,我發(fā)誓你不過是換了地方,你自己也忘了。”
“你明明關(guān)注那瓶香水了!”我企圖糾正她。
“我說了,發(fā)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分不清真假,那天晚上之后,你挪動(dòng)了它。如果你不信,現(xiàn)在就去臥室的柜子里找,它們?cè)谧髠?cè)門中部的第二個(gè)抽屜,裝在一只黑皮夾子里。我敢打賭,黑皮夾子里還有一只心形小金屬盒,里面裝些煙蒂和煙灰。對(duì)了,是價(jià)值不菲的上等香煙。你要不要我說出哪一種牌子?”
“不可能!”我絕望地嚎叫。
老太婆咧嘴大笑,深得沒有盡頭。
我立馬起身,幾步竄到臥室,拉開柜門,拽出第二只抽屜……
我蔫了,回到客廳,沉默不語。
“那么,你告訴我,你怎么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
老太婆一聳肩。
“怎么樣,你同意嗎?”
過了一會(huì)兒,老太婆問我。
“你容我考慮考慮。”我像只斗敗的公雞。
“三天時(shí)間夠嗎?”
我點(diǎn)頭。
老太婆朝我伸出手,我握著它,活像握著一把落雪的松枝。
“啊,這樣很好。我困啦,想休息了。”
我把老太婆安頓在沙發(fā)上,她很快睡著了,她睡著的時(shí)候,既像嬰兒,又像魔鬼。
照例,她在我醒來之前走了。我到底沒弄清楚她是誰。不過,她現(xiàn)在是誰已經(jīng)不要緊了,經(jīng)過認(rèn)真考慮,我決定賣掉那枚指針。事實(shí)上,我每次看到它,都以為是一柄一股無形的力量把持著的鋒利短刃,切割完美的時(shí)間,讓人活在對(duì)過去無所依憑以及對(duì)未來的無限恐懼之中。
第三天下午,老太婆赴約了。進(jìn)門就問,“你準(zhǔn)備好了嗎?”
“準(zhǔn)備好了。”我把卸掉的指針高高舉起。
老太婆興奮起來,眼神異常明亮,夸張地嘎嘎大笑,“我就知道你不會(huì)讓我失望。”老太婆笑得我發(fā)毛,不由得又生惶惑——一個(gè)沒有指針的鐘,還稱得上鐘嗎?鐘拆解了指針,就和時(shí)間沒有關(guān)系了,沒有鐘的提示,所有的黑夜都是白天,所有的白天都是黑夜,作為一個(gè)生命的個(gè)體,要么在這個(gè)空間里永恒,要么滅亡。無論永恒還是滅亡,我只剩下無感的軀殼,靈魂出竅,不是神,不是仙,妖魔鬼怪也算不上,那我是誰呢?不行,這絕對(duì)不行,這太可怕了!
我的天,一想到這些,我反悔了。
老太婆卻奪過指針,迅速揣進(jìn)懷里,疾步開門要走。
我躥上去攔住她,“等等,我不賣了。”
“你已經(jīng)收了我的錢!”老太婆兇相畢露。
“那么你休想走出這間屋子。”我和她較勁。
“嗯哼,你終究不肯放棄。我敢斷言,不聽我的話,一輩子夠你受的。”老太婆鄙夷地從上到下檢視我,“瞧瞧,一個(gè)高傲得低到塵埃里的人,一個(gè)可憐的,自以為強(qiáng)大無比的人。”老太婆笑得歇斯底里。
“住嘴!你給我住嘴!”我氣急敗壞地上前推搡她。
“你頑固堅(jiān)守的,正是捆綁你的鎖鏈。啊哈。”老太婆繼續(xù)譏諷我。
我和老太婆廝打起來,失手把她推倒,腦袋磕到茶幾的棱角,老太婆呻吟一聲,摔倒在地,再也沒有聲息。我意識(shí)到老太婆死了,我決不能讓她死在我這里,等她的家人找上門,我的好日子就來了。我得趁著黑夜把她弄走,扔得遠(yuǎn)遠(yuǎn)的,永遠(yuǎn)不被人發(fā)現(xiàn)。
于是,我找出一只大帆布口袋,把老太婆裝進(jìn)去,背上她下樓。
我乘坐鄉(xiāng)間公交汽車到一座荒嶺,下了車,確定四下無人,剛想把沉甸甸的口袋推進(jìn)深澗,就聽到老太婆在口袋里面說:“姑娘,還是放我出來吧,我現(xiàn)在憋得難受呢。”
“你這該死的!”
我站起身,拍拍手,看都沒有看她一眼,攔下一輛過路車返回城里。
路上,我接到研究玄學(xué)的老頭電話,他從五臺(tái)山回來了,說這一趟累夠嗆。他還說:“姑娘你信我的,好運(yùn)氣在你這邊,你會(huì)越來越強(qiáng)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