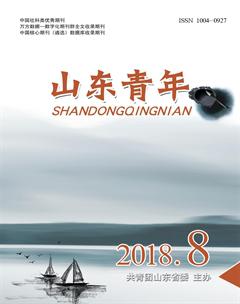論漢人義利觀與漢代宗族關系
秦鐵柱
摘 要:“義利之辯”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個時期內形成了各種義利思想,為漢代各種義利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漢人的義利觀總體上包括重義輕利、先利后義兩種義利觀。從兩漢歷史來看,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具有最廣泛的影響。它對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漢代人們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尤其是宗族內部關系的主流思想。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今天借鑒。我們要對漢人的義利觀及其在宗族關系領域中的實踐進行理性的分析,以便對當今社會正確義利觀的建立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以期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添磚加瓦。
關鍵詞:宗族;重利輕義;重義輕利
一、漢人義利觀的形成與發展
義利觀是一個大問題,思想流派、任何思想家都、任何人必須面對這個問題。春秋戰國時期是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奴隸制經濟崩潰,封建制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思想領域內也發生巨大變革。“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各派(儒、墨、道、法、陰陽等)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形成了各自的理論體系,自然也形成了各自的義利觀。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義利之辯”成為“百家爭鳴”的一個重要內容。在這個時期內形成的各派義利思想為漢代各種義利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漢人的義利觀無非包括先義后利、重利輕義兩種義利觀。董仲舒的義利觀是重義輕利義利觀的典型代表,兩漢還有很多思想家如陸賈、賈誼、桓寬、班固、王符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達了重義輕利思想。而公開地宣揚重利輕義或見利忘義義利觀的學派尚屬罕見,但在社會實踐中卻有不少重利輕義的事例。
從兩漢歷史來看,儒學大師董仲舒的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具有最廣泛的影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開始成為兩漢正統的統治思想,重義輕利義利觀可以說成為了兩漢正統的義利觀,它對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有兩種義利觀并存,一種是義利對立,談義不談利;另一種是義利兩有,但義重于利。“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2542。“正”、“明”均是對道義的肯定;“不謀”、“不計”均是對功利的否定。這是一種將道義與功利對立起來的義利觀。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又說:“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 152初看起來,這兩句話的含義并無大異,但“計”與“急”這一字之差就使含義有了重大區別。“不急”將道義與功利看作了一種先后的關系,這是一種對義利都有所肯定,但義又重于利的義利觀。《春秋繁露》出自董仲舒之手,《漢書》出自班固之手,兩種說法均有一定的根據。這兩種說法都與董仲舒的思想是相符的。董仲舒一般不反對言“利”。他主張給予民眾一定的物質利益,提出了“薄賦斂”、“省徭役”等主張。在他看來,只有使民眾的基本物質利益得到保證,社會才能得到治理。但是,他始終將義置于利之上。“君子篤于禮,薄于利”[1]64當人們將利置于義之上時,董仲舒則予以堅決的反對與痛斥,這是董仲舒義利觀的原則。
董仲舒的義利觀,總結了孔子、孟子、荀子的義利觀,吸收了“利”的觀念,從而更加富有彈性與活力。因此,他的義利觀既是對先秦儒家義利觀的繼承,又是對先秦儒家義利觀的發展。成為了漢代人們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尤其是宗族內部關系的主流思想。盡管在兩漢歷史上亦有不少重利輕義的事例,但重利輕義思想始終處于次要思想地位。
二、漢人義利觀在宗族關系中的表現
1、宗族互助
有的人把自己的俸祿、賞賜、財產分給宗族成員。如朱邑,“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鄉黨,家亡余財。”[2]3636初,(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后母昆弟。再受資千余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2]2890宋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3]904任隗,“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凈寡欲,所得俸秩,常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3]753“(廉范)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于賑宗族朋友。[3]1104“長嫂舞陰長公主贍給諸梁,親疏有序,特敬重(梁)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3]1166梁竦尚不富裕,他依然把衣食器物分給宗族貧者。“(張)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3]1198張奮雖財產傾匱,但仍不斷地接濟宗族之貧者。有的人在饑荒、戰爭中賑救宗族成員,如伏湛,“謂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余家。[3]894”趙溫,“歲遭大饑,散家量以振窮餓,所活萬余人。[3]949“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余,(朱)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3]1459有的人收養宗族中的遺孤。如宣秉,“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
石之儲。”[3]928 “(虞)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于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3]1151有的人主動出錢斂葬死去的宗族成員,“(廖)扶逆知歲荒,乃聚谷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瘟疫死亡不能自收者。”[3]2720 “(符融)妻亡,貧無所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3]2233以上事例不免有收買人心的動機,以鞏固其在鄉里之地位,但他們的行為確實緩和了階級矛盾,緩解了戰爭、饑荒給廣大民眾帶來的痛苦。
以上事例均體現了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類似的事例在兩漢的歷史上還有很多,但也存在著宗族成員之間重利輕義的事例。
2、相互爭財
有的人侵吞宗人財產,“(周黨)家產千金,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游學。”[3]2761宗族成員之間持兵械斗以爭財物。“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斗,(高)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扣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于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3]2769有的人因家貧而受到宗族成員的欺凌與鄙視,“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3]1209
總而言之,從《漢書》、《后漢書》及其它一些史料來看,絕大多數有關漢代宗族關系的例子所透露出來的都是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馮緄)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3]1281從這一句話就可以看出,廣大民眾贊同馮緄以重義輕利義利觀處理宗族關系的行為。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是漢代人們處理宗族關系的主流思想,而重利輕義的義利觀則是非主流思想。
三、重義輕利何以成為漢代宗族關系模式的主流思想
從漢代人們處理宗族內部關系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成為漢代宗族關系模式的主流思想。原因何在?
一是,思想家的大力宣傳。兩漢歷史上出現了許多有名的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達了重義輕利思想,他們不遺余力地向社會宣揚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強調以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在處理宗族內部關系。他們的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地由社會上層滲透到社會下層,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廣大民眾的日常行為,如“(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3]930廣大宗族成員贊同王丹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深深地影響了當地的風俗習慣。這些社會輿論傾向表明普通民眾認可了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重義輕利義利觀最終成為了漢代人們處理宗族關系的主流思想。
二是,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在漢代社會,宗族是漢代鄉里社會的基礎,是國家穩定的基礎,宗族關系的有序與否關系到鄉里秩序的穩定與否,關系到國家秩序的穩定與否,所以統治者對此非常重視。凡是在宗族關系中踐行重義輕利的義利觀的人是能夠得到統治者較快地提拔與任用的,上引所舉之例馮緄,他在宗族關系中,力行輕利的義利觀,后“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2]1281后又為隴西太守、遼東太守、京兆尹、司隸校尉、廷尉、太常。任隗賑恤宗族,力行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以為將作大將,……建初五年,遷太仆,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勛,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2]753統治者的以上策略又促使人們以重義輕利的義利觀來處理宗族關系。
三是,運用法律手段嚴懲破壞宗族關系的行為。前引周黨之例,周黨及其財產由宗人照料。周黨成人后,宗人企圖侵吞其財產,兩人對簿公堂,縣官把財產歸還周黨,給其宗人一定的懲罰。縣官處理此案必有一定的法律根據,漢代法律定然嚴懲破壞宗族關系之人。
通過對漢人義利觀與宗族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一是,我們要長時間地通過各種方式宣揚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使其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二是,我們要將正確義利觀的推行與個人利益、個人前途緊密結合起來。三是,采用教育和法律手段,規勸與強制相結合的方式推廣正確的義利觀。
三十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得到逐步確立,物質文明得到極大豐富,但有些人卻喪失了正確義利觀的指導,我們相信以上論述能夠對當今社會主義新型義利觀的建立具有一些積極的借鑒意義。在現實社會當中,我們并不否認個人利益,但個人利益要在義的引導與制約之下。要先見利思義、重義輕利,而絕不能見利忘義、重利輕義。
[參考文獻]
[1]董仲舒.春秋繁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M].上海:上海師范大學出版社,1945.
[5]呂世容.義利觀研究[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
[6]李玲芬.《先秦儒法兩家“義利之辨”探微》[J],《陜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1(9).
[7] 蘭堂.《墨孟“義”辯》[J],《駐馬店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2).
[8] 周舜南:《韓非的功利主義思想》[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8(5).
[9] 王澤應:《漢代道家的義利學說》[J],《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1).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