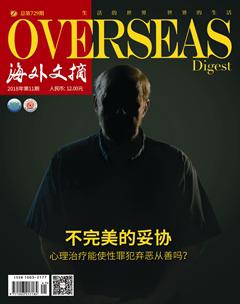40歲做母親,50歲做父親
深澤友紀 劉欣
近年來,日本社會少子化現象愈發嚴重。由于工作強度加大和婚戀觀念變化,高齡生育的情況越來越多。40歲做母親,50歲做父親,盡管有些無奈,但是做好規劃后,也是一番幸福的人生體驗。
40歲生子現象,20年增加3倍
看著孩子的睡顏,一旁的母親流下了眼淚。
我能陪他到何時呢?到他30歲或是40歲的時候?
去年剛剛生下孩子的46歲母親偶爾會這樣想。
她的生育之路非常兇險。40歲時她才開始找結婚對象,之后遇到了大她5歲的丈夫,同居半年兩人結了婚。她問丈夫想不想要孩子,丈夫說:“有孩子的話當然高興,還是順其自然吧。”丈夫這輕輕松松的心情讓她心生不快。
“如果我再年輕15歲,懷孕對我來說不過是考取私立大學的難度。可是,對于41歲的我來說,這就相當于考東京大學的難度了。不去不孕不育醫院治療是不行的。”
夫妻倆做好了思想準備,就去醫院開始接受治療。很快,這位女士懷孕了,檢查了孩子的胎心之后,兩個人很開心,可沒過多久她就流產了。第二次懷孕又以流產告終。夫妻倆又一次接受了檢查,檢查結果顯示妻子患有“抗心磷脂抗體綜合癥”,血栓導致血液無法正常輸送給胎兒。經過治療,她第三次懷孕,卻又胎死腹中。
休養幾個月之后,她想再次進行不孕治療,卻因為年齡被醫院拒收,她眼前一黑。此時她已經43歲了。感受到懷孕期限的緊迫,她十分焦慮。為了找到為她診治的醫院,她去了大阪。
經過體外受精,她第四次懷孕了。此時對她而言,與喜悅相比,對小生命消失的恐懼更為強烈。終于,在45歲的時候,她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隨著少子化的愈演愈烈,40歲以上才生育的人越來越多。日本人口動態調查結果顯示,2016年在日本出生的人口為97.69萬,自1899年統計以來,這一數字第一次跌破100萬。盡管孩子的出生數量在減少,40歲以上才生育的母親人數在2015年為5.39萬,是10年前的2.6倍、20年前的4倍。50歲以上生育的父親人數2015年統計有8236人,是20年前的2.4倍。
本刊針對35歲以上第一次生育的女性和45歲以上初為人父的男性進行了問卷調查。在“四五十歲才做父母的原因”這一問題上,47%的人回答是因為晚婚,33%是工作,還有18%是不孕不育。
一位來自廣島的家庭主婦今年40歲,她有兩個孩子,一個3歲,一個還不到1歲。說到晚育的原因,她的回答是“工作”。生第一個孩子之前,她在小學擔任教員。她的目標是成為學校的正式工,幾次挑戰錄用考試卻都沒成功,作為音樂課的臨時教員在校工作。
29歲的時候,她和比她大9歲的男性結了婚。她想著“該要個孩子了”,可沒有產假、育兒假的她只是個臨時雇員,她不能跟學校說“我懷孕了”,于是將懷孕往后拖。有了孩子的朋友因為照看孩子疲憊不堪,看到這樣的情景,她也不想放棄現有的金錢和時間,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她的懷孕積極性。
2012年,隨著NHK電視臺專題節目的播出,“卵子的老化”成為熱門話題。當時她35歲。
“誒,我也要成為高齡產婦了嗎?”她第一次感到焦慮。她不能再看著別人懷孕生子,自己無動于衷了。她很快開始備孕,半年之后她懷孕了,卻又流產了。與失去這個小生命的痛苦相比,生子離自己的遙遠讓她很是震驚。她再次懷孕,產假剛好是音樂發表會的一個月前。她說:“我的同事們都覺得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該休息。可是如果我一味考慮周圍這些情況,那我什么時候都生不了孩子了。”
剛剛步入30歲年齡層的時候,她工作努力,每年都去國外旅游,為了看自己喜歡的藝術家的表演飛到全國各處。生子之后,一切都變了。她再也沒有出國旅行過,出門都要按著孩子的情況去安排,連悠閑地上廁所也做不到。和孩子的合影里,她就像那位比她早生孩子的朋友一樣,素面朝天,頭發凌亂,但這樣的日常生活是珍貴的。
活用網購和家務電器
現在40歲左右的日本人在大學畢業的時候經歷了求職冰河期,有的人參加幾十家公司的面試,也無法簽約成為正式員工,只能做著合同工的工作。有的人雖然成為了正式職員,卻因為過勞而身心疲憊,不得不更換工作。他們在工作穩定前不結婚不生子,于是變成了晚育一族。中央大學山田昌弘教授說:“可以說結婚生育與經濟相關。因為有強烈的‘不想讓孩子受苦的意識,所以如果不能在寬裕的經濟環境下撫育孩子,人們就不會打算結婚和生子。”
但是晚育也不是只有缺點。
“在今天這個時代,人們可以兼顧工作和育兒,從這一點來說高齡生育也不是壞事。”說這話的是一位47歲的女性,她在43歲時才生下長子,目前在金融公司就職。公司里二三十歲懷孕生子的人基本都辭了工作,沒辭職的少數派工作強度相當大。
她之前不想生孩子,但41歲的時候被診斷出了子宮肌瘤,醫生問她是否要做子宮全切手術。她第一次強烈地有了生子的念頭,于是自然受孕了。
現在她還在做全職工作,活用“每周可在家工作2天”的工作制和電視會議工作系統。如果回到過去,即便有這種制度,受科技等條件的限制,也難以靈活利用。現在的她還有一種為后來人率先試驗的使命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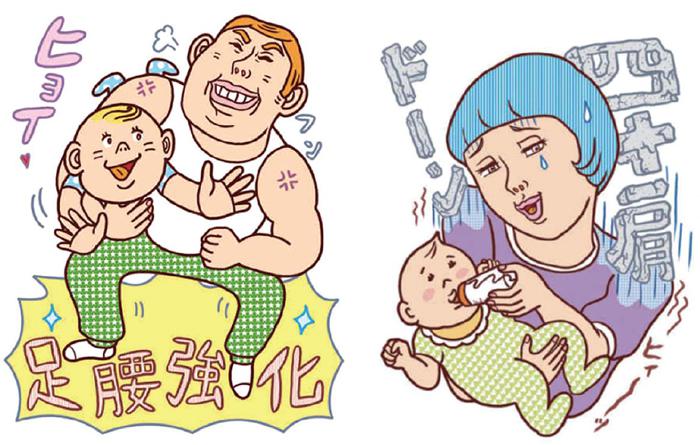
她會在上下班搭乘電車時,在網上訂購食材,第二天東西就會送到家。家里有洗碗機、烘干機、掃地機器人等家電,盡可能節省做家務的時間,擠出時間陪孩子。她既不會放棄工作,也不會放棄育兒。如果她在30歲前后生孩子,是無法享受到這樣的環境的。
女兒成年,我已古稀
高齡做爸爸的男性也有同感。一位52歲的男性的女兒剛剛兩歲,他說:“假如我年輕時就為人父,不會像現在這樣在育兒方面傾注心血。對我來說,現在是撫育女兒的最佳時間。”二三十歲的時候,他每天忙得只能搭乘最后一班電車回家。如今身居管理層的他能夠掌控工作時間,按時回家,帶孩子洗澡,一家三口一起休息。
他在意的是金錢問題,女兒成年的時候,他已到了古稀之年。女兒出生之后,他立刻買了學費保險,但依然感到不安,考慮申請公司自主創業。原本他想把自己對世界豐富的認識傳授給女兒,卻發現女兒的出生讓他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
而另一位51歲的男性則在問卷調查中寫道:“高齡育兒絕不是好事。”他46歲才有了女兒。帶孩子去公園的時候,會被陌生的孩子問:“你是這個小朋友的爺爺嗎?”自己退休的時候,女兒還不到成年,教育費夠不夠呢?
有人將對經濟狀況的擔心轉化為動力。一位46歲的男性4年前有了女兒,對于孩子還未成年自己就會到花甲之年這件事,他感到不安,于是設定了提高收入的目標,獲得了升職,他打算以后將努力的重點放在保持健康方面。
終于成為一家人
幾乎活了半個世紀的男女孕育出一個嬰兒,夫妻關系與生活節奏會一下子發生改變。
東京澀谷的一位41歲女性通過不孕治療,38歲時自然受孕生下了長子,當時丈夫已經49歲了。結婚之后大概6年的時間里,夫妻倆以工作為重,彼此有獨立的世界。有了孩子以后,夫妻的溝通變多了,笑容也多了。她說:“我覺得我們終于成為了真正的一家人,孩子給予了我們人生最大的幸福。”
另一位45歲的女性經歷了4次流產,42歲那年生下女兒。生產時她一度陷入病危狀態,產后因為骨質疏松癥骨折了4次,還患上了肺炎和胸膜炎。但是她沒有太多時間休養。因為高齡生育,她的父母年事已高,不能幫助她帶孩子,相反她還要看護老人,父母生病時去照顧他們。
目前3歲的女兒一出生就患有疾病,在綜合醫院、大學附屬醫院、家附近的診所等等5個醫療機構接受治療,因為手術和檢查頻繁住院,每次都要在病房徘徊。懷孕、生子、撫育孩子,她切實體會到,人是無法自主掌控這些人生大事的。她也不能放棄工作。雖然工作強度無法和生孩子之前保持一致,但她運用培養至今的工作能力彌補了工作強度和時長的減少。她有著必須工作的理由:“我希望女兒長大后,迎接她的是一個女性更易外出工作的時代。”高齡生育給了她無可替代的珍寶,也成為了她努力的動力。
學費與養老錢的平衡
在本刊進行的問卷調查中,一位46歲初為人父的讀者說:“當我60歲退休的時候,孩子15歲,正是需要花錢的年齡。在收入下滑階段準備孩子的教育資金,讓人不禁感到擔憂。如果夫妻雙方的哪一個生病了,生活費也是一個難題。”
如果人到中年才有孩子,會在經濟方面產生強烈的不安。有些人需要面對“沒有收入,孩子的教育費需求卻達到頂峰”的情形。一位44歲的女性最近5年生育了兩個孩子,現在在做兼職工作,她說:“我們打算用丈夫的退休金支付孩子的教育費和住房貸款。”為了退休后還能找到工作,她考取了針灸師資格證。
很多家庭為孩子購買了學費保險,注意儲蓄和節約。但也有人表示“雖然覺得棘手,但沒有采取對策”“還沒有做經濟方面的準備”。40歲以上才做父母的人要如何在家計方面避免風險呢?財務計劃師氏家祥美指出:“這類人群存儲資金的時間比較短。如果不采取相應對策,退休后生活可能會比較困難。”
氏家說,存款的好時機是孩子小學畢業前的幾年時間。父母都有工作的家庭如果要將學齡前的孩子送去幼兒園,那么最佳存錢期就是孩子3歲開始到小學畢業這幾年。再就是孩子大學畢業開始,到父母退休的時間段。但是,如果40歲之后才有孩子,那么孩子大學畢業的時候,自己很快就會退休了,后面這段存錢期過短,那么可以把存錢期定為從孩子上大學到父母退休的一段時間。
除了高額教育費用,還有其他導致困境的因素。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父母大多收入高,社會經驗豐富,對信息敏感,也因此更容易無節制地將錢花在孩子的身上。食物也好,生活用品也好,都優先選擇品質更好的,而不是更便宜的。對孩子的學習也嚴格要求,比如孩子小學和中學都報考私立學校。為了更好的教育環境,不惜金錢。如果沒錢,家長們還會放棄更高的教育標準,但因為當下還有錢,高齡父母容易做出“不管怎樣先投資”的決定。結果導致每月的固定支出增多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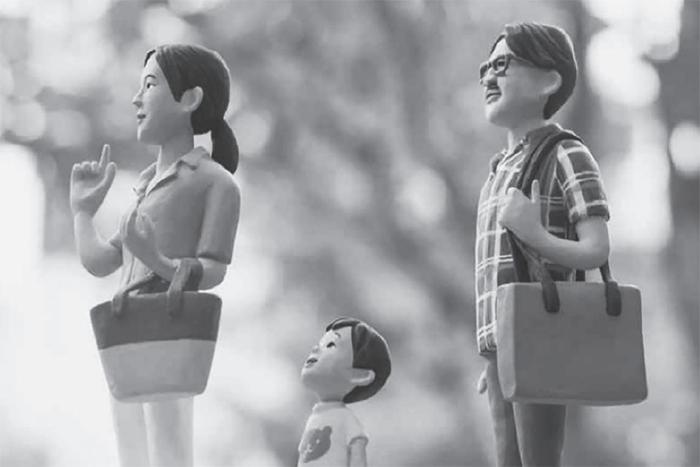
氏家說:“隨著在公司職位的提升,人會變得更忙碌,容易對自己的體力產生不自信,保姆和家務鐘點工費用也會增長。”有些父母因為年齡已高,產子之后自己也需要接受看護,結果一方不得不辭職回家,還要使用自費的看護服務,家庭負擔增加。有些家庭會因孩子的出生而購買房產。此時離退休時間比較短,按貸款年限計算,月供較高,而且退休之后還要繼續還貸款。人生的三大支出項目是“住宅費、教育費、養老費”。可以想象,再上一輩老人的看護費用也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與其他負擔同時出現。氏家強調:“高齡生子的夫妻絕對有必要聊一聊,為今后的人生做好規劃。”
[譯自日本《AERA》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