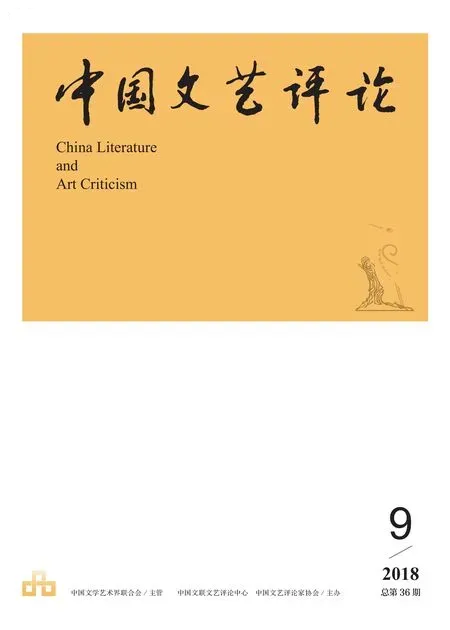20世紀戲劇史視野下的現代主義戲劇
陶慶梅
現代主義是20世紀重要的文藝思想,對于藝術創作的方方面面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戲劇也是如此。但是,現代主義戲劇(乃至整個現代主義藝術)是非常難討論的。這是因為現代主義的產生,伴隨著哲學上理想主義/非理性主義的轉型,它是在質疑、破壞古典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標準的基礎之上,產生的一個具有豐富藝術流派的集合體(在這個意義上,后現代不過是現代主義的延伸而已)。因而,脫離具體的語境,只討論現代主義的理念,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很難說清楚的;而如果我們將現代主義戲劇的發展,置于思想史的整體氛圍與戲劇史的發展脈絡中,置于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話關系中,就有可能更為清晰地把握20世紀的現代主義戲劇發展的脈絡與內在動力,也能更好地理解現代主義戲劇對中國戲劇發展的意義所在。
一、理解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關鍵詞
從時間上來說,現代主義是個20世紀問題。20世紀初期,在繪畫、建筑、戲劇、文學等不同的領域,各種實驗性的藝術不斷涌現,象征主義、表現主義、荒誕派……對于這種種的不同于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的風格與流派,人們將之統稱為“現代派”。現代主義作為對現代派的理論概括,當然是相對現實主義而言的;但如果我們僅局限于藝術理論的規定,從概念出發討論現代主義,就容易迷失于其內部原則的錯綜復雜;而如果我們將它們置于思想史的整體氛圍與藝術史的發展過程中,就會發現,不管我們稱之為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的藝術樣式,它們都糾纏在時代的物質條件與思想氛圍之中,是時代精神的某種藝術折射。一般來說,現實主義是15世紀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精神在藝術史上不斷發展達到的高峰;而現代主義則伴隨著19世紀末期啟蒙主義以來的理性主義在整體上受到的質疑,在藝術表現方式上呈現出的一種“斷裂”。
從這個視角我們就能發現,作為一種藝術手法與藝術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之后的藝術的一次高峰呈現。啟蒙運動之后,在歐洲思想家看來,人,或者說個體,逐漸從上帝/神那兒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他們認為,人/個體,有可能通過自己的“理性”“客觀”地認識、把握自然世界,進而征服自然世界。和這種哲學思想相匹配的,是文藝復興以后,藝術家們也在這種整體的思想框架內,不斷通過繪畫、戲劇、文學……各種方式,力圖發揚人的理性精神,通過觀察,在作品中呈現“真實”的自然世界。“現實主義”某些意義上,就是對這個復雜過程進行的原理性概括;而從這個視角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在一些核心觀念上,也確實是有不同的思考。
第一個核心概念是“真實”。“真實”是個哲學問題。現實主義是“真實”這一哲學問題的藝術方法。這個藝術理念,貢布里希在《藝術的故事》中以“征服真實”(《藝術的故事》第十二章標題《征服真實:15世紀初期》)做了最形象的概括。這個真實,它既來源于文藝復興以來人們對于個人可以通過重新觀察自然,并能通過藝術“征服”自然世界的努力,也內涵著歐洲哲學源頭柏拉圖思想對于作為一種完美“理念”的“真實”的追求。戲劇舞臺對于真實的征服,從文藝復興起,經歷過古典主義“三一律”的極端方式(“三一律”要求的是舞臺時間和戲劇時間的重合),到舞臺布景吸收透視畫法、追求立體布景的逼真效果,最終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臺上完成。
但從繪畫領域開始的“征服真實”在19世紀末期開始遭遇到懷疑。這個懷疑來自于19世紀末,從印象派開始,藝術家們在觀察自然“征服真實”的藝術實踐中,對于什么是“真實”逐漸產生懷疑,對于認識的真實的主觀/客觀產生了懷疑,對于真/假的二分法也開始懷疑。這種懷疑,逐漸成為20世紀哲學認識論的一個主軸,也是20世紀思想的一個大轉折。
第二個是“史觀”問題。啟蒙時代以來,人們對理性主義的信任,使得人們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充滿了信心。人們普遍相信,通過人的理性,人們可以逐漸以自身的力量理解、分析,進而控制自然世界,使之為人類的理性生活服務。這表現在進化論成為人們理解歷史發展的主軸。但從19世紀末期開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負面因素逐漸凸顯,尤其是20世紀爆發的世界大戰,人們對這種線性發展的歷史觀逐漸產生了懷疑。本雅明在他討論《新天使》的畫作中對此作了精彩的描述:
保羅·克利的《新天使》畫的是一個天使看上去正要由他入神注視的事物離去。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
對歷史進步論的懷疑在20世紀催生了歐洲后現代哲學,并在思想層面深刻影響了藝術創作。
第三,怎么理解“個人”。在現實主義背后的強大理性主義傳統中,這個“個人”,是從基督教會那兒獨立出來的個人。是個人可以直接和上帝對話,并且可以通過理性去掌握世界,征服“真實”的個人。這個“個人”,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通過一句臺詞對此有過精準的表達:
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但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伴隨著非理性思想的崛起,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為代表,以“科學”的方式發現,在理性之下,有著更為復雜的非理性世界。如果每個個體的理性都有非理性的一面,那么,這個混合著理性與非理性的個人,又該怎樣描述呢?正是這些哲學上的關鍵詞,構成了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轉型過程中內在的思想動力。藝術呈現是表象,而這些問題卻是推動藝術呈現方式變化的內在要素。因而,本文在討論戲劇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關系時,會圍繞著這些核心問題加以辨析。
此外,在討論戲劇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之前,必須強調一下,戲劇是由兩種最基本的要素構成的,一是文本,一是劇場與舞臺。戲劇文本,是那些戲劇家通過戲劇文學呈現自己的思想與戲劇觀念。從易卜生到布萊希特、貝克特,一直到今天,諸如《枕頭人》《4:48精神崩潰》等作品,戲劇文學的創作有一條自己的發展脈絡;而且,這些作品有時也可以脫離舞臺演出獨立存在,具有自身獨立的意義。
但戲劇和文學、詩歌最大的區別在于,戲劇文本是需要在舞臺上演出的。20世紀的現代主義戲劇,在藝術理念與舞臺物質條件變化——包括劇場的形態,舞臺燈光的技術水平等——的雙重作用之下,舞臺表現也出現了層出不窮的變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戲劇文學也一直對舞臺提出挑戰。比如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向習慣了寫實布景的舞臺演出提出了一個挑戰:“一條路,一棵樹”,該怎么處理?
20世紀以來的戲劇文學一直在給劇場提出挑戰。而20世紀的戲劇史在某些意義上也是在回答這個挑戰過程中擴展了戲劇的邊界。
二、現實主義的原點
我們說現代主義是在質疑現實主義原則的框架下發展;我們也會發現,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又確實是一組辯證的關系。從具體創作中我們就會發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高峰的創作者,在他對現實主義原則——思想的與藝術的——不斷追求的過程中,在他自身到達現實主義高峰的那一刻,也是他自我懷疑的那一刻——易卜生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是如此。
1. 從易卜生談現實主義戲劇文本
易卜生一方面是現實主義戲劇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又是現實主義的破壞者。易卜生的現實主義戲劇發展過程也很漫長。早期代表作《培爾金特》,那種大開大合的時空觀完全是超越現實主義舞臺的,顯然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現實主義戲劇作品。但易卜生的中期作品,尤其是易卜生在歐洲大陸的一些主流劇院工作過之后完成的作品,從《培爾金特》《布朗德》這樣帶有詩劇意義的作品,轉變成了《社會支柱》《人民公敵》《玩偶之家》這樣被我們今天稱之為“現實主義”戲劇的作品。易卜生這樣的一個轉變,與歐洲大陸法國人安圖昂在法國以“自由劇場”名義演出自然主義戲劇的實驗相呼應。戲劇的舞臺表現,逐漸從以詩劇化、浪漫劇化的舞臺風格,走向了以中產階級社會生活為表現內容、具有生活寫實感的表現方式的現實主義戲劇。
易卜生的現實主義戲劇有幾個要點。從戲劇文學來看,首先,他的戲劇文本創作,舞臺集中在資產階級家庭;其次,他的戲劇文本是以清晰的人物關系與明確的人物對話來組織的;再次,他關注的是當時社會的思想議題。在易卜生的劇本中我們發現,經歷過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后,與資產階級并生的中產階級在20世紀初期興起,成為歐洲社會主要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隨著這個社會結構變化而來的,是這些構成社會主體的中產階級的家庭,逐漸取代了貴族的城堡,成為劇本的角色——也是劇場里的觀眾——的活動中心;而他們之間的人物關系、他們的對話方式、他們的心理問題,也被易卜生以精準的戲劇手法呈現了出來。
但我們說易卜生是大師,是他從來不滿足于自己開創的一個流派而不斷往前走。易卜生的中晚期作品,像《建筑大師》《野鴨》《約翰·蓋勃呂爾·博克曼》,雖然還是集中以人物對話為表現方式,但顯然更著重在人物的內在心理起伏。這樣的心理起伏在小說描寫中比較容易,而易卜生為這樣的內心,創造性地發展出一些帶有心理外化特征的“意象”——野鴨也罷,《約翰·蓋勃呂爾·博克曼》中的腳步聲也罷,《建筑大師》中通往云端的樓梯也罷——這些都是人物心理外化的某種舞臺意象。易卜生最讓人敬佩的是他一直在突破。在戲劇文學的表現上,不僅把話劇從現實主義發展到象征主義,他在最后一部作品《當我們死人醒來時》中又回到詩劇的創作方法,為以后各種戲劇文學表現打開了新的空間。
易卜生的創作的確是集大成的。他用戲劇文學把現實主義戲劇帶到了一個高峰,但他自己又從這個高峰不斷地往前走。易卜生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他在戲劇文學上的創造性表達,而且,他還通過自身的戲劇文學,一直在回答現代性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理解“個人”?
“個人主義”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中有著非常不同的方向。在“五四”“新青年”的語境中,《玩偶之家》因為其獨特的意義,與當時新文化運動所鼓吹的沖破舊家庭的語境相結合,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但其實,易卜生的個人主義,并不是鼓吹婚姻自由,也不是要鼓勵沖出家庭的藩籬。在易卜生的語境中的“個人主義”,是啟蒙思想中從教會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個人,是通過自己選擇和上帝的關系確立自己行為的個人。比如《群鬼》里的阿爾文太太說,她本來以為,“在你(牧師)把我深惡痛絕的事情說成正確的、合理的事情”,她發現“本來只想解開一個疙瘩,誰知道一個疙瘩解開了,整塊兒的東西就全都松開了。我才明白這些東西是機器縫的”。
而易卜生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一直在不斷地懷疑自己。他的懷疑自己不僅表現在戲劇文學的表現樣式上,而且還是在對于個人的思考上。在《玩偶之家》《人民公敵》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于個人主義充滿信心的易卜生;從《群鬼》《野鴨》開始,我們明顯看到對人充滿信心的易卜生開始了懷疑。比如《群鬼》里的阿爾文太太如同娜拉一樣,她已經揭開了社會虛假的面紗,向著虛假的社會開始了毫不留情的挑戰。但是,這個拆開了社會許多荒謬之處的阿爾文太太,這個耗盡了一生的心血想把自己的兒子從舊的世界中拯救出來的阿爾文太太,忽然面對的卻是兒子央求母親殺死自己:“這是什么樣的生命啊!我沒有要這樣的生命,你把它拿回去!”離開了舊世界的個體,還承擔不了被孤零零地拋棄在世界的責任,承擔不了自己的命運。《群鬼》已經在文學層面上開啟了存在主義的先聲。易卜生自己發現,當他在《玩偶之家》里讓娜拉可以在海爾茂面前宣布牧師、律師以及丈夫都不重要,自己要離開家庭建立自己的人生的時候,他也許并沒有想到,這個個人有一天會發現,他是不能完整地承擔自己的。這樣的思想從《野鴨》開始,到《群鬼》《建筑大師》,最后到《當我們死人醒來時》。易卜生是在非常嚴肅地思考個人在現實中的存在問題。
易卜生不僅在藝術樣式上已經預言了20世紀的變化,而且,他通過他的“詩”,表達了對于個人的毫不遲疑、毫不妥協的探究。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話關系,也正在此。
2. 現實主義的舞臺與表演
戲劇難以研究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很難身臨其境到一百多年前的演出現場。所幸,斯特林堡寫于19世紀末期的名作《朱麗小姐》,留下了一段序言,為我們描述了當時主流劇院的劇場與舞臺。
如果我們能取消人人都看得見的樂隊,因為它們使用的燈光對觀眾有干擾作用,他們的臉正對著觀眾;如果我們能把觀眾席的前排座位提高,讓觀眾的眼睛看到演員的膝蓋以上;如果我們能把那些人們哧哧地笑著吃晚餐和女人喝酒的包廂去掉,并且在演出過程中讓觀眾席完全黑暗,而且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小舞臺和一個小劇場,那么就有可能出現一種新的戲劇形式。
這是斯特林堡在19世紀末寫《朱莉小姐》的時候劇場的樣子。
這一小段序言包含了幾個重要的信息:在歐洲傳統劇場,原來的觀眾池座是凹下去的,非常不適合觀看演出;而且,劇場在演出的時候是不關燈的。這說明在100年前劇場不僅僅是演戲,更重要的是它是個社交場所。這一點,在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里都有詳細的描述。
斯特林堡的這一段序言,非常清晰地說明了歐洲大陸在20世紀初期開始推動小劇場運動的原因。安圖昂當年在法國選擇“小劇場”作為實驗戲劇的場所,除了小劇場的便宜之外,也有他在戲劇美學上的追求。他反對戲是社交、商業行為的附屬品,他希望觀眾觀賞戲劇,是在劇場內嚴肅地思考現實生活的問題——他通過排演左拉的自然主義戲劇,通過運用真實的家庭道具,通過去除浮夸的表演風格,要創造一種20世紀的真實舞臺。這種追求“真實”的努力,從安圖昂開始,經由梅寧根公爵劇團,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達到了現實主義舞臺與表演的高潮。
如果說易卜生的戲劇文學是現實主義的集大成,那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顯然是為這樣一種戲劇文學樣式,找到了最準確的舞臺表現;而且,最為難得的是,他為這樣的舞臺表現,建立起了最為難得的表演訓練方法。
我們可以以《海鷗》為例來說明現實主義戲劇舞臺表現。《海鷗》的第一句臺詞是:
麥德維堅科:瑪莎,你為什么總穿黑色的衣服?
瑪莎:我為我的生活戴孝。
這是《海鷗》劇本的第一句臺詞。在此之前,沒有任何鋪墊,也沒有任何解釋性的語言。對話的雙方,瑪莎是管家的女兒,問瑪莎的麥德維堅科是當地的小學教師。麥德維堅科一直在追求瑪莎,而瑪莎愛的是貴族公子特里波列夫。如果不去考慮這兩個人的身份,這句臺詞很像兩個“文藝青年”在對話。但考慮到瑪莎是管家的女兒,考慮到這兩個人物之間的關系,穿越話語本身去看這個場面,就會發現這是個喜劇:瑪莎的身份是仆人,但她說的卻是貴族小姐的話;這句話本來不該她說出來的。這就是契訶夫的“喜劇”。在契訶夫的喜劇中,沒有任何意大利喜劇的動作性沖突,就是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通過他們自己的話,揭示出這其中每個人對自己的認識是錯位的。正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認識錯位,人就總會在糊里糊涂的喜劇中演出一幕幕的悲劇來。
契訶夫對生活的觀察太透徹了。而且他能把他對生活的冷靜觀察,化作冷靜的臺詞在文本中呈現。但怎么演?怎么把不同人物的內心通過表演“演”出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迎難而上,要為這種“真實的生活”尋找到一種表現方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開始是一個演員。他非常自覺地根據現實主義的要求整理自己的表演經驗,整理自己在舞臺上是如何失敗,然后又能如何避免這些失敗。而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表演、舞臺上往現實主義發展的時候,契訶夫的劇本給了他最好的入口。在不斷試錯的基礎上,他總結了一套關于“體驗”的表演理論,并且,他發展出一套與這種表演理論相匹配的訓練方法。
20世紀的現實主義的基本框架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這兒形成了。它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在戲劇文學上,它是以創作者對現實生活為基本觀察、描述與思考對象,通過較為逼真地還原現實生活的質感,探討當下的社會與思想問題;在舞臺表現上,它是通過相對寫實的舞臺布景,通過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為中心的“體驗派”表演訓練,塑造帶有鮮明生活質感的舞臺人物,創造出帶有“生活幻覺”的舞臺表達,以期讓觀眾切入到生活的真實感受中。
當然,戲劇的現實主義特性,又是很復雜的。比如易卜生的現實主義戲劇和契訶夫的現實主義戲劇不完全相同;而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的契訶夫作品和莎士比亞作品也不相同。但總的來說,現實主義戲劇的基本語境,是相信人通過理性能夠把握世界的真實面貌,并相信戲劇家能夠將這種真實面貌“如其所是”地呈現給觀眾,讓觀眾透過舞臺的幻覺,抵達現實生活的內在動力與人物的思想情感。也許正因為現實主義是難以描述的,我們發現,后來越來越多關于現實主義戲劇的討論,在文學上往往被簡化為“現實題材”與“社會問題”,在表現上也往往簡化為生活化的表現。這其實就完全弱化了現實主義戲劇舞臺的深度。
如同易卜生在戲劇文學的創作上,遵循著自身對真實、個人等問題的探討,不斷以象征等方式做突破一樣,舞臺上,伴隨著20世紀燈光技術的進步,舞臺上的“生活幻覺”也不斷被打破。只是,舞臺實踐要比文學實踐困難得多。縱觀20世紀戲劇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無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學生梅耶荷德、格洛托夫斯基,還是受他影響的布萊希特,都在“體驗派”的基礎上,執著地探討舞臺表達的新方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是一組深刻的對話關系,而不是簡單的逆反。
三、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不同對話關系
如果我們深入到現代主義的發展,就會發現,在我們籠統地稱為“現代主義”的普遍原理之下,歐洲現代主義,也是因為各個民族國家的自身傳統、各個民族國家在20世紀的獨特問題,現代主義的面貌其實非常不一樣。從現代主義戲劇的發展歷程來看,在意大利假面喜劇傳統的基礎上,皮蘭德婁通過自身的藝術創造,對于真/假問題做了杰出的回答;德國以強大的表現主義繪畫為基礎,發展出強大感染力的舞臺表現,在此基礎上,布萊希特最終創新出敘述體戲劇;法國在強大的意識流文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礎上,以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給予了一次總結性的呈現;而在波蘭濃郁的天主教氛圍中,格洛托夫斯基帶有宗教色彩的“質樸戲劇”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也逐漸產生影響。
1. 皮蘭德婁與意大利假面喜劇傳統
意大利現代主義戲劇的代表性人物是皮蘭德婁。皮蘭德婁192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在獲獎時已經有兩部代表劇作:《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與《亨利四世》。這兩部作品很好地說明了皮蘭德婁的現代主義戲劇理念和意大利假面喜劇的傳統有關。《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亨利四世》這兩部作品,都以明顯的扮演關系,作為戲劇的推動性結構。
如《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是一個典型的戲中戲結構。它的基本框架是一個劇團要演出一部倫理悲劇;但在排練的過程中,演員們所扮演的人物突然闖入劇場,認為他們演的不好,他們要自己出演自己的故事。這個戲中戲的倫理悲劇,是一個家庭故事。母親年輕時和人私奔,但最終衣食無著,不得不讓自己的女兒去賣淫;而父親在妓院里突然發現,他找的妓女其實是他的女兒。最終,在這個家庭的沉郁氛圍中,小女兒淹死,小兒子自殺,一家人最終崩潰。世界上這樣的倫理悲劇太多了,如果這只是一個倫理劇的話,諾貝爾獎為什么要授予他?前兩年,俄羅斯導演在排演《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對這個戲中戲的結構做了特別細致的解讀,也讓我們得以更為清晰地理解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
這個導演的排演特別突出了這是一個戲中戲——這里是扮演關系!扮演意味著:這不是真的。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段,是這幾個劇中的角色不滿意這幾個演員的扮演,他們要自己上場去演自己。這時,導演的調度中,“劇中人”在中間演戲,在舞臺兩側坐的是扮演演員的演員,演員的后面才是觀眾;最為奇妙的是,在觀眾與演出之間,有一池水倒映著整場演出。
導演的這種處理,清晰地揭示出《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的本來面目。皮蘭德婁從假面喜劇的傳統中來,把假面喜劇的方式編織到現代戲劇文本中,他想通過扮演的方式去討論,對于觀眾來說,你所看到的哪個部分是真實的?真和假是不是沒有那么絕對?皮蘭德婁是以戲劇文學的方式,直接回應了歐洲20世紀的哲學認識論問題。我們要明白,對于中國人來說“假作真時真亦假”是特別簡單的道理,而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卻是認識論的痛苦轉折。
2. 法國:現代文學與貝克特的《等待戈多》
某種意義上,巴黎是19世紀的世界之都,是歐洲藝術家都向往的藝術之都。20世紀初期,法國是個思想活躍的地方。很多現代主義思潮,都是在巴黎誕生并被發揚光大的。現代戲劇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貝克特及他的代表作《等待戈多》,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現。
《等待戈多》在戲劇史上是一部極為特殊的作品。這樣一個作品,在文學性上,在戲劇文本上,對現代劇場提出了非常嚴肅的挑戰。貝克特可以說是跨時代的大師。在那之前,無論是馬雅可夫斯基、皮蘭德婁,他們寫作的文本還是在原來現實主義“戲劇”的框架里做小的突破;他們的作品,不管是詩劇還是戲中戲,都還是有人物、有結構的基本形狀,但在《等待戈多》這兒,貝克特完全打碎了現實主義的關于人物與結構的基本規定性。《等待戈多》的世界,是兩個不明身份、不明來歷的抽象的人在一個非常抽象的語境當中——荒原,一棵樹—— “胡亂”的對話。
對于中國讀者,也包括日本、韓國這樣的東方讀者來說,理解《等待戈多》就更為困難了。《等待戈多》里其實隱藏著一個前文本——《圣經》。《等待戈多》的很多“胡言亂語”是建立在歐洲觀眾對《圣經》很熟悉的基礎上。在《等待戈多》中,一個觀念的表達,緊接著會冒出一個推翻這一觀念的觀念,貝克特對自己所引用的觀念的懷疑,把意義落在觀念與觀念之間。如果對貝克特所引述的觀念本身就很陌生的話,要理解《等待戈多》著實困難。
比如說弗拉基米爾給愛斯特拉岡講故事:
弗拉基米爾:故事講的是兩個賊,跟我們的救世主同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有一個賊——
愛斯特拉岡:我們的什么?
弗拉基米爾:我們的救世主。兩個賊。有一個賊據說得救了。有一個……萬劫不復。
愛斯特拉岡:得救?從什么地方救出來?
弗拉基米爾:地獄。
這兩個人討論的前提是,絕大部分西方人知道的福音書里四本福音書對于耶穌受難的具體細節描述是不一樣的。救世主有沒有救在他身邊的那兩個小偷?得救又是什么意思?是說他們也復活了,還是他們被救世主從地獄救到天堂?對于熟悉《圣經》的歐洲人來說,他們很明白貝克特是用反閱讀的方式來重新閱讀最神圣的文本。
用貝克特自己的話來說,他是“發現一種形式,使它能與雜亂無章妥貼地配合起來”。他在發現自己的形式的過程中,一方面不斷吸納歐洲民間傳統中活躍著的宗教劇的戲劇形式,改變它的走向,修正它的意圖;另一方面,他又確實扎根在20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語境中,延續著法國詩歌與文學關于“荒原”的意象。在呈現上,有些地方,就是他的文字游戲;有些地方,又是他用歐洲中世紀戲劇中的雜耍為舞臺調色。他確實是用戲劇的方式,延續著尼采“上帝死了”的討論,呼應著歐洲大陸的存在主義思想。但如果太抽象地理解他的每一句臺詞,覺得處處是真理,《等待戈多》是沒法演出的。
3. 德國:表現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布萊希特
德國最為精彩的當然是它的表現主義傳統。德國表現主義之強大,大概是與它19世紀的浪漫主義傳統相關——浪漫主義直接啟發了表現主義。作為歐洲后發國家的德國,在他開展工業化與現代化道路的開端,從英國蔓延到歐洲大陸的工業化道路已經很清晰地呈現出現代性的弊端。德國、俄羅斯等國在開啟現代化的進程時,在思想上,就已經有強烈的民族性與宗教性對于現代性做出一定的反省。這種浪漫主義、表現主義,在哲學上的高峰代表自然是尼采;在藝術上,它體現在繪畫、詩歌、文學等各種藝術形式上。在戲劇舞臺,從萊因哈特到皮斯卡托,都自覺地把表現主義的藝術手法帶進了戲劇舞臺。在反省現代性的表現主義基礎之上,最終形成了布萊希特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戲劇觀與戲劇創作。
布萊希特是一個藝術思想上的雜家。早年,他在表現主義陣營,和盧卡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做過論戰。但他并沒有停留在表現主義,而是延續著個人與社會關系、文藝與社會關系的思考,將現實主義戲劇帶到了一個新的方向。
布萊希特的基本戲劇觀是認為文藝是可以改造社會的。這是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集中表現。正是在這種藝術觀的基礎上,他提出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史詩戲劇,或者敘事體戲劇。“史詩”戲劇與敘述體戲劇是布萊希特自己在不同時期針對不同問題時所持的理念。他用史詩戲劇的概念是他在與亞里士多德對話。亞里士多德把藝術分為史詩與戲劇不同門類——這兩個文藝種類的區別在于敘述方式。布萊希特認為,戲劇的表達方式也可以是如《荷馬史詩》那樣用敘述體來表達。但是,為什么要使用敘述體戲劇?
布萊希特要將“敘述”的概念帶入到戲劇之中,是因為他要回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以創造“舞臺幻覺”為目標的戲劇表現。布萊希特要用“敘述”的方式,打破舞臺幻覺;而他之所以強調打破舞臺幻覺的重要性,是要通過打破舞臺幻覺的文藝方式,實現觀眾重新認識現實生活、打破對現實生活的幻覺——也就是說,他要打破的幻覺不只是藝術上的幻覺,而是要使觀眾認識到現實生活中的生產關系,認識到為什么人會剝削人,認識到為什么人會壓迫人。
布萊希特的敘事體戲劇其實對歐洲戲劇影響特別深遠。我們現在所崇拜的大師,比如彼得布魯克,到中國來演出的他的作品,都是敘述體的。但他們和布萊希特的不同,就在于背后的價值觀與哲學思想。
布萊希特是個特別能創造概念的藝術家。他用敘述體/史詩劇的概念,直接反對的是西方戲劇理論之源——亞里士多德戲劇觀。與此同時,在藝術表現方式上,他也一直試圖尋找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同的藝術語言。他在觀看過梅蘭芳的京劇表演后受到啟發,將他尋找到的在舞臺上打破幻覺的種種手法,在理論上命名為“間離”。也就是說,間離不是他對中國京劇表演方式的總結,而是他用京劇表演的方法,來命名自己的敘述體戲劇想確立的藝術風格。
4. 波蘭:格洛托夫斯基與阿爾托的殘酷戲劇
波蘭最重要的戲劇理論著作當屬格洛托夫斯基的《邁向質樸戲劇》。當然,《邁向質樸戲劇》不能算是嚴謹的理論著作,這是一本集合著訪談與訓練方法的作品;不過,也正是在這部作品中,格洛托夫斯基將自己的理論溯源到了阿爾托的“殘酷戲劇”。
阿爾托的“殘酷戲劇”的理念,本來就是歐洲非理性主義哲學傳統中重要的一股力量。阿爾托的思想,表達的是對人類進步、人類理性等啟蒙主義思想命題的懷疑,同時,伴隨著歐洲對東方的殖民過程,逐漸轉向了印度、東印度的神秘主義思想。格洛托夫斯基受哲學家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的影響,正在于他非常強調戲劇神圣性的一面,認為戲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使人回到原本和神的關系當中去。但阿爾托的殘酷戲劇基本是哲學理念,格洛托夫斯基則嘗試把這套理念用演員的表演來實現。格洛托夫斯基也明顯受到20世紀中期東方神秘主義的影響,他從印度瑜伽、巴厘島舞蹈要素里尋找演員的訓練方式,讓演員的身體可以有特別強的表現力。
格洛托夫斯基在《邁向質樸戲劇》中確實發展了殘酷戲劇的命題,創造了“神圣的演員”這個概念。“神圣的演員”,意味著戲劇對人的要求,對演員的要求。這個要求是每個演員要成為一個和神有關系的人;觀眾可以通過演員,與神重新建立聯系。這種神秘主義思想,總的來說,有著強烈的東方神秘主義特性,但應該也與波蘭濃郁的天主教氛圍相關。格洛托夫斯基和追隨他的演員一直在山里訓練,并成立了研究所。幾年前,研究所在中國演出了一部作品叫《鹽》。舞臺上,滿地的玻璃,鹽不斷地從天花板上往下掉;演員身體的動作,是經由非常艱難的訓練所能達到的某種靜止。演員的身體一看都是長期訓練出來的,所有肢體的每一塊肌肉似乎都可以說話。他們通過這樣的身體,向觀眾傳達一種來自生命本能的痛感。這個痛,不是因為失戀了,不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是生命本身帶有原罪的痛感。
四、在自己的傳統中創造當代戲劇理論
通過以上簡單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歐洲不同民族國家是在自己民族傳統基礎上,在與現實主義的對話過程中,形成了我們今天統稱為“現代主義”的不同流派;在今天,隨著我們在中國就幾乎能同步欣賞到歐洲當代劇場的作品,我們還可以發現,現代主義的戲劇觀念與藝術手法,至今仍然在歐洲的舞臺上活躍,而且很可能已經成為歐洲主流藝術的一部分。
如2017年在烏鎮戲劇節演出的由圖米納斯導演的《葉普蓋尼·奧涅金》,其中包含著現代主義戲劇的一些基本要素。首先,從表演上看,他的演員明顯有著梅耶荷德有機造型術的影響。舞臺表演對于身體造型也有著嚴格的要求,很多時候,是演員的身體在充當情感塑造的方式。從敘述方式看,這部作品明顯受布萊希特敘述體的影響:劇中,老年奧涅金是主要敘述者,連斯基與驃騎兵的敘事穿插在其中,三個人在不同場景的敘事,代替原著中的作者敘事。這種敘述方式,確實使得這部作品在表現奧涅金與塔季亞娜的愛情上有所突破。比如,塔季亞娜的命名日那一場,導演正是通過老年奧涅金的敘述視角,把他老年時覺得人生最懊悔的那一個剎那,人為地拉長了。在這一場,塔季亞娜一直在忐忑地盼望著奧涅金的到來。舞臺上,塔季亞娜站在稍微高點的凳子上,來人,停頓,祝福。停頓了三到四次,奧涅金上場。他轉了一圈,結果把奧爾加的手一拉兩人開始跳舞,之后奧涅金還調戲奧爾加。這段演出,停頓非常多,時間也就很長——甚至會比現實時間還要長。正是這種人為的拉長,特別強調了老年奧涅金對這段愛情的懊悔,加深了這部作品的感傷情調。
如果將當下歐洲戲劇的表達,與上文所述原初的現代主義戲劇實驗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當前的歐洲現代主義戲劇,基本上是延續、發展了不同的現代主義戲劇手法;但是,脫離了創造出這些藝術手法的哲學語境與思想背景,今天許多現代主義的演出,普遍會缺乏深度。
比如近年來我們看到的很多在中國演出的德國當代劇場作品,仍然帶有強烈的表現主義特質。如德國中生代導演代表人物奧斯特瑪雅,在他導演的《理查三世》舞臺上,他不僅可以通過造型把理查塑造得非常丑陋,而且在理查說服安夫人嫁給他的那一場,可以讓舞臺上的理查直接裸體,用強奸的方式說服安夫人。德國的表現主義傳統,使得他們的當代導演總能制造出特別強烈的現場感,他們更著重用各種刺激感官的表現方式去刺激、挑逗觀眾。但這樣一種表現方式,沒有更深刻的哲學思想與社會關懷做支撐,容易流于表面。
因而,在我們當前快速引進當代歐洲劇場的過程中,不難發現,我們是面向一個技藝上不斷推進的戲劇藝術,面向文學對于舞臺提出的挑戰,面向歐洲知識分子的藝術思潮——但是,這樣一個思潮和我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我們不能被當前歐洲現代主義戲劇的各種變奏所困惑,還是應該回到原點,回到歐洲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對話關系中,尋找建設我們自身戲劇理論的途徑。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與藝術理論,深受西方文藝理論思想——不管是前蘇聯的文藝思想還是20世紀中葉以來的歐洲現代主義思想——的影響。因而,要建構自身的文藝理論思想,我們不太可能完全脫離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完全從傳統的語言系統中發明出適合當今文藝創作的理論。但是一直以來,在強大的西方文藝理論話語的壓力之下,我們除了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內部做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之外,在尋找自身的理論話語的過程中,并沒有系統的理論建設。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理論困境,首先是因為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藝術思想主流的“現實主義—現代(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框架與概念譜系,確實對中國的文藝創作與文藝思想有著壓倒性的優勢。很多時候,我們往往非常概括地以“現實主義—現代(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框架,有些粗暴地以一些簡單的概念范疇,來分析討論可能原理上與此非常不同的中國文學藝術形式。因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們的文藝理論思想的建設,面臨著雙重使命:一重使命是要把籠統的“西方”還原為具體的西方:即把現實主義、現代—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話語,還原到具體的場景——歷史的場景與文藝類型的場景;另一重使命,就是立足當下的文藝創作,從創作實踐出發,及時地總結、提煉,建構自身的理論語言。
本文的重點,就是力圖從戲劇這樣一個具體藝術形式出發,深入到西方文學與藝術發展的內部,在西方20世紀文學藝術的理論話語框架中,把西方“具體化”,把理論“具象化”。本文即是要通過辨析歐洲不同的民族國家,因為各自民族的不同歷史、遭遇的不同問題形成的不同藝術風格與理論流派,思考如何以自己的民族傳統為基礎,在與各種不同的外來思潮碰撞過程中,建構中國自身的戲劇理論語言,創造出屬于中華民族現代化的“現代藝術”。我們要知道,由于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歐洲20世紀的文化傳統差異太大,因而我們的創造也一定會比歐洲國家更為艱難。但只要我們不丟掉自己的文化基礎,只要我們對自身的文化表達有理解、有自信,這樣一種經由自身民族傳統與現代生活而來的“現代藝術”,也一定會在當代舞臺上收獲來自世界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