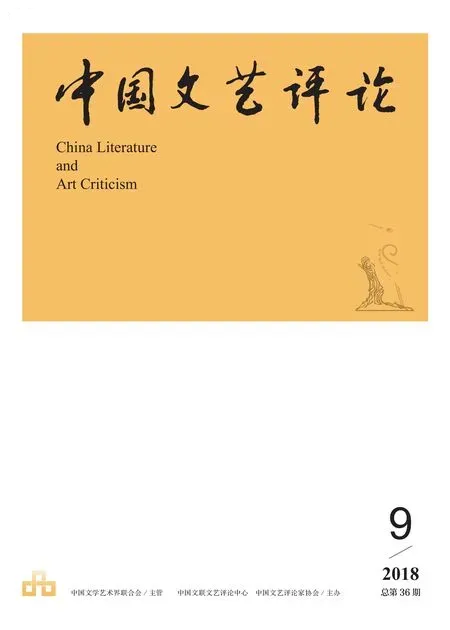從《經(jīng)典詠流傳》看歌曲的經(jīng)典化方式
陸正蘭
歌曲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shù)體裁之一,它具有藝術(shù)審美功能,亦是個(gè)人與個(gè)人,個(gè)人與群體、集團(tuán)之間的交流媒介。隨著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當(dāng)代歌曲作品生產(chǎn)數(shù)量迅猛增長(zhǎng),各種風(fēng)格的歌曲層出不窮,如何在這些眾多作品中引領(lǐng)大眾,尤其是青年受眾?如何選擇有文化價(jià)值的經(jīng)典歌曲,并讓這些經(jīng)典作品走入人心,做到真正流傳?本文試圖以近年一些成功的歌曲類電視節(jié)目為例,探討經(jīng)典與流傳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歌曲經(jīng)典化的特殊方式。
一、社會(huì)選擇與歌曲的經(jīng)典化
經(jīng)典,即一個(gè)成熟文化從歷代積累的大量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選出少數(shù)公認(rèn)的精品。經(jīng)典化,指經(jīng)典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不斷更新。經(jīng)典化離不開(kāi)兩個(gè)環(huán)節(jié):社會(huì)選擇與歷史保持。對(duì)任何藝術(shù)品,文藝評(píng)論家、傳播機(jī)構(gòu)、接受者大眾等都可以參與經(jīng)典的社會(huì)選擇與歷史保持,但幾方起的作用不同,且在歷史不同時(shí)期的側(cè)重點(diǎn)也不一樣。
比如歷史上的文學(xué)經(jīng)典主要依據(jù)精英批評(píng)家們的挑選,就像六朝鐘嶸的《詩(shī)品》,在122名詩(shī)人中挑出上品12人,靠的是比較,依據(jù)標(biāo)準(zhǔn)是仿漢代的“九品論人,七略裁詩(shī)”。而當(dāng)代文化對(duì)經(jīng)典的選擇似乎有些變化,多了另一種經(jīng)典化的方式,即“群選經(jīng)典”。正如學(xué)者趙毅衡所論:“群選經(jīng)典的名家,是群眾需要的文化世界的提喻,大眾無(wú)法接觸全部藝術(shù)家,于是他們選擇一人或某幾個(gè)人,作為文化的替代性提喻,而每個(gè)時(shí)代面對(duì)一個(gè)新的文化,會(huì)需要自己的提喻。”當(dāng)前這種大眾群選經(jīng)典化,主要靠投票、點(diǎn)擊、購(gòu)買、閱讀、觀看方式,以達(dá)到積聚人氣和數(shù)量的連接。它們和精英式的批評(píng)相比,往往更注重從人到作品,而不是從作品到人。這兩種經(jīng)典化方式有時(shí)會(huì)互相抵觸,但它們?cè)诋?dāng)代社會(huì)共存,都對(duì)文化的傳播發(fā)生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的藝術(shù)門類都遵循一種經(jīng)典方式。藝術(shù)門類的不同,同樣制約著經(jīng)典的產(chǎn)生。歌曲經(jīng)典化,既不同于精英批評(píng)家的挑選,也不完全由大眾的群選決定,它與其他藝術(shù)門類的區(qū)別在于:聲樂(lè)教學(xué)雖然是學(xué)校的一科,但學(xué)院派批評(píng)價(jià)值有限。媒體機(jī)構(gòu)的批評(píng)可能在某種特定時(shí)期對(duì)某種特定種類起作用,但商業(yè)化包裝(例如今日的網(wǎng)絡(luò)媒介,排行榜,歌單)成功的把握并不大。因此,大部分歌曲的流傳,主要靠媒體引導(dǎo),歌眾選擇,靠歌眾自覺(jué)傳播,因而成為經(jīng)典。
中央電視臺(tái)綜合頻道和央視創(chuàng)造傳媒聯(lián)合制作的詩(shī)詞文化音樂(lè)節(jié)目《經(jīng)典詠流傳》,是一個(gè)值得分析的佳例。《經(jīng)典詠流傳》是一臺(tái)大型文化節(jié)目,自2018年大年初一推出第一期以來(lái),至今已有多期,每期都獲得受眾的好評(píng)。它以生動(dòng)、時(shí)尚的形式,復(fù)活了中國(guó)獨(dú)特的歌詩(shī)傳統(tǒng),傳播中華詩(shī)詞文化經(jīng)典,吸引了中國(guó)青少年的眼光。它之所以獲得成功,是由詞曲作品、傳播機(jī)構(gòu)、演唱者以及接受者大眾等的合力決定的。
首先,詞曲是一首歌的意義中心。《經(jīng)典詠流傳》中反響很熱烈的歌曲之一是《苔》。這是一首300年前清代詩(shī)人袁枚創(chuàng)作的無(wú)名小詩(shī),并不列在我們所熟悉的唐詩(shī)宋詞的經(jīng)典目錄中,演唱者也不是為人熟知的明星歌手,而是普通的鄉(xiāng)村教師梁俊和他的學(xué)生,以樸實(shí)的曲調(diào),演繹了“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lái)。苔花如米小,也學(xué)牡丹開(kāi)”的境界。一首小詩(shī)穿越古今,靠的是被普通民眾挑選和演唱,靠的是“苔花”的提喻功能。正是在這個(gè)時(shí)代語(yǔ)境下憑借大眾情感的經(jīng)典提喻,傳達(dá)了當(dāng)代社會(huì)中普通大眾身處平凡卻積極向上的精神風(fēng)貌。這首歌完成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提喻功能,因而廣為流傳,成為新的經(jīng)典。
其次,傳播機(jī)構(gòu)媒體的推廣也非常重要。中央電視臺(tái)綜合頻道作為影響力極大的傳播媒體渠道,它鼓勵(lì)歌眾往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價(jià)值觀方向釋義。新釋義場(chǎng)的構(gòu)筑,的確會(huì)創(chuàng)造歌曲的“新解”,而大眾所喜愛(ài)的歌星的演繹會(huì)有助于歌眾傳播,它推動(dòng)了一首經(jīng)典歌曲變成無(wú)數(shù)個(gè)歌眾口中、心中的歌,他們自己的歌,這樣一首歌就變成了廣為流傳的歌。
其三,演唱者的身份會(huì)提升歌曲的傳播效應(yīng)。《經(jīng)典詠流傳》中有一首東漢劉楨的詩(shī)《亭亭山上松》:“亭亭山上松,瑟瑟古中風(fēng)。風(fēng)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由體育明星孫楊選擇在節(jié)目中演唱,這與孫楊在游泳場(chǎng)中自強(qiáng)不息、勇敢拼搏的年輕表率形象很匹配,從而加深了歌眾對(duì)此歌的接受和理解。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明星的加入使節(jié)目注入了時(shí)尚性,但并不代替文化產(chǎn)品原有的品格,只是附加給文化產(chǎn)品一種臨時(shí)的“標(biāo)志”,并加上社會(huì)價(jià)值、社群價(jià)值。不可否認(rèn),被加上時(shí)尚因素的歌,流傳更為順暢。時(shí)尚的過(guò)程是一時(shí)的,而流傳的過(guò)程是歷史的。
最后,歌眾的接受和傳唱是歌曲意義實(shí)現(xiàn)的最重要一環(huán)。一首歌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意圖,就是希望被更多人接受并廣為流傳。可以有從來(lái)不發(fā)表的抽屜詩(shī),卻不可能有不被人唱的抽屜歌,因此我創(chuàng)用一個(gè)名詞“歌眾”:“歌”是名詞也是動(dòng)詞,它的雙性特征,決定了歌眾的二重性——歌曲的接收者不僅是歌的聽(tīng)眾,還是歌的再創(chuàng)造大眾。一般藝術(shù)的受眾,能動(dòng)性只表現(xiàn)在“掏腰包”上,費(fèi)斯克所說(shuō)的“能動(dòng)觀眾”,說(shuō)的只是電影觀眾有用腳選擇、用錢包選擇的能力。歌眾才是真正的能動(dòng)接收者,因?yàn)楦枨慕?jīng)典化是他們傳唱出來(lái)的。
因此,一首歌之所以流傳,取決于多方力量,還需要歌曲特殊的傳播方式。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心理學(xué)家伽塔利(Felix Guattari)在名作《千高原》中提出文化的“塊莖狀模式”傳播說(shuō)。這種模式不同于一般傳統(tǒng)文化傳播的“樹狀模式”:“樹狀模式”有根、有胚芽、有基干,此后發(fā)出枝葉,但有權(quán)威性的源頭,可追溯根源,可回溯發(fā)展途徑,回向意義的權(quán)威源頭。“塊莖模式”在地下蔓延,隨處可以冒出頭,另成一個(gè)體系,另成一個(gè)意義源頭。而“塊莖狀模式”反等級(jí)、反體系,是動(dòng)態(tài)的、異質(zhì)的。傳播分途蔓生,各個(gè)節(jié)點(diǎn)可以成為新的意義之源,重新長(zhǎng)出意義。
從上面分析的兩首歌曲可以看到,歌曲的經(jīng)典挑選和傳播方式是典型的“塊莖式”。歌曲的源頭意義、權(quán)威性并不能完全主宰歌曲意義傳播的旁側(cè)再生。不僅每次新歌的挑選發(fā)行,每個(gè)歌手的演唱,每一臺(tái)節(jié)目都是在新語(yǔ)境中創(chuàng)造新文本,每個(gè)歌眾的歌唱,甚至哼唱,也是在創(chuàng)造新文本。歌曲的這種“塊莖式”的傳播方式,決定了歌曲的經(jīng)典化只能通過(guò)歌眾選擇。古今中外,各種媒介機(jī)構(gòu)、各種精英一直在試圖引導(dǎo)歌曲經(jīng)典化,但歌曲這個(gè)藝術(shù)門類的特殊性質(zhì),決定了它的文化機(jī)制不可能根本改變:如果歌眾不跟上,媒介機(jī)構(gòu)推動(dòng)力就會(huì)削弱。一首歌的經(jīng)典化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歌眾的應(yīng)和。正如克蘭指出,“如果一個(gè)文本的話語(yǔ)符合人們?cè)谔囟ǖ臅r(shí)間闡釋他們社會(huì)體驗(yàn)的方式,這個(gè)文本就會(huì)流行起來(lái)。”歌曲的流傳,正好符合這個(gè)規(guī)則。
二、“歌不附體”與再語(yǔ)境化
經(jīng)典化的另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是歷史保持。對(duì)歌曲來(lái)說(shuō),歷史保持落在兩個(gè)層面上,一是物質(zhì)載體,二是語(yǔ)境載體。物質(zhì)載體可以長(zhǎng)久保存,例如歌本、唱片、磁帶、卡拉OK帶、CD、VCD、DVD、MV光盤、數(shù)字下載等,它們?yōu)楦枨?jīng)典化的歷史保持提供了必要的物質(zhì)支持。語(yǔ)境載體雖然也具有物質(zhì)性,卻是臨時(shí)的、“現(xiàn)場(chǎng)”的。常見(jiàn)的語(yǔ)境載體有電影、電視劇、歌劇、電視節(jié)目、廣播節(jié)目、現(xiàn)場(chǎng)演唱會(huì)、網(wǎng)絡(luò)觀看等。語(yǔ)境載體對(duì)一首歌曲流傳的最初階段起很大作用,但是歌曲流行過(guò)程一旦開(kāi)始,各種語(yǔ)境載體就多多少少開(kāi)始淡出,就形成了“歌不附體”現(xiàn)象。
對(duì)語(yǔ)境載體來(lái)說(shuō),歌不附“體”現(xiàn)象是傳播的必要機(jī)制。歌曲流行雖然起始于最初的語(yǔ)境載體,但要保持它的流傳,就必須不斷投放入新的語(yǔ)境,依靠新語(yǔ)境與舊語(yǔ)境的對(duì)比展開(kāi)實(shí)現(xiàn)成功流傳。
其中有些電影插曲和歌劇單曲,完全脫離原來(lái)語(yǔ)境,成為某演唱會(huì)中的一首歌,或者直接在群眾中單獨(dú)傳唱、流行。最典型的是《義勇軍進(jìn)行曲》。它最初為1935年電通影片公司發(fā)行的電影《風(fēng)云兒女》主題歌。這首歌曲出現(xiàn)在影片結(jié)尾,配合主人公阿鳳等覺(jué)醒了的中華兒女步伐堅(jiān)定投入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的場(chǎng)景。后來(lái)成為中國(guó)國(guó)歌的《義勇軍進(jìn)行曲》,作為各種國(guó)際活動(dòng)的儀式歌曲唱出來(lái)的時(shí)候,歌曲所傳達(dá)的意義已經(jīng)很不相同。原電影已經(jīng)被忘卻,抵抗武裝侵略的語(yǔ)境也已經(jīng)遙遠(yuǎn),而民族尊嚴(yán)和驕傲的情感還包含其中。
還有一類歌曲得益于“半不附體”,它們雖然也脫離了最初的語(yǔ)境載體而單獨(dú)流傳,但還與原語(yǔ)境若即若離,歌者聽(tīng)著都依稀記得是某電影的插曲。比如《花兒為什么這樣紅》,是20世紀(jì)50年代電影《冰山上的來(lái)客》插曲,它帶有新疆塔吉克舞蹈風(fēng)情的曲調(diào)讓人們依稀想起電影的某些情節(jié)和畫面。《四季歌》原來(lái)是周璇在電影《馬路天使》中唱的插曲,此歌的流行既與這個(gè)始發(fā)點(diǎn)有關(guān),也由于脫離了原載體獲得了新的生命。
這種一再的“再語(yǔ)境化”,使歌曲獲得豐富的意義,突破時(shí)間障礙,流傳為經(jīng)典。比如,學(xué)堂樂(lè)歌時(shí)期李叔同根據(jù)美國(guó)歌曲重新填詞的《送別》,20世紀(jì)60年代被電影《早春二月》用作插曲,80年代被電影《小城舊事》再次用作主題曲。《難忘今宵》原是為晚會(huì)所作的結(jié)尾曲。后來(lái)在1987年的春節(jié),由著名歌手李谷一作為晚會(huì)壓軸歌演唱,從此家喻戶曉,成為人人傳唱的經(jīng)典歌曲。此歌流行了三十多年,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情感象征,成為大大小小各種晚會(huì)的結(jié)束歌曲,從最大規(guī)模的中央電視臺(tái)春節(jié)晚會(huì),到個(gè)人的生日晚會(huì),一次次出場(chǎng),一次次不同的語(yǔ)境,衍生出一次次不同的意義。對(duì)春節(jié)晚會(huì)來(lái)說(shuō),難忘的是全世界華人共享祖國(guó)昌盛、人民安康的美好祝福。而對(duì)于一個(gè)人的生日晚會(huì)來(lái)說(shuō),難忘的是親朋好友的聚會(huì)和又一個(gè)生日年歲的到來(lái)。
在《經(jīng)典詠流傳》節(jié)目中,我們也聽(tīng)到了很多這樣的老歌,比如再次聽(tīng)到《滾滾長(zhǎng)江東逝水》等老歌,這些都是原語(yǔ)境存留,與“歌不附體”結(jié)合,生成成功經(jīng)典化的例子。歌曲傳唱,就落在多重語(yǔ)境的控制之中,其意義越來(lái)越豐富。“塊莖模式”是共時(shí)傳播,“歌不附體”形成了經(jīng)典歌曲動(dòng)態(tài)的歷史保存:歌不是保存在哪一場(chǎng)物質(zhì)載體CD上,也不是保存在哪一場(chǎng)晚會(huì)的語(yǔ)境載體中,而是不斷在新的物質(zhì)與語(yǔ)境載體中復(fù)活蔓生。
三、“老歌翻唱”與歌曲的“共同主體性”
“老歌翻唱”是最重要的音樂(lè)流傳機(jī)制。最早最具規(guī)模系統(tǒng)地更新載體的“老歌翻唱”,當(dāng)為中央電視臺(tái)組織的大型文藝演出《同一首歌》。此欄目于2000年1月27日創(chuàng)立,持續(xù)了五年之久,一直以現(xiàn)場(chǎng)和電視直播的形式亮相,人氣指數(shù)和收視率一直據(jù)先。據(jù)央視國(guó)際《2005年播出節(jié)目一覽》統(tǒng)計(jì),就2005年1月7日至8月12日,不到八個(gè)月的時(shí)間內(nèi),總共組織了29場(chǎng)演出,平均每場(chǎng)演出在18首歌以上。這些音樂(lè)中大多數(shù)屬于老歌翻唱,也有正在流傳或者意圖推向流傳的音樂(lè)。2005年,中央電視臺(tái)《同一首歌》欄目組配套出版了一套音樂(lè)叢書共六本。后來(lái),中央電視臺(tái)的《歌聲飄過(guò)30年》《歌聲飄過(guò)80年》,也都是老歌翻唱式的經(jīng)典選擇,它們都收到了很好的社會(huì)文化效果。
這些老歌被歌手們?cè)谂_(tái)上復(fù)活,又被文字文本和VCD文本再次記錄。就如《同一首歌》欄目的組織者所說(shuō),意圖在于“在歌聲中回憶過(guò)去的好時(shí)光,在歌聲中品味現(xiàn)在的好日子”。對(duì)不同的歌眾來(lái)說(shuō),老歌新唱確實(shí)將時(shí)間空間化了。男女老少,不同時(shí)代的人可以匯聚在同一首歌的場(chǎng)景里。
同樣值得探討的,是2005年的電視節(jié)目《超級(jí)女聲》,可以說(shuō)是當(dāng)代典型的、最具沖擊力的一種“老歌翻唱”。“超級(jí)女生”的成名,并沒(méi)有沿著過(guò)去歌星成名的套路:量身定歌,憑借一首新歌一炮打紅。她們一路唱來(lái)的音樂(lè)大多是舊歌,也基本屬于“老歌翻唱”,這一點(diǎn)并未被評(píng)論界真正注意。在她們演唱的音樂(lè)中,幾乎包含了現(xiàn)有歌手的各種翻唱形式,這里做個(gè)簡(jiǎn)要分析。
1. 民歌翻唱:李宇春選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周筆暢選唱的《青春舞曲》,周筆暢選唱的《烏蘇里船歌》等,吸引了很多民歌愛(ài)好者。
2. 影視音樂(lè)翻唱:黃雅莉選唱的《橄欖樹》(臺(tái)灣電影《歡顏》插曲),張靚穎選唱的《一簾幽夢(mèng)》《在水一方》(瓊謠影視劇的音樂(lè)),滿足20世紀(jì)80年代一批成長(zhǎng)于瓊謠小說(shuō)中的純情男女。在此之前,歌手許茹蕓曾推出過(guò)愛(ài)情電影主題曲翻唱合輯《云且留住》,以獨(dú)特的唱腔重新詮釋了早年瓊瑤電影的主題曲,反響積極。
3. 跨性別翻唱:紀(jì)敏佳選唱的《天堂》,原為蒙古族歌手騰格爾演唱。張靚穎選唱的《真心英雄》,原為香港歌手成龍演唱。
4. 西方音樂(lè)翻唱:張靚穎選唱的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這首歌來(lái)自于當(dāng)代著名音樂(lè)劇作曲家安德魯·勞伊德-韋伯(Andrew Lloyd-Weber)創(chuàng)作的音樂(lè)劇《艾薇塔》(Evita
,作于1976年),由蒂姆·萊斯(Tim Rice)作詞,可謂當(dāng)代西方經(jīng)典音樂(lè)。李宇春選唱的Everything I Do
,是美國(guó)電影《獅子王》(Lion King
)中家喻戶曉的經(jīng)典插曲。這些歌似乎更針對(duì)“白領(lǐng)階層”。5. 不同風(fēng)格音樂(lè)翻唱:李宇春選唱舞曲風(fēng)格的《我最搖擺》《請(qǐng)你恰恰》,超級(jí)女生合唱的無(wú)伴奏風(fēng)格的《半個(gè)月亮爬上來(lái)》《彩云追月》,紀(jì)敏佳選唱的戲曲風(fēng)格的《說(shuō)唱臉譜》等。
6. 不同時(shí)期不同歌星的代表音樂(lè)翻唱:周筆暢選唱的《龍拳》,是RAP歌星周杰倫的代表作之一;張靚穎選唱的《好大一棵樹》,是實(shí)力派歌星那英的代表作之一;張靚穎選唱的《鄉(xiāng)戀》,是老牌歌星李谷一的代表音樂(lè)之一;張靚穎選唱的《小城故事》,是鄧麗君的代表音樂(lè)之一;周筆暢選唱的《流星雨》,是臺(tái)灣偶像派組合F4的代表音樂(lè)之一;還有周筆暢選唱的《兩只蝴蝶》,是網(wǎng)絡(luò)音樂(lè)代表作之一。
7. 幾種主題歌曲的翻唱:張靚穎選唱了頌歌《我和我的祖國(guó)》《愛(ài)我中華》,李宇春選唱了情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沒(méi)有他》,超級(jí)女生群唱了勵(lì)志音樂(lè)《明天會(huì)更好》《同一首歌》等。
在這些老歌翻唱中,一個(gè)能指指向另一能指,這個(gè)不斷延伸、無(wú)限衍義的意指過(guò)程,也是歌曲在歌眾不斷傳唱中特殊經(jīng)典化的過(guò)程。最終歌曲必須由歌眾自覺(jué)傳唱,在歌眾的不斷老歌翻唱中得以形成,得以保持。老歌的不斷翻唱,不僅鞏固了此歌的經(jīng)典地位,也在流傳的過(guò)程中滋生新的文化功能。如果沒(méi)有成功地利用這幾種歷史保持和翻唱方式,哪怕在一代人中成功流行的經(jīng)典歌曲,也會(huì)在世代更替中,從經(jīng)典中消失。
沒(méi)有一種藝術(shù)門類能像歌曲這樣,給予歌眾以如此大的自由創(chuàng)造可能,而唱歌也是歌眾自然的文化需要。伯明翰學(xué)派的斯圖亞特·霍爾在《電視話語(yǔ)的制碼與解碼》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種解碼”理論。霍爾認(rèn)為,意義生成過(guò)程,取決于觀眾的三種不同解碼方式。第一種解碼立場(chǎng):“主導(dǎo)霸權(quán)式解碼”(Hegemonic Reading)。觀眾與電視制作生產(chǎn)精英的編碼立場(chǎng)完全一致,完全明白無(wú)誤地接受電視劇制作機(jī)構(gòu)意圖中的意義,觀眾自己沒(méi)有獨(dú)立的立場(chǎng)。第二種解碼立場(chǎng):“協(xié)商式解碼”(Negotiated Reading)。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觀眾既接受社會(huì)文化中主導(dǎo)意識(shí)形態(tài)的權(quán)威,又看到自己的具體利益所在,但拒絕完全接受制作精英機(jī)構(gòu)意圖。第三種解碼立場(chǎng):“對(duì)抗式解碼”(Oppositional Reading)。觀眾明白電視制作精英要借電視傳送的意義,也明了電視文本各層次意義,卻選擇以完全相反的立場(chǎng)解碼,“讀出”針鋒相對(duì)的意義。
霍爾理論指出文化產(chǎn)品的接受方式才是最后意義的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理論對(duì)歌曲研究有重要意義。三種解碼對(duì)別的藝術(shù)門類可能足夠多樣了,卻不夠說(shuō)明歌曲流傳的多樣化。
歌的接受,歌眾的傳唱,一開(kāi)始是模仿,不久就變成自我表達(dá)、自我創(chuàng)造,而自我表達(dá)不可能完全遵循“制作精英”規(guī)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體條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了改造。這樣在歌曲流傳過(guò)程中就出現(xiàn)了不同于霍爾三種解碼的第四種解碼方式,即“創(chuàng)作式解碼”(我建議英譯為Creative Reading)。這種“創(chuàng)作式解碼”不再是藝術(shù)專家的領(lǐng)域,面對(duì)歌曲這種最普泛的共同客體,歌眾創(chuàng)造并分享世界,成了每個(gè)個(gè)體生命自覺(jué)和不自覺(jué)的一種努力,從而構(gòu)筑共同主體性。唱歌屬于個(gè)人,卻不存在純粹個(gè)人的歌。歌者總是在交流,而且有意無(wú)意地加入并形成了共同主體性,來(lái)推動(dòng)一首歌的經(jīng)典化。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理想地體現(xiàn)了這一共同主體性。其核心是人與人之間通過(guò)語(yǔ)言行為相互理解。歌唱作為一種人類最自然的表意行為,看似獨(dú)自歌唱,實(shí)際上卻是通過(guò)同唱一首歌,獲得了“歌眾群體”。他們不必形成合唱,即使相隔萬(wàn)里,從未相逢,卻通過(guò)共同主體性,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一個(gè)意義,這不是一般所說(shuō)的“集體主義”,而是各個(gè)主體自由意志的貫通,它并不要求整個(gè)社群取得統(tǒng)一意志,相反,它必須依靠主體各自的主觀意愿,提供不同的再創(chuàng)造,才能形成。就像《經(jīng)典詠流傳》中廣為流傳的一些歌曲,它能喚起一批人群心靈的共同響應(yīng),并且使他們自覺(jué)自愿地唱起來(lái)。“個(gè)體之主體性只有在共同主體性里才成為現(xiàn)實(shí)的東西;共同主體性也只有在眾多的個(gè)體主體性發(fā)揮中才成為現(xiàn)實(shí)的東西。”這是哈貝馬斯理想的共同主體性。歌曲取得的共同主體性,在這里得到非常生動(dòng)的表現(xiàn)。就像他的論述:“語(yǔ)言行動(dòng)不只是服務(wù)于說(shuō)明(或假定)各種情況與事件,言語(yǔ)者以此同客觀世界中某種東西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語(yǔ)言行動(dòng)同時(shí)服務(wù)于建立(或更新)個(gè)人關(guān)系。”的確,能夠把個(gè)人與共同主體相關(guān)聯(lián)的藝術(shù)品,才是真正的經(jīng)典。
這樣一種理想的主體借“經(jīng)典化”溝通的模式,首先在歌曲與歌曲傳播方式中有活力地展開(kāi),并為努力探尋“共同主體性”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個(gè)絕佳的觀察及實(shí)驗(yàn)場(chǎng)地,對(duì)有同樣追求的其他藝術(shù)門類來(lái)說(shuō),借鑒歌曲傳播模式,吸引大眾積極參與,或許是經(jīng)典化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