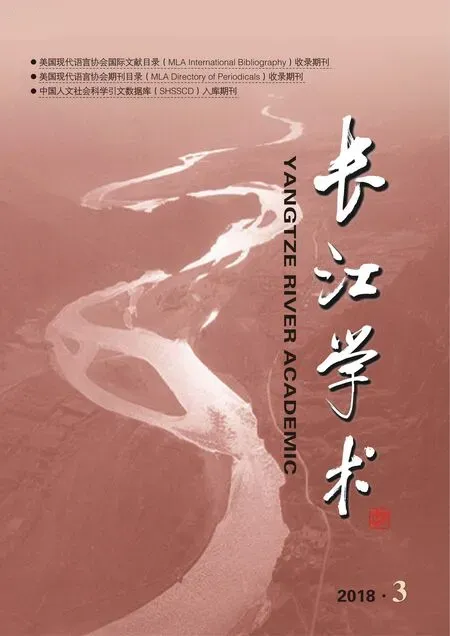在中國新詩百年紀念大會上的致辭:一百年來一件大事※
謝 冕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今天我們在北京大學陽光大廳隆重舉行中國新詩一百年紀念大會。今年是戊戌維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北京大學建校一百二十周年。這些重要的日子重疊在一起,給我們的大會增添了莊嚴的氣氛。一百年前,即公元1917年,陳獨秀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將《新青年》從上海遷來北京大學,當時的辦公地點是東華門外箭桿胡同。移刊后的《新青年》刊登過“分期編輯表”,這些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這些人都是北大的教授,也是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他們也都參與了中國新詩的提倡與建設,有的本身就是新詩人。
《新青年》創刊時,陳獨秀曾對中國青年提出六點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這六條,簡括起來,也就是“科學民主”四個字,這既是新青年雜志的辦刊宗旨,也是北大的立校根基,更是體現了新文化運動和新詩革命的基本精神。談到新詩的歷史,《新青年》是繞不過去的話題,我們不妨從一個角度來看《新青年》與新詩的密切關系:胡適是“嘗試”新詩的第一人,也是發表新詩和出版新詩集的第一人。他的“白話詩八首”是中國新詩的開山之作,刊登于《新青年》二卷六號,時間是民國六年,即1917年。他的這些最先發表的白話詩與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于同期刊物,可以認為是文學革命的先聲。接著是《新青年》四卷一號,即1918年1月,發表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鴿子》《人力車夫》《月夜》等詩九首。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號,魯迅以唐俟為筆名發表《夢》《愛之神》《桃花》等三首新詩。這些新詩的紀元之作,均與《新青年》有關。
距今一百年前,與魯迅筆下的狂人發出“救救孩子”吶喊的同時,中國的新詩人也滿懷激情地立在地球邊上狂歌五千年古國的鳳凰涅槃,那是呼喚“女神之再生”的狂飆突進的時代。中國新詩是中國詩人的一個時代夢。晚清道、咸以降,列強肆虐,國勢凌池,內憂外患,凄風苦雨。有識之士,天下才俊,尋求救亡圖存、強國新民的道理,遂有了通過“新”文學、“新”詩以達于“新”中國之訴求。簡括地說,當日的目標在于通過改造舊詩而為新詩,期待著以詩的革新使新知識和新思想得到展現與傳播。新詩生于憂患,也成于憂患。由此看來,一百年前進行的新詩運動不僅是一場文體革命和藝術革命,也是一場思想革命。這是百年來的一件文化建設的大事。
公元19世紀末,詩人黃遵憲等曾倡導“詩界革命”,提出“我手寫我口”的主張。但因未能打破舊格律的束縛,詩體未能解放,這場預設的革命沒有成功。胡適“嘗試”新詩的貢獻在于,他勇敢地確立以白話代替文言,以自由代替格律,實行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情感方能跑到詩里去。”這是大破壞之后的大建設。因為沖出了格律束縛的大障礙,于是獲得了新詩發展的大生機。一百年來,因為有了白話寫作的自由體新詩,我們于是能與世界詩歌“對接”,從而擁有了表達現代人情感和思想的最理想也最親民的抒情方式。新詩的誕生實現了中國人的百年夢想。
新詩從最初的“嘗試”到日臻成熟的自立的過程,我們可以從周作人的“小河”到艾青的“大堰河”的持續實踐中,看到幾代詩人以白話寫詩所進行的英勇行進的軌跡。擺脫了傳統格律的新詩人,在日常口語的陌生和單純中尋求鮮活的語言和精美的抒情,他們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成功。幾代詩人的探索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終于建立起并實現了無愧于千年詩學傳統的現代審美風尚。我們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新詩不僅是中國詩歌傳統的革新,更是中國詩歌傳統的延續,它全面地繼承了中國詩歌“詩言志”的精髓,它所實行的徹底的變革,如前所述,最終是為了詩的“有益于世”。
匆匆百年,戰亂連綿。挺立并前進于戰火中的,不僅有英勇抗戰的舉國軍民,在抗擊侵略者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隊列中,同樣行進著中國詩人激情而無畏的身影。他們投身于全民抗戰的激流中,他們因國家民族的不幸而自覺地“放逐抒情”,甚至為此犧牲寶貴的生命。他們以自己的行動譜寫了全民抗戰的壯麗史詩。我們都記得詩人艾青,那年他“從彩色的歐羅巴帶回了一支蘆笛”,他在這首詩的前面引用了詩人阿波里內爾的法文詩句:
當年我有一支蘆笛
拿法國大元帥的節杖我也不換
但當詩人面對著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時,他決絕地將那支蘆笛換成了呼喚自由解放的號角。不僅是艾青,中國所有的詩人都自覺地告別唯美的豎琴和短笛,那些他們曾經心醉的柔美的旋律,頓時化為了呼喚自由的進軍的鼓點:九月的窗外,亞細亞的田野上,自由呵,從血的那邊,從兄弟尸骸的那邊,向我們來了。也許我們此種悲壯的追述還可延續下去,因為苦難曾經是那樣的綿長。但我們只能適可而止。
曾經有過一個時代,詩歌被禁錮,陽光被壟斷。然而詩人在抗爭,那是一個焚書毀琴的年代,詩人被流放,被監禁,被冠以種種惡名。然而他們在監獄,在勞改農場,在遙遠鄉村昏暗的燈光下繼續創造著光明和溫暖。地火在燃燒,巖漿在熔化,終于有一天,十月的陽光沖破至少長達十年的暗夜。一切也如同神話描寫的那樣,被雷電劈倒的懸巖邊的樹,失去生命變成化石的魚,一起都在新的陽光下復活了。帶著肉體和心靈創傷的詩人,滿懷希望地迎接重新開始的生活,他們走上街頭,歡慶文明對于邪惡的勝利。他們祈求從今以后“愛情不被譏笑”,祈求“跌倒有人扶持”,他們如同發現新大陸那樣歡呼:詩啊,我又找到了你!
禁錮的閘門終于打開,解放了的詩歌沖破思想和藝術的牢籠,一代新詩人接過五四的火種,開始在中國開放的時空向世界大聲“宣告”: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正在填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未來人們的眼睛在凝視我們,彌足珍貴的自由精神重新回到出發的原點,中國新詩進入一個偉大復興的時代。詩歌告別了虛假和空言,回到了自主自立的抒情本位,它呼喚對于獨立人格和自由人性的認同與敬畏。詩人的想象力和獨創性得到尊重——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寫作,而無需別人為它規定戒律。不談或少談“主義”而專注于“自以為是”的獨立創造,已經成為當代風尚。打破大一統之后的詩歌,呈現出紛繁多彩的多元格局,這是幾代詩人所夢寐以求的良好生態。
歷史安排我們站立在一個偉大的一百年的終點上,歷史又安排我們站立在另一個偉大的一百年的起點上。百年一遇,百年一聚,百年一慶!與其說我們是幸運的,不如說我們是沉重的。一代先驅者把百年的詩歌夢想交給了我們,我們不僅是享受前人創造成果的一代人,我們也是承受前人重托的一代人。記得一百年前新詩誕生的時節,我們的前輩就告誠我們:不能因為“新”而忘了“詩”,也不能因為“白話”而忘了“詩”。他們擔憂的是,我們因熱衷于變革而對于詩歌本體的輕忽或遺忘。一代人又一代人走遠了,他們把懸念和期待留給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