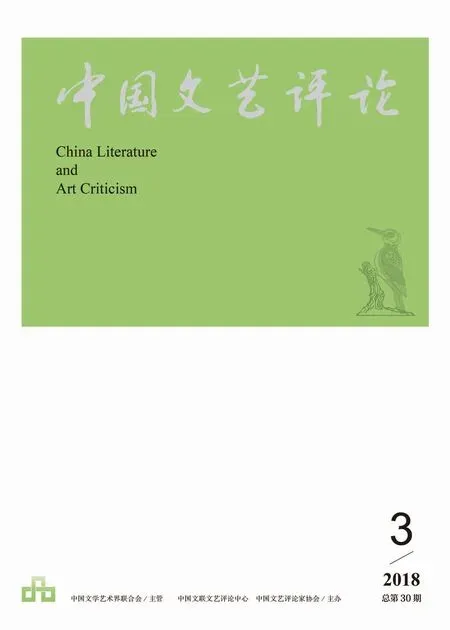月落重生燈再紅
——新時代傳承和傳播經典劇目的美學意義
顧春芳
2017年歲末,上海戲曲藝術中心攜昆曲四本《長生殿》(每本九出)、新編歷史京劇《曹操與楊修》、滬劇《雷雨》進京演出。被譽為“中華昆劇永恒經典、明清傳奇中冠首”的《長生殿》能夠以全本面貌重現于當代舞臺。這是經典的幸事,也是時代的幸事。《牡丹亭》【離魂】杜麗娘離世之前有一句唱詞,“月落重生燈再紅”,古老的昆曲能夠從垂垂老矣、奄奄一息的狀態中得以重生,并以青春現代的完整面貌呈現在舞臺上,這是中華文化當代復興的一個象征,是昆曲自身的“月落重生燈再紅”,帶給我們諸多啟示。
第一,新時代的文化藝術建設應高度重視經典對當代戲曲發展的引領作用。
經典劇目對于文化生態的改善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民族經典關乎國家氣象,季札在魯國看周代的樂舞,樂工為他唱《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這里體現的正是藝術和國家氣象的關系,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如果缺乏標志性的傳世經典是難以稱其為復興的。
縱觀世界各國的國家劇院,無不有奠定自己劇院歷史地位的經典之作。比如莎劇對于英國人而言,始終是英倫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俄羅斯19世紀的文學和戲劇對于其民族精神的傳承和弘揚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讓德國的拜羅伊特自19世紀以來一直成為全世界朝圣的文化圣地。2014年,《齊格弗里德》(《尼伯龍根的指環》四聯劇之三)在中國國家大劇院上演,八位演員,持續五小時的演出,我們不得不信服由瓦格納營造的樂劇神殿,攜帶著德意志的思辨理性和民族精神,依然高聳在幾個世紀以來的戲劇和舞臺的極限夢想中,由音樂和演出所匯聚的神圣而莊嚴的精神光照足以超越歷史、超越種族、超越文化的隔閡。正如主人公齊格弗里德的詠嘆調所唱:“我曾永恒,我今永恒!”偉大的經典是永恒的,它可以凝聚并持續引領一個民族的精神。2014年和2017年在天津大劇院相繼上演的俄羅斯歌劇《戰爭與和平》和現實主義話劇《兄弟姐妹》,讓大多數國人領略了經典的舞臺藝術和國家氣象之間的關系。對戲劇藝術而言,至高的思想以及文化意義的追尋和表達,最終都要歸屬和凝結在民族與時代的經典劇目之中。
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必然召喚屬于這個時代的藝術經典。什么樣的作品才具備經典的基本品格?首先,經典戲劇需要具備足夠強大的哲理內核和人文精神。《長生殿》之所以比一般的愛情悲劇深刻,在于洪昇思考的是有限人生的終極意義,他把“情”的價值推向了永恒與形而上的高度,其對于人性和自由意志的覺醒和張揚顛覆了理學的重壓,向前延續著湯顯祖在《牡丹亭》“至情”的觀念,向后影響了曹雪芹《紅樓夢》“有情之天下”的理想。《雷雨》不以“亂倫”的乖張取悅于人,它最根本的意義在于觸及了存在的哲理命題,人的可貴的青春、愛情和生命在對命運的抗爭中,最終被命運的風暴所吞噬的悲劇,偉大的經典凝結著人類關于存在的普遍體驗。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不停留于描繪一般層面的君臣矛盾,而著意于剖析偉人的精神黑洞。曹操縱然有曠世奇才,縱然懂得禮賢下士,廣納天下賢達,但是他不能正視自我精神世界的“黑洞”。這個“黑洞”就是“猜忌”,就是“怕因猜忌而犯下的殺戮為天下人所恥笑和痛恨”,為此他不惜制造“夢中殺人”的謊言,繼而欲蓋彌彰,殺人如麻,并且踏著無辜者的鮮血一步步走向權力的巔峰。他的可悲,集中起來就是他自己的那句臺詞:“難將赦免說出口!”多么深刻!一個不懂得反思的人是孱弱的!一個沒有勇氣掙脫謊言的人是可悲的!一個將錯就錯的人是沒有希望的!曹操與古希臘悲劇中那位“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的選擇恰好相反,前者選擇欺騙,后者選擇求真,無論是欺騙還是求真,都深刻挖掘并展示了人性中那些促成其善或促成其惡的歷史成因,而一切經典的基本品格正是基于對人性深刻的洞察和剖析。
其次,經典戲劇承載時代的精神和人學的傳統。它需要藝術家站在哲學和思想的制高點,在整個人類戲劇史的寬廣視野中,在連接戲劇傳統和未來的歷史坡道上,敏銳地發現和把握這個時代乃至全人類的普遍處境和命運。當前,中國戲劇如果要締造經典,必須從創作意識中真正接續起“人學”的傳統,堅守戲劇藝術的“人學之根”。戲劇藝術最強大的生命力和藝術張力就在于對真實和復雜人性的思考與追問,對人類普遍生存的關注,對時代生活最深層的關注和思考。如果脫離了對人和人性的思考,脫離了對人的內在心靈世界的探索,無視時代的真實以及由此真實照應的普遍性體驗,甚至不屑傳達時代精神,那么這樣的戲劇作品注定是短命的。藝術創造究其本質而言,就是洞察潛藏在表象之下的“本真”,表現出人類生活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和情感,通過藝術的審美創造盡人、盡己、盡物、盡性。
憂患意識和仁愛精神一直是中國戲劇思想取向的主流。這與儒家美學的深刻影響不無關系。憂患意識的呈現,仁愛精神的張揚,經世愛民的精神,責任使命的擔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義承擔,都是儒家美學思想在藝術追求和創作理念上的體現。“君子憂道不憂貧”,由“仁愛”精神所生發出的對家國命運和生民立命的關懷,乃至整個人類存在的責任和使命意識是歷代藝術家的精神線索,也是知識分子心馳神往和親躬履踐的人格美的范式,它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此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在戲劇史中則表現為對社會歷史的深刻反思,對真理和謬誤的理性思辨,對至高的美以及希望的追尋與捍衛。
偉大的經典是人性的實驗室。藝術品到底能否穿越歷史時空而重生,能否越過多個歷史朝代還保住它的生命力,關鍵是藝術本身所蘊含的人性的圓滿程度。偉大的經典是人類的鏡子。我們在里面照見自己、照見歷史、照見良知、照見真理。經典是民族精神的容器,是大國氣象的呈現。只有那些承載文化使命、美學內涵和人文精神的作品,才有可能成為時代的經典、民族的經典乃至世界的經典。
第二,昆曲經典全本大戲的演出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
有人認為,昆曲全本大戲的演出效果未必有折子戲好,昆曲傳承要側重折子戲,沒有必要完整搬演曲折的傳奇故事,唯有串演精彩的折子戲段落,才能吸引當代觀眾。我們卻認為,昆曲的傳承和光大不能只搬演折子戲,不能只停留于把觀眾吸引到劇場里來。
首先,折子戲的演出傳統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折子戲的確是昆曲藝術的精華所在,好的折子戲大多是從傳統的全本大戲中擷取的最富有戲劇性的出目,在形式和內容上最能體現昆曲的藝術特征,矛盾沖突尖銳,人物形象生動,情節安排別出心裁,唱念做打也最能展現演員的功夫,故而最能吸引和贏得觀眾。“折子戲”曾經給乾嘉時期的昆曲活動創造出生動活潑的局面,經過歷代表演藝術家的精心創造和打磨,積淀了一批生、旦、凈、丑等本行為主的應工戲,不少昆曲折子戲甚至成為了“名家傳戲”的基礎,比如《琴挑》《游園》《驚夢》《尋夢》《山門》《斷橋》《夜奔》《哭像》《嫁妹》《出塞》等,都是歷代觀眾百看不厭的精品。折子戲通過演員精湛的技藝,扎實的舞臺功力,可以把人物的意緒和心境強烈而集中地傳達給觀眾。折子戲的教習和演出,從歷史和實踐兩方面看,確實有利于昆曲藝術表演藝術的傳承,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昆曲的傳承不僅僅是場上的傳承,不僅僅是表演藝術的傳承,更有文學深度和人文精神的傳承,更有昆曲審美形態的最高呈現。唯有經典的昆曲全本大戲才可作為這一劇種的文學深度、人文精神和審美形態的最高呈現。
其次,昆曲經典折子戲固然是傳統昆曲的精粹,除了可以展現演員的表演功力和人物塑造之外,它還應該自覺地確立自身作為國劇的思想高度和經典品位。我們看全本的《長生殿》和《牡丹亭》所獲得的審美愉悅和思想啟迪,是看幾出折子戲所不能代替的。偉大的戲劇經典往往承載著深刻的哲理和思想,這個深刻的哲理和思想需要戲劇從案頭到場上的完整呈現。一個只能演出折子戲而不能演出全本的演員是有局限的,一個只能演出折子戲而不能演出全本的劇院不可能躋身世界一流,一個只能欣賞折子戲而不善于欣賞全本的民族終歸是沒有深度的。從這個意義而言,昆曲未來的發展和延續,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它不僅要通過精彩的折子戲把觀眾吸引進劇場,更要培養他們欣賞戲劇文學的修養和深度。唯其如此,昆曲才不會淪為簡單的娛樂方式,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人文品格。
近年來,南北各大劇院對于昆曲全本大戲的排演給予了高度重視,這是順應昆曲自身發展和當代文化復興的趨勢的,無論是傳統經典還是現代新編的演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最突出的是青春版《牡丹亭》、北昆和江蘇省昆的《紅樓夢》《桃花扇》以及上海昆劇院的《長生殿》和湯顯祖“臨川四夢”——《紫釵記》《牡丹亭》《南柯夢》《邯鄲夢》的排演,這些全本大戲的現代呈現,對于昆曲在當代的傳承發展以及海內外的傳播,可謂意義重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以折子戲的編劇思維來創編經典大戲,讓我們看到了昆曲原創的一種新的觀念。比如江蘇省昆的新編《紅樓夢》,在選材、編戲、文辭、遣句方面無一不考究,無一不精妙,如出古人之手,不見今人造詞之拙,曲詞既白又雅,宜唱宜懂;既有創新,又見出處;既出紅樓,又入紅樓。在昆曲的改編中既不背離曹雪芹,又不囿于曹雪芹,而且全面體現昆曲修養、詩詞功力確實并非易事,這絕非一個華麗的舞臺外觀所能替代的。江蘇省昆《紅樓夢》之所以“妙”,妙在取舍,妙在提煉,妙在傳統演出之純之真,妙在以質樸而又深厚的唱功做功淋漓盡致地刻畫了紅樓人物——寶玉、黛玉、王熙鳳、襲人、晴雯的性格之真。抓住形象的真也就抓住了紅樓的魂。而藝術形象刻畫的真和美,是編劇、音樂唱腔設計、演員、導演共同努力的結果。
再次,全本大戲的復原和排演有利于藝術的代際傳承與流派構建。全本大戲可以說是昆曲表演的極限運動,其難度是單純折子戲的表演難以相提并論的。它對演員的基本功、體力、人物塑造、情感表達、臨場發揮的綜合鍛煉;對演出團隊的綜合實力、合作精神的提升;對編導修養和整體駕馭能力都是全面的考驗,因而唯有全本大戲演出的強度才能真正培養出一流的演員和一流的團隊。上昆的“臨川四夢”,四本《長生殿》,師生同臺,薪火相傳,已經積累了昆曲傳承的實際經驗,也形成了上昆獨特的昆唱藝術和表演風格的流派。蔡正仁、張靜嫻等藝術家“老當益壯”,黎安、沈昳麗等青年演員“日趨成熟”,這種歷史的交匯折射出昆曲自身的歷史感、滄桑感和現代感,同時也能夠體現出上昆代際變化中一脈相承的美學品位和藝術追求。
總體而言,全本《長生殿》導演的整體處理張弛有度,結構謹嚴,節奏緊湊,天上人間、宮闈民間、悲喜、冷熱、剛柔、文武的交替轉換,比較充分地實現了洪昇劇本在演出敘事上的藝術追求。全劇一景到底,用天幕垂下的三塊簾子分割前后演區,后景以宋元繪畫渲染總體氛圍(如果用唐代繪畫也許更妥當),三塊簾子可以自由起落,由此在縱橫兩個向度構成了空間變化的基本格局,保證了場景的自由轉換以及舞臺演出的流暢。值得一提的是,角色之間的交流很好地化用了話劇藝術的人物關系和內心動作的處理方式,創造出較為細膩傳神的舞臺交流形式,群戲場面的調度和節奏也比較清晰利落,這是導演藝術的成功。如果燈光的設計和運用在“天上”“人間”兩個世界的總體色調和氛圍的處理中有所區分,也許會更加強化“有情世界”與“世俗世界”和“天上仙界”的對照。對未來的昆曲而言,我以為燈光較之布景是更為重要的舞臺技術手段,昆曲演出燈光的運用需要高度的節制,否則就不能很好地突出昆曲總體典雅、純凈、詩意的藝術品格。在表演上,每個角色都找到了各自準確的人物感覺和心理節奏,表演的程式最終落實在人物形象和心理變化的刻畫和塑造上。所以,觀眾看到的演出不是程式的堆砌和組裝,而是人物心靈的表達和情感的抒發,這是《長生殿》表演上的追求和成功。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案頭和場上缺一不可。表演鑄造堅實地基,劇本呈現絕對高度。沒有地基,高度無從體現;沒有高度,戲劇就不可能具備足夠的歷史的穿透力和延伸力。偉大的戲劇經典必需鼓動起文學和表演的雙翼。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在目前比較有利于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條件下,在藝術創造對于中國美學精神的召喚中,應該在保護和積累經典折子戲的基礎上加緊全本經典傳奇的復原和排演,這必將對昆曲藝術的復興和傳承起到積極作用。
第三,經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需要表導演整體把握和精確呈現經典的意蘊。
我個人比較注意《長生殿》文本改編中的取舍,但凡經典文本取舍不當就會傷及作品的哲理意蘊。《長生殿》原著50出,演出本改編為四本36出,演出分成四個部分,分別題為《釵盒情定》《霓裳羽衣》《馬嵬驚變》《樂宮重圓》。《長生殿》并非一般意義上以離合寫興亡的愛情悲劇,而是一出思考存在的哲理悲劇,它的深刻性之所以超越一般愛情悲劇的主要原因在于,由情之世界、世俗世界、天上仙界三層環狀套層的敘事結構構成一種極具現代性的敘事形式,這一敘事形式超越了同時期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陳腐舊套和敘事模式。特別是對楊貴妃這一藝術形象的塑造,突出地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現代性意義,同時賦予了李楊二人的愛情以“永恒的意蘊”。
這一“永恒的意蘊”一方面延續并深化了湯顯祖“至情觀念”,通過刻畫李楊二人的“至情”對于宗法朝綱和仙界永生的超越,其愛情所展現出來的自由人性的覺醒和追求,(這一層意義類似于《牡丹亭》中柳夢梅和杜麗娘的“至情”對于法理世界和生死兩界的超越);另一方面《長生殿》雖然涉及到愛情和政治的矛盾,君臣關系和政治斗爭,但主要表現的是人生難以兩全的處境,表現現實的不自由和意志的自由之間的沖突,表現有限人生的終極意義的追尋,為了體現這種終極追求,洪昇把“情”的價值推上了形而上的高度。
舞臺本《長生殿》以李楊二人“情的堅守、抗爭、犧牲和勝利”來取舍情節,呈現“有情世界”對于“世間禮法”和“仙界永生”兩個世界的抗爭,最終在劇本的深層構筑起了一個超越于前兩個世界的“情之世界”,為經典大戲的改編提供了一個比較成功的范例。也正因如此,我們認為對于《長生殿》意蘊的開掘似可更深入一步,應該適當保留有些原作的筆墨。比如第二十二出“密誓”【越調過曲·山桃紅】 【下山虎頭】中眾仙議論李楊二人七夕盟誓的一場戲被刪去了,原作【(合)天上留佳會,年年在斯,卻笑他人世情緣頃刻時。(齊下)】這一句話在開頭和結尾重復了兩次,這句話大有深意,可說是一語道破《長生殿》劇名的意涵。
“密誓”表現李楊二人在七夕之夜對天發愿,互訴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愛情誓言。而此時,大唐正逢盛世繁榮,李楊二人恩愛纏綿之際,渾然不知命運的風暴就在附近,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即將導致二人生死兩隔。作者洪昇這一筆是要通過天上仙班對人間眷侶的評價,冷靜地玩味,并且直接道出世間繁華的真相是“人世情緣頃刻時”。這樣的敘事方式,其意圖在于啟示觀眾:人生的悲歡離合在人心的體驗是悲劇,然而在更浩渺的天宇和仙界看來則是司空見慣的人間喜劇。從宇宙的角度俯瞰人世,人世的悲歡離合本就是幻夢一場。李楊二人“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永恒誓言在天界眾仙看來是毫無永恒性可言的,因為一切在世的富貴榮華、永恒誓言只不過是時間中轉瞬即逝的幻光。因此,在這一場戲中,對天盟誓生死相依的李楊二人仿佛就是眾仙注視下正在經歷“悲歡離合”的“戲中人”,他們苦苦追求情的永恒,卻根本無法識破塵世的虛幻和無常。劇本似乎是要在更廣闊的宇宙視角表明,無論是臺上敷演的傳奇,或是臺下正在發生的世事,無非只是短暫的幻夢而已。
但是,如果劇本停留在這一層意義,《長生殿》的現代性意義根本無從談起。《長生殿》并非是要代釋家立言,而是寫人在無常、突變、易逝和短暫的人生中對自由的渴望和對真愛的信念。尤其是洪昇筆下的楊玉環,不遵禮制,不羨神仙,上天入地,九死一生就是要和唐明皇長相廝守,即便因荒疏朝綱而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并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真愛之心依然不死,由此閃耀出經典內在動人無際的人文主義光輝。李楊二人的愛情及其所處地位的要求之間的尖銳矛盾,決定了其愛情悲劇的必然性,然而作者并不是要刻畫這種悲劇的必然性從而鼓吹“情”的虛無,而是進一步肯定“情”的意義。他不僅寫出了楊玉環對于命運的抗爭,對于情的易逝的抗爭,對于女性地位的抗爭,更寫出了她對于“永恒的至愛”的追求;不僅寫出了她對于“永恒的至愛”的追求,還進一步寫出了個體勇于承擔自我過失所導致的倫理道德的譴責。【冥追】一折,在楊玉環的魂魄追隨唐明皇的旅途中,當她看見虢國夫人的愁魂,不禁感慨“想當日天邊奪笑歌,今日里地下同零落”;當她目睹安史之亂所帶來的生靈涂炭,當下醒覺和懺悔“早則是五更夢短,瞥眼醒南柯。把榮華拋卻,只留得罪殃多”。然而,最終楊玉環仍然拒絕通過證入仙班以換來永生的結局,她無視宇宙意義上的“長生”,而選擇虛幻的心靈世界的“長生”,寧為“長生鈿”(愛情信物)不羨“長生殿”(天上人間的富貴和永恒),這是原作撼人心魄的一筆。
“有情世界”的追尋是洪昇在劇中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哲理思考,更是《長生殿》在劇本文學的哲理層面高出其他戲曲傳奇的深刻性所在。這種思想的深刻性使《長生殿》這部經典超越了一般意義上才子佳人、帝王妃子的題材,而呈現出不朽的人文品格,足以媲美西方戲劇史上的人文經典。因此,如果舞臺敘事能兼顧原作敘述層級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在取舍上把握更準確的度,我以為《長生殿》的意蘊將會更加有力地呈現出來。
第四,戲曲原創必須穩固地構筑在對戲曲最根本的美學問題的體悟基礎上。
戲曲程式作為一種藝術的抽象,需要從程式與生活、程式與形象等的內在聯系的研究中,才能得出一些有利于戲曲藝術創造的規律性知識,需要從程式自身的美學追求中才能見出程式的本質意義。以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為例,該劇在舞臺呈現方面最突出的特點是突破了京劇凈角行當、流派乃至程式的界限,其程式浸潤了人物真實的心理和情感,程式的背后有著堅實的內在情感與真實體驗作為基礎,這就是龔和徳先生提出的“心理現實主義”的內涵。比如,當曹操被告知孔聞岱輾轉南北的真相時,他后悔莫及但又不能當下懺悔,楊修的暢快的“笑”和曹操的假裝暢快的“笑”形成了兩人在規定情境中不同性格和心理的鮮明對照;當曹操逼死倩娘后伏身抱起她時突然下意識地猛回頭,這個動作深刻地揭示出了曹操內心深陷恐懼和黑暗的真實感,可謂 “無戲之處,處處是戲;無言之時,時時有言”。正是基于真實,歷史劇與現實的那道鴻溝被人物真實的情、真實的心理和真實的舞臺生活所彌合。程式承載起準確的人物感覺和心理節奏,落實在人物形象和心理動作的刻畫和塑造上。得魚而忘筌,觀眾看到的不是京劇程式技巧的堆砌,而是角色心靈的表達和情感的抒發,是舞臺上真實生活著的人物。在這個最高的藝術理想的實現中,程式與真實并不對立。
《曹操與楊修》之所以對戲劇角色的內心動作、心理過程的呈現如此細膩傳神,也許和戲曲取法話劇塑造人物角色“從體驗到表現”“從心理到行動”的一整套科學的理念和方法不無關系(當然傳統的戲曲理論也有一套刻畫人物心理和體驗的方法和技術,如何更好地幫助演員體驗和外化角色的心理,加強人物之間的交流和動作,這與表導演的舞臺觀念密切相關)。流派、行當和程式不再是表演的目的,而成為了塑造人物的手段;花臉行當、“架子”“銅錘”歸并于人物形象的創造。正如尚長榮先生自己總結的那樣:“如果把人物形象的理解和切入作為內功的話,那么使這一形象展示于舞臺的一切手段就是外功。在內外功的關系上,我的觀點是‘發于內、形于外’,做到‘內重、外準’。在深切感受和把握觀眾脈搏的同時,以最靈活的方式,力求準確地撥動觀眾的心弦。為了做到這一點,我突破了傳統的凈角行當界限,試圖將架子的做、念、舞和銅錘的唱糅合在同一表演框架內,努力形成粗獷深厚又不失嫵媚夸張的表演風格,這里我力圖避免長久以來形成的為技術而技術,以行當演行當的傾向,使行當和技法為塑造人物服務。”《曹操與楊修》之所以成為新編現代歷史劇的里程碑,它在表演方面的突破和高明正在于此。
《曹操與楊修》是原創京劇的一座高峰。原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基于特定歷史和時代的深刻認識,在敘事深度、形式語言和人文內涵三個維度,構成對原有的戲劇觀念和戲劇傳統的變革性的超越。作為一出現代經典,《曹操與楊修》體現了經典所應該承載的文化使命、美學內涵和人文精神。戲曲的傳承一方面是對傳統的領悟和吸納,另一方面是要對傳統藝術的外部形式和表現特點加以推升和創新。創新和化用的關鍵并不在外部符號的套用和裝點,而在于中國藝術精神的涵養和體悟,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從道技兩個層面吸收、借鑒、繼承和發展戲曲傳統。無論是京劇還是昆曲,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瑰寶和文化精粹,一定要在守護好自己的精神主體、藝術特質、獨特個性以及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發展,不能輕易地被話劇、歌劇、音樂劇或者其他任何形態的戲劇所同化,一旦同化,也就是自身異化的開始。
當前,由全球化帶來的戲劇文化的充分共享,許多世界公認的舞臺經典正在不斷提升當代中國觀眾的審美品位,而習慣了經典的觀眾更加渴望當代的原創劇作。縱觀世界各國的國家劇院,無疑都有奠定自己劇院美學和歷史地位的經典。對任何國家的戲劇和劇院而言,一切意義的尋找和表達最終都需要歸屬和凝結在民族和時代的經典劇目之中。
牟宗三先生曾說:“為人不易,為學實難”,他接著說:“這句話字面上很簡單,就是說做人不容易,做學問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它的真實意義,卻并不這么簡單。我現在先籠統地說一句,就是:無論為人或為學同是要拿出我們的真實生命才能夠有點真實的結果。”同樣,經典劇目的締造,也是要拿出我們的真實生命才能夠有點真實的結果,不是自己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沒有真正的藝術,也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藝術。究竟能不能從這個生命的核心里生發出力量和信念來對待藝術,本就非常困難和不易,因此對于那些把藝術看成自己生命所在的“真正的藝術家”而不是“偽藝術家”,這個時代應該創造一切條件給予尊重,讓他起飛。
真正有意義的戲劇原創還必須穩固地構筑在對戲劇藝術最根本的美學問題的體悟基礎上,戲劇理想的實現從來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繁華,而是精神和美學意義上的富足,戲劇的“黃金時代”雖然不能離開經濟,更重要的是那一片代表著人類偉大經典和不朽靈魂的璀璨星空。對于當代戲劇而言,最根本性的問題,莫過于“人”的問題,即作為創作者的“人才”和作為“人”的不朽藝術形象的出現。如果年輕的戲劇人在修養、智識、才能、社會責任以及思想深度方面時常放眼世界而反觀自身,如果未來的藝術家可以從急功近利的創作生態中超脫出來,從日益僵化和陳舊的劇場和舞臺觀念中解放出來,不斷砥礪和精進戲劇思維、戲劇觀念和戲劇技能,不斷完善內在的學養和智識,不斷改造和優化目前的戲劇生態,才能創構新的敘事觀念、時空觀念和演出形態,逐步縮小中國戲劇在審美層面和思想層面與世界戲劇的差距,同時彰顯中國戲劇的主體意識和美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