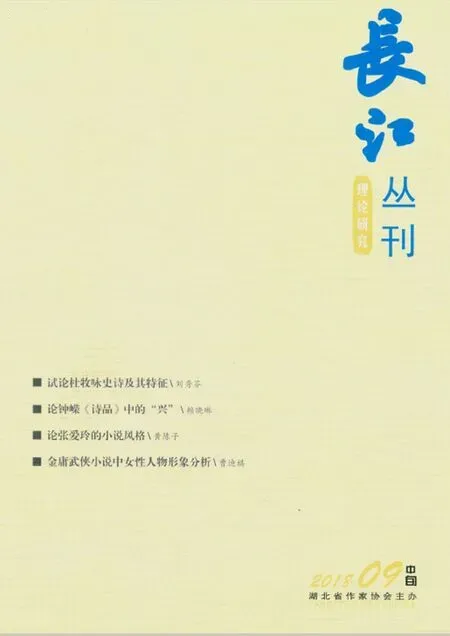試論杜牧詠史詩及其特征
■/
詠史詩在文學史中的發展歷程源遠流長。自東漢班固創作的《詠史》伊始,中國的詠史詩逐漸繁盛,尤其是到了晚唐時期,詠史詩創作步入到了鼎盛發展階段,也成就了一批享譽中外與古今的詩人,如杜牧、李商隱等。杜牧在文學領域中有著較高的修養,對現實社會也有深刻的考察與體會,在歷史方面也十分精通,且懷有為國為民的遠大抱負,在詩歌領域具有很高的成就。尤其是其詠史詩,在唐詩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詠史詩,不管是從內容還是表現手法,都具有獨特之處。本文主要針對其詠史詩及其特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以期對詠史這一題材領域有所深化。
一、見微知著,獨具特色
古詩詞篇幅短小,語言簡潔,寥寥數語卻能千古流傳,廣為人頌。究其原因在于古詩詞善于通過微小的世界表現豐富的內涵。杜牧作為晚唐時期的一位著名詩人,在創作詠史詩中更是體現出了見微知著的態度與精神,并使得其作品獨具特色。譬如《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首詩以赤壁大戰中周瑜借東風火燒曹操麾下戰船的故事作為創作背景,表達了其對吳國僥幸獲勝的看法,即一場東風救了東吳,否則周瑜就要面臨亡國的悲劇,尤其是詩歌后兩句,將獨特的議論融入到“銅雀臺、二喬”的優美意境之中,議論與畫面有機結合,二者渾然一體。但如此優美的意境杜牧卻用了一個“鎖”字,此情此景對于吳國統帥、小喬夫君的周瑜而言,其實是最為不堪的恥辱與慘劇。杜牧直接將決定三分天下的赤壁之戰的戰爭過程撇開,而是著眼于戰爭的結果,用寥寥二十八個字述說了一段影響深遠的史實,見微知著,從一首小詩中折射出了深沉的家國之嘆,并抒發了其有志難報的現實境遇。
詠史詩的題材因襲現象十分常見,這是因為一些歷史事件或者人物的文學性特征非常突出,且能夠體現出普遍性的內涵與蘊意,因而特別容易吸引文學創作者的目光,也易于成為諸多詠史詩的題材。然而,也正是出于這種原因,導致相當一部分詠史詩作者拘泥于前人的思路與框架,難以創作出新穎的題材。但晚唐詩人杜牧卻突破了傳統的束縛,不僅能夠見微知著,而且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比如,曾被諸多詩人詠嘆過的商山四皓這一故事,其作品幾乎都是著眼于功名的進與退,但杜牧《題商山四皓廟》卻運用千篇一律的題目創出了新意,即僅從四皓出山而造成的政治得失進行立論,創作角度別出心裁,可謂立意高絕,見解獨到。
二、審視歷史,感喟現實
品讀杜牧創作的詠史詩,濃重的歷史感撲面而來,且隨之又能透過歷史通道感受到現實的復雜與沉重。從安史之亂之后,唐王朝就開始從鼎盛時期滑落,即便是通過貞元改革與中興等一系列舉措,也沒有讓唐朝原有的繁榮與盛況恢復,國威日漸衰落。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牛李黨爭是導致唐朝墮落的毒瘤,這三大問題的迅速膨脹最終將唐朝送向了滅亡。作為一名飽讀詩書的詩人,杜牧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有著遠大的抱負,特別是當其目睹一些著名的歷史遺跡,感受國家昔日的輝煌之時,就會對當下黑暗無比的時局痛心疾首,對自己報國無門的狀況感到悲憤。歷史與現實的襯托、交錯及對比,促使杜牧對歷史事件的思考與探索更為深入。
詠史詩的一個顯著功能就是能夠通過對歷史表象的藝術性表現,揭露出隱藏在這些表象下面的問題實質,并能有效地抒發創作者的見解、體驗與思想。因此,品鑒杜牧的詠史詩作品,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其有力跳動的心臟與脈搏,另一方面也可以體會到作者在審視盛唐歷史與沒落晚唐時的悲哀、沉痛與無奈,同時還能想象到杜牧為挽救風雨飄搖中的唐朝而竭盡全力的抗爭形象。杜牧詠史詩的字里行間透露著詩人的矛盾、掙扎、迷惘和哀痛,這就使得其詩歌滲透出深沉而堅實的歷史感,以及無可奈何但又引人深入思索的復雜現實感。例如,杜牧在詠史詩《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中就寫道“百感中來不自由”“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將他內心痛苦的掙扎表露無遺,體現出了這位末世有才有識有志之士的悲痛情懷。就杜牧而言,他不僅僅是一位敏感的文人,同時還是一位有報國之志的詩人,他具有深沉的洞察力與思考力,也具有治國之能。望著一步步走向衰敗之路的唐王朝,杜牧一心想要挽救國與民,也愿意將自己的智慧與經歷予以奉獻,但黑暗的現實社會并未給杜牧發光發熱的機會,從而造成其內心十分矛盾與糾結,而這種復雜的情緒也隨著杜牧的創作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了詠史詩中。
三、沉重傷感,冷峻理性
杜牧所創作的詠史詩作品,鮮有對勝利者的贊揚與歌頌,也很少對盛世王朝進行贊歌,給予更多關注的則是對失敗者與沒落王朝的同情。這種獨特的詠史詩情懷,與杜牧所處的晚唐時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詠史詩的創作中,杜牧寄寓了對政治現實的痛恨與感慨,也對黑暗社會進行了有力的抨擊與批判。沉重的歷史傷感之情奠定了杜牧詠史詩的感情基調,冷峻的現實理性又使得其詠史詩充滿了獨特的個性與色彩。
杜牧通過詩歌詠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晚唐實況昭示及警誡后世,字詞之間透露著濃濃的憂國憂民之心,既有對現實黑暗的傷感與沉重,也有對治國理事的冷峻與理性。以杜牧的《春申君》為例,作者通過這首詠史詩感嘆了家奴控制主人的史實,尤其是詩中的“春申誰與快冤魂?”“欲使何人殺李園!”等詩句,更是將杜牧內心的沉思與感傷展示無疑。《戰國策》中有載,春申君生于春秋時期,且是楚國一位喜好養士的貴族,門客多達三千余人,李園就是其中一名門客,但楚考烈皇帝去世之后,李園卻對春申君恩將仇報,將春申君一家滅門,更為令人心寒的還有曾經被春申君收到門下的三千門客并未有一人替其報仇。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事件,通過杜牧的詩筆更顯殘酷與悲涼,這與晚唐多位皇帝被宦官控制甚至殺害的境況如出一轍,且朝堂上下的眾多官員甚至沒有一人敢于挺身而出揭發罪魁禍首。沉重的歷史,傷感的現實,卻都未能讓杜牧陷入痛苦的漩渦與麻木的狀態,對待過往與時下的那份冷峻,始終讓杜牧以理性的眼光剖析與看待問題及局勢,并期望能夠為后世提供警誡。
四、透析歷史,直擊本質
杜牧的詠史詩并不是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簡單闡述,而是通過對歷史的分析與思索,深入挖掘導致各種現象與問題的本質所在,以此總結規律,啟迪后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過華清宮絕句》(其一)這首詠史詩,后面兩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從字面意思去看,這首詠史詩就是對唐玄宗為博楊貴妃一笑,而不惜耗費大量的物力與人力運送鮮荔枝的歷史事件。但若從內在含義去分析,杜牧旨在通過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反映晚唐的現況,即透過表層現象探尋歷史之間的因果聯系。
晚唐內外交困的狀態下,統治者依然沒有警醒,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過著奢靡的荒淫生活,階級矛盾白熱化。因此,杜牧通過述說送荔枝這件小事情,將統治階級的腐敗享樂以及不體恤民情的嚴重后果都表現得淋漓盡致,以此作為對晚唐統治者的警示和教訓。
五、心系國運,體恤國民
杜牧是現實主義詩人的代表,繼承了歷代文人的憂國憂民情懷與責任意識。對于搖搖欲墜的唐王朝,杜牧一心想要救國救民,但卻被黑暗的社會現實拒之門外,無可奈何之下只能將自己對腐敗朝廷與墮落官場的諷刺及憤恨,尤其是熾熱的愛國愛民之情與鴻鵠之志寄托于史詩之中。
在杜牧的諸多詠史詩中,像吳王夫差、陳后主隋煬帝與唐玄宗等一系列歷史人物都是其批判與諷刺的對象,時下的腐敗人物與事件也是其極力抨擊的目標,他深刻揭示了晚唐統治者的腐敗與昏庸,這種直批帝王的膽略與見識都令人贊嘆。譬如,杜牧創作的《泊秦淮》這首詠史詩,以曾經知名的煙花之地、酒樓林立、繁華遍地的秦淮河為背景,寫他看到秦淮兩岸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糜爛生活,聽到刺耳的靡靡淫歌,無比地憤懣和擔憂。詩中嚴厲諷刺了唐朝統治階級茍且偷安以及醉生夢死的墮落生活,展現出了他對封建統治階級荒淫無度現狀的憂憤之情,杜牧心系國運的情懷溢于筆端。
總而言之,無論身處何朝何代的人們,都在現實生活與心靈感悟的雙重世界中穿梭。詩人亦是如此,客觀世界是其生存與活動的場所,心靈世界則是詩人精神家園的所在。不同的現實社會帶給詩人的心靈體驗也是不盡相同的,而緬懷已逝時光、感嘆世事滄桑又是常情,也是詩人創作的根源與動力。杜牧作為晚唐時期的一名詩人,動蕩不安的黑暗現實社會使其經常借酒消愁,通過詠史詩抒發內心的憤懣與憂愁,并以此實現精神的解脫與救贖。因此,對杜牧詠史詩及其特征的研究,對這一題材領域的拓展和深化具有一定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