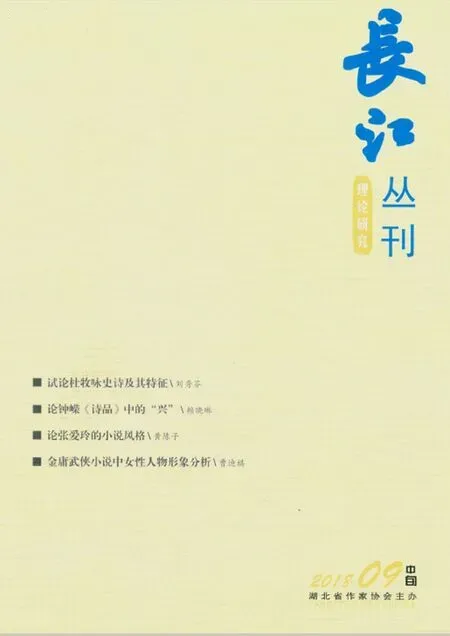淺談我對嵇康《聲無哀樂論》論證過程的幾點思考
■ /
一、《聲無哀樂論》中的主要觀點
嵇康是三國時期魏國著名的思想家與詩人,“竹林七賢”之一,也是當時“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創作于公元260年間,其內容集中體現了嵇康關于音樂的思想觀點。閱讀全文后不難看出,《聲無哀樂論》具有較強的思辨色彩,文章圍繞著“音樂能否表達人們的感情”這一爭論焦點,通過文中設定的“秦客”和“東野主人”兩個人物進行論辯,二人爭論的內容逐步推進,爭辯交鋒有來有回,共分八個回合,在這些回合中逐漸呈現出“東野主人”嵇康的音樂觀點。
在《聲無哀樂論》中,嵇康給予“秦客”的定位是儒家傳統禮教和樂論思想的代表,在此定位上,“秦客”對“東野主人”的觀念進行質詢與詰難,而嵇康本人也在回答“秦客”問題的過程中反復論證了“聲無哀樂”的觀點。不論嵇康的論證在邏輯上是否合理有力,他在中心思想上都圍繞著一點來進行,即對“秦客”所代表的儒家傳統禮樂文化提出質疑。在文中,嵇康闡述了自己有關于音樂的觀點,在他看來,音樂是沒有哀樂之分的并且與人們的主觀情感沒有聯系。從這一點上看來,嵇康對傳統樂論中“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的觀點進行了強有力的駁斥。在嵇康看來,他眼中的“聲”是天地間客觀存在的事物,其自身并非是完全憑借依附于人類而存在,更非依靠人類的情感而顯示其價值,“聲”是不隨著人們情感的變化而改變的。當我們評判“聲”時,標準僅在于其排列組合是否和諧,若和諧,則能稱之為“善”或“美”,并不隨人心的變化而更改。我們可以這樣說,嵇康眼中的“聲”所具有的是一種自然屬性,而非社會屬性。至于人們會產生對“聲”美與不美的感覺,在嵇康看來,這只是一種接受者在聽到音樂時對音樂旋律或曲調是否合適而產生的一種反應,與音樂本身無關。然而,在我看來,嵇康筆下的“聲”其實就是指“聲音”,這種“聲音”包含著“音樂”和“音聲”,只是嵇康有意將物理之聲替代樂曲之聲罷了。以上是我對《聲無哀樂論》的大抵閱讀感受,接下來我想就嵇康關于“聲無哀樂”的論證過程談幾點自己的思考。
二、關于“聲無哀樂”觀點的論證
《聲無哀樂論》通篇都蘊含著魏晉玄學中常見的思辨精神,這種思辨精神必然需要嚴謹的論證過程方可呈現。我想就嵇康關于“聲無哀樂”觀點的論證說一下我的看法。
關于“聲”,在嵇康看來應指“音樂”,但我卻認為嵇康筆下的“聲”既包括自然界中的具有自然屬性的聲音,如風聲、雷聲等,也包括著人們所作之樂曲。篇中“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聲音克諧,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鍾。”一段就指出了這兩類聲音。“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的聲音顯然是指物理的或是自然的聲音,而后面“及宮商集比,聲音克諧,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鍾”一句顯然說明的就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樂曲或音樂。我認為,嵇康對于聲音的區分不夠明確,將上下文聯系起來看,嵇康的“聲”都是在說“音樂”,完全忽略了自然與物理之聲。若是自然與物理之聲,其作為一種自然或物理現象,當然是沒有哀樂之分的,這一點無需論證。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嵇康關于“聲無哀樂”的論證就顯得有失偏頗,不夠嚴謹。
在后文中,嵇康說道:“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雖然聲音的呈現方式與效果各不相同,但卻都表達出了相同的哀樂之情,這不就說明了聲音的表達內容和情感之間的關系不是固定的嗎?此處嵇康認為聲音和感情的關系是不固定的,這樣的觀點是由前文“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而哀樂之情均也。”論證得來的。我認為,“音聲無常”的意思是,一定的聲音并不一定表示哀或者樂,對于“音聲無常”可以這樣理解:是音聲與意義或感情的關系沒有固定的搭配。嵇康由此來推出哀樂不是聲音自身的屬性。然而,這里用“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來說明聲音無常,這樣的論證是不夠嚴謹的,本身論據也并不充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否真有聽到哭聲感到喜悅,聽到歌聲而感到悲傷的情況是難以確定的,不得不承認現實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比如我們聽到初生嬰兒的哭聲會有“喜獲麟兒”的感受,而聽到一首悲傷的歌曲便會感到心中戚戚,但更多情況下卻不是這樣,因此值得我們去懷疑這種現象的普遍性。進一步而言,人們因為悲傷而哭泣、因為歡樂而歌唱是符合人類的自然本性的,從這一角度來說,人們的哭泣和歡樂相對于音樂的悲傷和喜悅而言就不是“無常”的,而是“有常”的。我認為,嵇康在此處論證中是用一個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其真偽的不夠嚴謹的說法作為先決條件和前提,用未經證明的說法來推出結論的論證過程,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是有問題的。
接著,嵇康又說道:“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這句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然而和諧組合在一起的聲音是最能打動人的。辛勤勞作的人用歌聲來表達他們的生活經歷和狀態,感到快樂的人手舞足蹈,以此來表達他們的內心的喜悅。人們的心中有悲傷的情緒,就會用哀傷的語言表達出來,把這些話組織起來就成了人們眼中的詩,而把聲音與各種旋律組織起來就變成了音樂。從事不同工作的人們一起吟詩歌唱,很多人圍聚在一起傾聽這些聲音,聽眾的內心被這些聲音打動,感受到歌詠者的悲傷之情,他們的嘆息還沒有停止,就已經淚流滿面了。嵇康此段本是為了接著論證“聲無哀樂”,可我卻認為,這樣行文恰恰是論證了“聲有哀樂”。正因為心中有情感波動,所以才會說出富有激昂情緒的話語,說出的話經過組織和加工就變成了詩歌,人們哼唱發聲就成為了音樂,這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現象,卻被嵇康用來論證“音樂沒有哀樂之分”的觀點,我認為是十分不恰當的。而且,這一段給人呈現出因為音樂而給人帶來的富于生活氣息的現實景象本是十分具體形象的,緊接著在下文中嵇康又說道“和聲無象”,我認為這存在著邏輯上的一種斷裂。對于“無象”,我的理解是沒有具體的形象,但是在上文“泣涕流漣”的景象出現后,再話鋒一轉,說道音樂沒有具體的形象可讓人了解與觸及,我認為還是稍有偏頗的,而我也更愿意將這種邏輯上的斷裂視為是嵇康有意為之。
總言之,《聲無哀樂論》的第一段是嵇康“聲無哀樂”這一核心觀點的提出,也是總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立論階段,接下來的七段是駁論。然而,在其立論階段嵇康做得并不完善,相反,我認為是存在較多問題與偏頗之處的,更不說還有邏輯上的斷裂之嫌。
首先,“聲無哀樂”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命題,需要論證者提出嚴謹的論據加以逐層分析,我認為嵇康在這一點上做得并不好。他在論證的時候混淆了物理的聲音和音樂之間的差別,自然界中的許多聲音顯然是沒有哀樂的,風聲、雨聲等不過是一些物理現象所引起的,但是音樂卻是人們結合其情感經歷和生活經驗創作出來的,怎么會沒有哀樂呢?創作與非創作之間是存在很大區別的,創作必然裹挾著創作者的個人主觀情感,情感必然包含著哀與樂,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認為嵇康的“聲無哀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帶有些許詭辯色彩。他用自然或物理聲音的特征來代替音樂或樂曲的特點,力求讓人覺得他的觀點準確和有理有據,這本身是站不住腳的。
其次,“音聲無常”是一定的普遍規律嗎?這仍然是值得我們去問一個為什么的,我們不應該先入為主地輕易接受這個論證的先決條件而不加辨析。我認為,“音聲無常”應該區別來看,從音樂創作的無限自由的空間而言,每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個性與立意,想法的不同帶來的是曲調的別具一格,從這一點上來看,音聲當然是無常的。但是,若從哀樂之情在樂曲中的呈現方式而言,又有著讓人們習以為常的大致的范式。就好像我們在聽一首樂曲時,快樂之曲往往比較輕快靈動,悲傷之歌往往旋律沉重,節奏緩慢一樣,這是為人們所廣泛接受的,人們悲傷了要哭,快樂了要笑,這是有著心理依據的,也可以說是有常的。
再者,用嵇康的話來說,“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按照他的推論,既然自然的聲音并非來源于人的創造,那么聲音與人的關系就只能局限在聲音和所謂的“接受者”之間的關系。然而我們知道,音樂與人的關系十分復雜,當人們聽到聲音的時候就意味著這其中包含著兩段關系,其一是創作者和他們所創作出的音樂之間的關系,其二是創作者所創作出的音樂與接受這些音樂的聽眾之間的關系。因此倘要論證文中“聲無哀樂”的這一觀點,我們就必須要回答創作者與他們所創作出的音樂作品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很明顯,嵇康在他的論證過程中有意回避了這個關鍵問題。音樂作品是按照創作者個人的主觀意愿創造出來的,其中包含著他創作時的情感與心境,創作的人使用特定的音符、旋律、節奏對自然的聲音做了編排與改造。因此,創作者所面對的音樂不是“其體自若而無變”的形態,對于這種可稱得上是人們自我創造的聲音,又如何能以沒有情感上的哀樂之分來加以描述呢?我認為,嵇康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也回避了在這一環節上的論證,這對于論證的嚴謹性而言無疑是十分不妥的。
三、結語
我們可以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視為一篇音樂新解之作,也可將之看作一篇富于哲思的論辯奇文,或許作為論辯之文而言,它的論點、論據和論證過程還不夠嚴謹,在邏輯上還存在著些許斷裂,但是這并不能抹殺其蘊含在文章中的深厚的人文意義和精神追求。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嵇康《聲無哀樂論》中“聲無哀樂”的思想觀點,若能棄其糟粕,將文中些許詭辯之言擯棄,取其精華,將文中追求個性解放,反抗儒家傳統禮樂制度的桎梏的自由之精神發揚,我想,可能這才是我們觀照現世時最能收獲感悟與幫助的。
注釋
:①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聲無哀樂論[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436.
②③④同上,第437頁。
⑤同上,第438頁。
⑥同上,第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