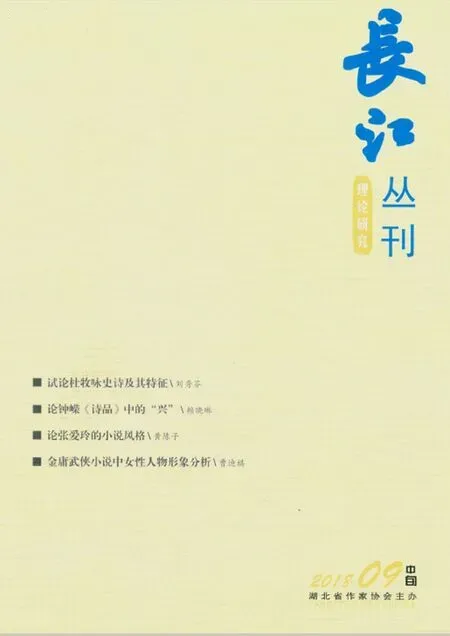伊沙詩集《車過黃河》德譯本研究
■ /
一、前言
在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前后,中國當代文學就受到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這些被關注的優(yōu)秀作品首先需要經(jīng)過成功的翻譯才可獲取世界的目光。從這個角度講,可以說優(yōu)秀的文學翻譯與文學作品本身同樣重要。文學翻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翻譯,需要譯者對原文中的文藝描述進行藝術再創(chuàng)造。詩是一種獨特的文藝表現(xiàn)手法,無論從本質上還是從藝術形式上都是對于真理的追求。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藝術的本性是詩,而詩的本性卻是真理。”目前以詩歌來表現(xiàn)真理正是中國文藝界很多人的追求。其中當代著名作家伊沙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其詩歌中獨特的藝術表現(xiàn)手法早在20世紀就受到了西方的關注。2016年奧地利人維馬丁(Martin Winter)在奧地利推出了伊沙詩集《車過黃河》的德漢對照譯本,德語名為“überquerung des gelben Flusses”。該詩集中的詩篇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德語讀者的?這些文藝作品中的“詩與真”是如何在德語譯文中得以體現(xiàn)的?譯者又是如何再現(xiàn)原詩歌中的文藝的意境之美?這些都需要從文學翻譯的本質上加以研究。
二、文學翻譯的本質
文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藝術,因此很多人認為文學翻譯是基于文學創(chuàng)作之上的藝術再創(chuàng)造。首先,譯者就要一方面積極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對原作進行文藝再現(xiàn),另一方面又不能隨心所欲地夸大其詞,否則就成為脫離原作的胡譯、濫譯的自由創(chuàng)作。其次,譯者還要正確認識與作者的關系,作者是創(chuàng)作主體,譯者是翻譯主體,而文學翻譯是譯者對于原作的文藝再現(xiàn)的一個過程,即譯者的文藝再現(xiàn)需要以作家的原創(chuàng)作為前提。第三,由于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存在一定差異,因此譯者需要處理好語言風格特點以及藝術審美價值。讓譯文讀者也能夠感受到原作中源語文化的韻味之美。
在文學翻譯中譯者是藝術主體,其審美對象是作者和原作。譯者發(fā)揮自己的審美心理機制,對作家在原作中通過藝術形象所反映的自然和社會生活進行審美再體驗,然后通過譯語把自己的審美感受表達出來。對譯者來說,把握作者的原始審美體驗是關鍵。陳圣生先生在《現(xiàn)代詩學》中指出詩性思維是一種“全面的綜合性思維”,是“原創(chuàng)性的思維”是“具體化和形象化的思維”,它包括“神話式的原始思維”和各種“藝術思維”。(朱光潛,151)作家善于詩性思維才能賦予作品以詩意,同樣身為文學翻譯工作者也要具備詩性思維。這是因為譯者身兼讀者、譯者與作者三重身份,可以說譯者首先要具備詩性思維,這是成功的文學翻譯的前提,接著就需要譯者通過努力創(chuàng)造將原作描述的文藝境界在譯入語中再現(xiàn)出來。近現(xiàn)代很多著名的文學家如郭沫若、魯迅、錢鐘書、余光中等本身也是成功的翻譯家。中國一些當代知名作家如伊沙也在創(chuàng)作中進行著翻譯,此外其詩作近年來也被翻譯成了德語。
三、伊沙詩集《車過黃河》德譯本及其藝術真實
伊沙不僅是中國當代著名詩人與作家,也是翻譯家,他原名吳文健。現(xiàn)居陜西省西安市,任教于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自從20世紀末以來伊沙就一直在國內外的詩壇上頻頻創(chuàng)作。他的詩作不僅獲得大眾關注,也遭受到一些人的非議,是非官方反學院的“民間寫作”的代表詩人,同時他還是《新世紀詩典》主編。在當代中國詩壇,伊沙是口語詩的旗幟性人物;口語詩是漢語現(xiàn)代詩的重要分支,“近十五年來,口語詩因其涌現(xiàn)的實力作者和佳作之多,已蔚然成為當代詩寫作的主流。”(鐘潤生,58)。伊沙跟妻子老G一起翻譯出版了《當你老了——中外名詩100首新譯》、《布考斯基詩歌快遞》、《布考斯基詩選:干凈老頭》、《特朗斯特羅姆:最好的托馬斯》、《生如夏花、死如秋葉:泰戈爾名詩精選》。伊沙可謂是名副其實的作家兼翻譯家,也因此而獲得西方世界的關注。
20世紀90年代德國北威州的一個作家旅行團來華旅行。他們在回國后的一年即1994年出版了一本書《雞年—一趟中國行的報告》,德語名“Im Jahr Des Hahns.Zeugnisse einer Reise durch China”。該書共收錄了伊沙的10首著名詩作。這些詩分別為《車過黃河》(Im Zug den Gelben Fluss überqueren)、《歷史寫不出的我寫》(Das schreibe ich,was die Geschichte nicht schreiben kann.)、《叛國者》(Der Landesverr?ter)、《我是一筆被寫錯的漢字》(Ich war ein Zug falsch geschriebener Schriftzeichen)、《諾貝爾獎:永恒的答謝辭》(Nobelpreis:immerw?hrende Dankesrede)、《名片》(Visitenkarte)、《野種之歌》(Lied eines unehelichen Kindes)、《強奸犯小C》(Der Vergewaltigter Kleiner C)等十首詩作,其譯者名為張瑞。這本書收錄了伊沙早期的一些著名詩作,單從這些詩的題目來看,其獨特的寫作風格早已刻印在德國讀者心中。
2016年由維也納出版社Fabrik Transit出版了由維馬丁翻譯的伊沙詩集《車過黃河》的漢德對照版的上冊,該書收錄了伊沙1988-2009年間的一些作品,下冊于2017年夏季面世,收錄了伊沙2010-2016年間的一些較新詩作。因是漢德雙語版本,所以每冊就厚達好幾百頁。2017年2月10號德國知名報刊《法蘭克福匯報》于周五的報紙副刊上刊登了伊沙的著名詩作《當年的情書殘片》,德譯名“Aus alten Liebensbriefen”。這首詩歌第一次在德國以報刊形式呈獻給德國大眾視野,可見其藝術魅力所在。以下來欣賞一下《車過黃河》這首詩及其德譯:“列車正經(jīng)過黃河,我正在廁所小便,我深知這不該,我應該坐在窗前,或站在車門旁邊,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象個偉人,至少象個詩人,想點河上的事情,或歷史的陳帳,那時人們都在眺望,我在廁所里,時間很長,現(xiàn)在這時間屬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黃河已經(jīng)流遠。” 以下為該詩作的德語翻譯:üBERQUERUNG DES GELBEN FLUSSES —Der Zug überquert den gelben Fluss,ich hab gerade ein kleines Gesch?ft,ich wei,ich sollte nicht auf dem Klo sein,ich sollte vor meinem Fenster sitzen oder stehen an einer Tür,linke Hand an der Hüfte,rechte Hand an der Stirn,Ausschau halten wie ein groer Mann,oder wenigstens wie ein Dichter,in Gedanken an Dinge im Flusse,an alte Rechnungen aus der Geschichte,alle Menschen halten Ausschau,ich bin auf der Toilette,eine ganz lange Zeit,diese Zeit geh?rt mir,eine Nacht,einen Tag hab ich gewartet,in der Zeit meines kleinen Gesch?ftes,ist der gelbe Fluss weit weg geflossen.
通過對比不難看出,維馬丁的德譯本不僅抓住了原作的神韻,也抓住了中文口語詩的特點,通過樸實的文藝再現(xiàn)表達了原作中的藝術真實。這首先是因為譯者本身也是詩人,善于用德英漢三種語言寫作。同時伊沙跟他互動很多,也曾把他的英語詩歌翻譯成漢語。這是詩作翻譯中藝術風格與藝術審美得以保留的前提。其次,譯文首先在形式上與原作保持一致,在翻譯中做到了形式美的統(tǒng)一。第三,譯文一字一句緊扣詩作中的“音”與“意”,將詩作中的詩性思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如從標題“車過黃河”再到第一句“列車正在經(jīng)過黃河”在德語中分別使用不同結構對其進行了相異表述。再如“小便”與“一泡尿”都處理成“kleines Gesch?ft”這樣在德語中比較俗稱的口語化的表達,可以說做到了與原詩風格一致等。諸如這樣的翻譯處理在整個詩集的其他譯作中隨處可見。這些都體現(xiàn)出了譯者獨到的藝術思維以及對詩作中原創(chuàng)性思維的最大保留。
四、結語
伊沙不僅在國內文壇的知名度相當高而且在國外也享有盛譽,而他的詩作之前在德語文壇卻并沒有引起更多關注,特別是評論界并沒有投去應有的目光。他的詩作“車過黃河”作為中國當代口語詩的創(chuàng)始代表,以其質樸且獨特的形式表現(xiàn)出了“詩與真”。這些也正是文學翻譯需要把握的關鍵。譯者本身需要跨越文化的藝術審美,通過文藝再創(chuàng)造來表達原作中的“弦外之音”與“意境之美”。奧地利人維馬丁成功地翻譯了伊沙的詩作,并且將原作中的詩性思維與自己的審美感受結合在一起再現(xiàn)于譯文中。相信隨著《車過黃河》德譯本上下冊的相繼出版,將會在德語區(qū)有更多人閱讀伊沙詩作,同時進一步認識這位用詩性思維書寫真理的中國當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