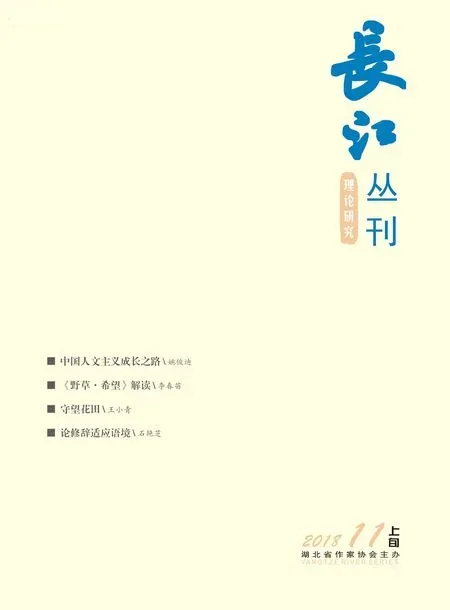從法學與醫學的相通之處談法學教育的理念
■羅 強/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近些年,國內高等教育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科際整合”的理念,有學者指出,面對形形色色的社會問題,依靠單一學科知識探尋解決方案是不足夠的,需要挖掘相關學科間“共同的工作假設、共同的理論模型、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語言”,以彌補單一學科知識在解決社會問題時表現出的不足。對此,筆者深以為然。人類知識體系的學科劃分固然有其特定的價值和意義,但由此造成的封閉性與局限性也不可忽視。法學與醫學原本就有著諸多“天然”的相通之處,通過對比分析法學與醫學的共通之處,并由此對法學教育應具有的理念進行檢討和反思,具有特別的意義。
一、法學與醫學的相通之處
第一,法學與醫學在權利領域有交叉。權利概念是法學的核心范疇,法學甚至可以說就是圍繞權利而建構的一系列知識體系。現實中,各種法律活動所圍繞以及處理的,也都可以歸結為相關當事人的法律權利。這一點是顯見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從表面看來,醫學處理的問題是人類的各種疾病,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以及社會觀念的更新,人們開始普遍地將一些醫學問題納入到法律視野來加以觀察,從而使法學與醫學有了顯著的交叉地帶。在當代社會,由于法律活動與醫療活動的參與者都是“社會動物”——人,因此,醫學領域的問題“溢出”學科邊界,成為跨界問題已是常態。第二,法學與醫學都注重秩序的維護。秩序,毫無疑問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重要價值目標之一。法學中所強調的秩序是一種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意味著各司其職、定分止爭,意味著社會中的各種主體都依規則行事,由此所達成的一種和諧、平衡及穩定的狀態。而反過來,假如規則意識喪失,社會主體的權利義務定位陷入混亂,那么社會有機體就一定會陷入“病態”,這也就是學者們所謂的“社會病”。“社會病”這一術語其比喻來源其實就是社會與人體二者之間的相似性。而對于這一點,早在古希臘時代的哲人柏拉圖就已經有了論述。根據柏拉圖的見解,正義的本質是一種和諧、平衡狀態,這一狀態既有外在于人的,即城邦的和諧平衡;他指出:“正如疾病是身體的不幸,不正義則是靈魂的不幸;它不幸是因為它意味著靈魂處于病態,失去了健康的平衡與秩序,取而代之的是混亂無序。”柏拉圖正確地指出了疾病的本質——失序。由人組成的城邦與社會倘若失序,也會使其處于病態之中,此時,同樣需要法學研究者去探尋患病的原因以及治療的方法。第三,法學與醫學解決問題的邏輯思路相同。醫學領域中解決疾病的診治問題,在邏輯上的思路可以理解為一種簡明的三段論推理模式,這一模式與法律領域的司法三段論極其相似:醫生面對的病患癥狀如同法官面對的案件事實,醫生頭腦中存儲的疾病特征如同法官頭腦中的法律規則,從這二者進而推導出應得的結論——對于醫生而言是診斷結果,對法官而言則是一紙判決。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正是這一思維過程的相似之處,使得法學教育中提出“診所式”或者“臨床式”教育成為可能。
二、法學與醫學的相通點對法學教育理念的啟示
第一,法學教育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是一種發現問題的能力,也是一種思維層面對問題存在的敏感度。作為法律人,無論是對于理論知識的學習,還是對案件事實的分析,抑或對社會事件的觀察,都需要具備足夠的問題意識。目前,國內雖然早已從西方國家引入了“診所式”法學教育,但由于各種原因,在現實中還是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狀況。筆者認為,雖然全面推廣“診所式”或“臨床式”法學教育有一定難度,但在本科階段的法學教育中,著重培養學生基礎的問題意識還是能夠做到和應該做到的。只有具有問題意識,才能切實地將法學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第二,法學教育應當培養學生的未來意識。早在兩千年前,希波克拉底就提出要注重醫生預見能力的培養。由此,醫學逐漸發展出一個重要概念——預后。這一術語主要是對疾病的發展和未來可能的結果做出預測。同時,預測并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種手段。借助于當下的預測,醫生要有針對性地調整自己的診療手段,同時要指導病人的生活管理,使得病程發展能走向最好的結果。這一概念及做法充滿了未來意識,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疾病。相較之下,法學教育領域對于這種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聯結鮮有強調。第三,法學教育應當強調謹慎判斷的思維習慣。無論法學還是醫學,其判斷的做出雖然都與三段論模式緊密相關,但絕不是大小前提的簡單相加和計算。現實生活中每一個病例和案例,都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學校、課本所提供的,是剔除了諸多細節與個性,僅將特征突出的共性部分保留下來的典型。對這一差異保持清醒的認識是認知的前提,在此前提下,走進社會現實的法律人,應當時刻提醒自己:任何一個細微“參數”的變動都可能引發“蝴蝶效應”,進而帶來最后結論的巨大變化。對于醫生而言,診斷結果的偏差,會直接影響到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對于法律人而言,一個錯誤的判斷也會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切身權利。因此,在做出結論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這一思維習慣需要在法學教育過程中加以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