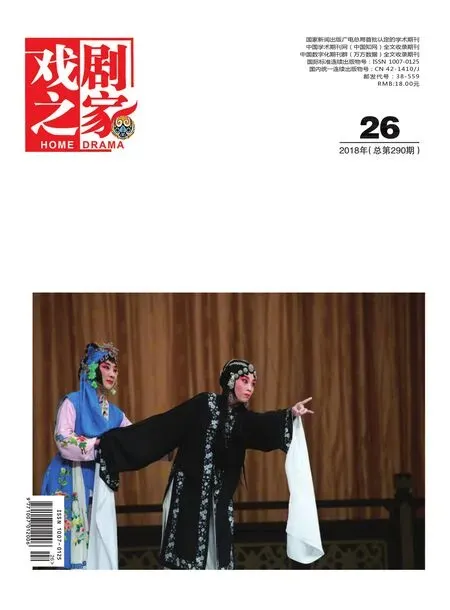在一帶一路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樂舞回望
魏燕鵬
(云南藝術學院 云南 昆明 650033)
一、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記憶。”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致使西域與中原的交往日漸頻繁。《后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座、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漢代的龜茲曾是西域諸國中最大的一個綠洲王國,佛教傳入西域后,它很快成為絲路北道天山南部地區一處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古籍記載魏晉時期龜茲已有上千所佛塔廟宇,隨后在庫車、拜城等處又開鑿了大量石窟。壁畫中描繪的佛像、菩薩、梵天、比丘和比丘尼,以及眾多的天神和諸天供養等構建了一個絢麗而奇妙的佛國世界。在壁畫內容與布局上,貫徹了濃郁的宗教哲理,透露了當時的佛教發展和社會狀況。
絲綢之路的對外交流在唐代達到頂峰,許多唐詩均有所記載。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胡旋女》便將胡旋舞描述得惟妙惟肖:“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起,中國的樂舞開始向海外傳播擴散,走出國門,實現了文化輸出。明清時敦煌樂舞文化又以靜態的壁畫形象通過基督教傳士和俄、英、美、法、日等國探索家掠奪式的粗暴方式進行傳播。
二、篳路藍縷 玉汝于成
絲綢之路隨著朝代更迭變遷,與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出新,以適應時代需求。由于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程度不斷升溫,原本流變于傳統生活的舞蹈得到了大力的保護與發揚。如近現代史上的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這部舞劇最大的藝術成就就在于它在“復活”敦煌壁畫舞蹈形象的同時還創建了一個自成一派的“敦煌舞”體系,徹底改變了過去中國民族舞劇只以戲曲舞蹈為基礎的做法,使觀眾耳目一新,既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整部舞劇又融合了中國古典舞、敦煌舞、印度舞、黑巾舞、波斯馬鈴舞、土耳其舞、新疆舞等各類藝術形式于一身,為敦煌題材類的歌舞注入了新的思路,新的活力,使得敦煌題材類的歌舞更加多元化。
另外,針對絲綢之路樂舞藝術的傳承問題,政府特別設置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這類“原生型”的樂舞傳承人提供了傳授技藝和維持生計的平臺及途徑。這些民族民間舞蹈傳承人通過“口傳身授”的方式,將最正統的“傳統”民族民間舞蹈帶入課堂,為原本固定而刻板的校園舞蹈課程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這種“活態傳承”的方式是當下最廣為流傳的民族民間舞蹈傳承方式,如福建省閩南地區男女老少皆愛的“拍胸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存在,這種舞蹈主要是通過“打七響”的方式,來表現出閩海之濱人民特有的豪爽干練的氣質。被譽為閩南地區傳統民族文化“行走的活化石”。
三、歲月變遷 絲路永存
筆者通過縱向對絲綢之路上各個時期舞蹈的誕生思想和知識體系進行淺顯梳理,同時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另一方面,也算為全民健身另辟蹊徑,因為目前社會上最廣為流傳的廣場舞其實最早來源于民間舞蹈,包括少數民族的舞蹈,而這些舞蹈均來自于絲綢之路上的樂舞。因此,絲綢之路上的舞蹈充分滿足了大眾渴望娛樂的內心需求和現實需求,為大眾尋求一種和諧的相處之道提供豐富資源。
絲綢之路樂舞的發展如何繼續,需要的是后來者的創造和勇氣,我們必須要將絲綢之路上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起各種聯系,將各類歌舞文化悄無聲息的編織交融在一起。這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發揚勇于探索和愿意擔當的精神,奮力將未來將絲綢之路上的樂舞發展成為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文化底蘊深厚、結構完整、形式多變的新型樂舞文化體系,在中華民族舞蹈文化歷史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為世界舞蹈文化貢獻中國力量 ,這些都是未來需要我們去務實的具體工作。
四、結語
綜述,絲綢之路上的樂舞藝術是隨著時代變化而動態發展,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腳步,也是藝術與生俱來的發展規律。廣大文藝工作者必須做好艱苦卓絕付出的巨大決心。正如戴愛蓮先生所言:“今天的中國,一定要有中國特色的精神,中國特色的文化和中國特色的舞蹈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