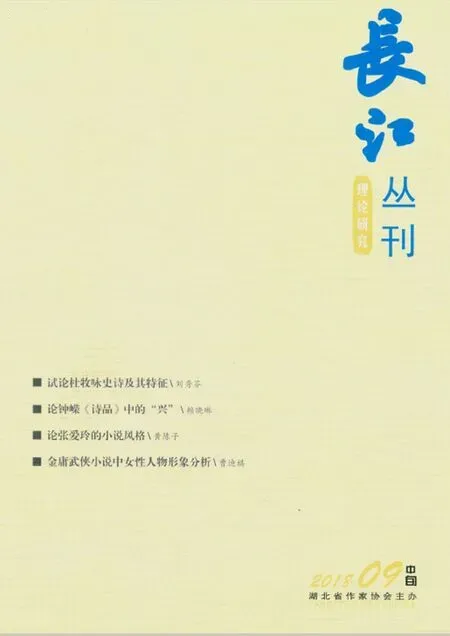安樂哲儒學人生觀初探:成人至仁
■ /
一、安樂哲對“仁”的理解
《說文解字》中說:“仁,親也。”孔子以及他后來的許多追隨者也都根據“愛人”來定義“仁”。其實,“仁”作為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其本身就不是一個確定的表述。安樂哲通過分析學者們對于“仁”這一概念的各種不同詮釋與見解,明晰了“仁”與“人”之間的內在聯系。
首先,安樂哲通過例舉杜維明詮釋“仁”的觀點,意在表明雖然“仁”這一隱晦的、具有深刻內涵的真理不能被確定地表達出來,但是這并不是孔子有意而為之,相反,孔子其實在努力地向他的學生傳達他所理解和感受到的“仁”的真正意義。其次,安樂哲又例舉出陳榮捷關于“仁”的解讀,他認為:“孔子是第一個將‘仁’作為一般價值來感知的”。不置可否,杜維明顯然追從了陳榮捷的解讀,將“仁”解釋為某種內在品格或價值,把它描述為“關涉內在力量和自我認知,是象征性地表達創造性社會的一個無可窮盡的源泉。”在這里,安樂哲并沒有直接對二者的觀點做出評價,而是進一步通過例舉出了芬格萊特不同思想。他說:“芬格萊特堅決反對這種他認為對該術語不合宜的心理分析式解讀……學者們確實一直有將仁‘心理學化’的傾向,將其視作一種由‘客觀’社會標準以及其他我們遵從或適應的禮儀行為所體現的‘主觀’情感。‘仁’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翻譯為心理稟賦,而禮儀行為則顯然是它的種種有形說明。芬格萊特告誡我們要反對這種簡化論……”顯然,芬格萊特反對通常學者對“仁”的內在詮釋,而是贊成某種外在的解讀——其中“仁”是一種使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個體及其作為行動者的傾向的舉止。在例舉了陳榮捷和杜維明,以及與之對立的芬格萊特的觀點之后,安樂哲評價說:“他們雙方截然不同的對‘仁’之‘內在’、‘外在’的解讀都消弱了該概念。因為他們并沒有充分關注到該術語本身。”[1]
顯然,安樂哲并不贊同他們的理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Perer Boodberg關于“仁”的論述,即“仁”與“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相等性。他認為:我們必須更多注意到儒家著作中‘仁’、‘人’的共同定義,例如,《孟子》和《中庸》都明確宣稱“‘仁’者,‘人’也。”安樂哲認為二者是共通的,準確地說,二者都意指“人”這一概念,而區分在于其性質:“人”的兩個不同層次。“仁”不僅是一種狀態,一個特征,還是一個“及物動詞”,即人性的轉化,不僅意指已獲得“仁”這一品格的人,還包括此一品格借以實現的過程:“成己,仁也。”(《中庸》第二十五章)
二、安樂哲對“仁”與“成人”聯系的解讀
孟子所謂:“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董仲舒有如下描述:“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春秋繁露·仁義法》)安樂哲借用孟子與董仲舒之言表達了對于“成人”的看法。盡管“仁”是針對“我”之外而言的,但是“仁”這一行為的基礎卻是由“我”內部引導的,即自我的“義”感。因此說,“成人”既是吸取他人塑造自我的過程,又體現了個體之“義”的運用。而且,個人之“義”會在運用和領受他者之“義”的過程中獲得提升和發展。“成人”的過程是既對己也對人。在此一過程中,個體既影響周圍的人也為他人所影響。[1]我們每個人不僅是獨立的、分離的個體,還是“自我”與“他者”、“我”與“我們”、“主體”與“客體”……之間不可分割的連續的統一體。正如個體是不能脫離整體而獨立存在的,離開了整體,個體也就不復存在了。“成人”既是個人本身的吸收與修養,也是對個人之外的一種闡發與表達,只有在兩個過程都成立且具備的前提下,才能夠促進“成人”,否則是無法達到的。
孔子以及他后來的許多追隨者都根據“愛人”來定義“仁”。安樂哲認為,古典中國傳統中“愛”這一概念與“成人”過程“受”的方面相一致,傳達了某種“宜”的意識。“愛”是將某人納入個體關心的范圍,且據此使之成為自我整體的一部分。當這一領受處在互給情況的時候,“愛”就是自我可參照其所愛來描述的盟約。《荀子》中有一段描述孔子問他幾個鐘愛的弟子對“仁”認識的對話,很有啟發性:
子路入,子曰:“……仁者若何?”子路對曰:“……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仁者若何?”子貢對曰:“……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仁者若何?”顏淵對曰:“……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2]
就這一段對話來說,孔子至少認為,“仁者”之愛是自我和他者彼此契合的基礎。首先,讓他者關心自己所關心的事情,這是最低層次的,值得贊揚的,但是卻不乏自私;其次,把別人關心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這也許是更高一些的層次,不足之處是這可能會忽略了自我之切身之事;那么,最高的層次就必然是具有相互性的,將自我與他者所關切之事融而為一。換句話說,最高的層次是在自我——他者形成的一個整體中互相決定的。安樂哲的觀點是,“自愛”意味著要關懷我置身其中的那些特殊角色與關系,將關懷它們當成滋養自己,將它們視為個人實現的根本源泉與實體——“自愛”,愛的是與我的妻子、孩子、同事等等我所置身其中之關系。[2]這便是“成人”的內在性。
至于“成人”的能動性,孔子說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孔子說仁者“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說在自己具有人生意義關系中長期滋養,從而使自己與他人同時提高做人的價值。安樂哲這樣認為:“自愛”從直接情感出發,這是說,做人的主導性是用心——是思維也是情感。頭腦思維與心的情感不分,認知與感情也不可分。沒有離開感情的理性思維,也沒有無所認知的情動。中國古代看的是宇宙觀看的過程和變化,而不是形定與靜止。因為是這樣看問題,所以講“心”首先是說“思維”與“情感”兩件事,然后才從這里比喻地講道與“思維”和“情感”相聯系的具體器官。“心”只是一個比喻性器官,因為事實上心是一個沒有具體界限的活動散發中心人與人互相誠信關系發展而成的所在之點,其實是個充滿思慮的情感水庫,在我們的心和腦中蕩漾。這只是說,充滿創意的個人相互交往,人的互相做的與經歷的事情,展開著互相對待的情感,這才是充滿意義的關系的源泉和本質。[2]
三、人生觀的圓成——成人至仁
安樂哲認為,圓滿的人生可以有不同的構思和表現。在儒家的人生觀中,仁行為的道德優點如同一幅藝術作品一般,是精湛技巧與想象力結合的具體體現。仁是道德的儲備,人人皆有,它可以提升、改進人生的經驗。“仁”指的是一個人整體性的行為:人修養而得的認知感、審美感和道德感,這些是通過“角色”和關系而喻意的,它們結合在一起,就成為一個人的品格。人不僅是智能的、精神的,也是形體的,是一個人的儀態與舉止,一個人的舉手投足與身體語言交流。對于怎樣找到一種適當語言,來表達儒家思想的以關系構成的“成仁”,儒家提出的是一種整體性觀念的通過修養而成的具體人的行為。儒家的道德人生觀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的成長觀,也即,圓滿“成仁”,成為“大人”,成為至“善”之人;“成人”,成為“君子”。[3]
安樂哲通過對傳統經典文獻的研究,綜合分析其他學者對于該觀點的解讀,構建了他自己對于儒家人生觀“成人至仁”的獨特見解。雖在對于“成仁”的理解中難免有所疏漏,不能做到盡善盡美,但還是解讀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對于“仁”的解讀與重構仍在日益更新,安樂哲作為中國古典思想文化的重要傳播者,其研究成果直接影響到世界各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安樂哲以海外學者的身份,用一種特殊視角幫我們更好地認識和解讀了儒學人生觀的深遠意義與影響,讓我們可以從“他者”的角度更好地了解自己,同時,也為中國文化能夠融入世界文化的大家庭并發揮其特殊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