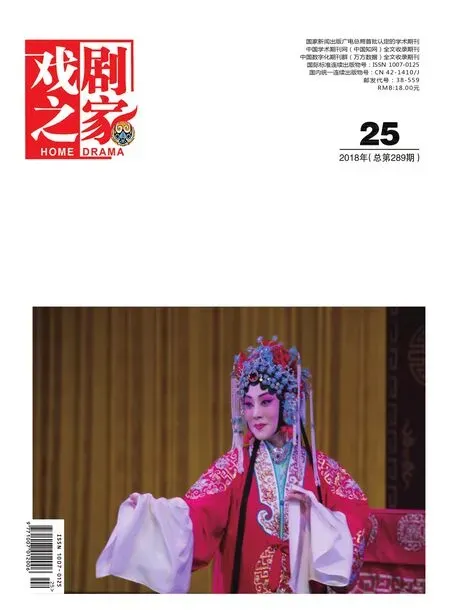《流浪》
——心無處可依,身何處“流浪”
馮 璐
(北京舞蹈學院 北京 100000)
若我沒有過流浪的日子,何曾知道什么是孤獨
若我沒有過流浪的日子,何曾明白友情的可貴
若我沒有過流浪的日子,何曾思念家人的陪伴
若我沒有過流浪的日子,何曾思考心底的聲音
若我沒有過流浪的日子,怎與你分享我的人生
走自己的路,回頭講自己的故事。
一、心無所依便是流浪
當聽到“流浪”這一詞時,你也許會覺得既熟悉又陌生。你或許曾經無數次地在書中、電影中、歌詞中見到過這個詞,聽過許多屬于別人的流浪故事,但它距離你自己仿佛又是那么的遙遠。離開自己熟悉的城市、熟悉的人,獨自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需要勇氣與決心。現代漢語詞典對于“流浪”這一詞的解釋是:“生活沒有著落,到處轉移,隨地謀生。”這一解釋毫無疑問的是為了獲取物質層面的滿足而進行的流浪,那么,還有其他的原因會使一個人選擇去流浪嗎?高曉松說過:“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我們日復一日地在都市的喧囂與浮躁的生活中循環往復,被欲望包圍,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以為用物質填滿了內心,便不會流浪。但當我們真正得到了物質的滿足時,卻發現,心,空了。三毛說:“心若沒有棲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心無所依的那一刻,便是流浪。
二、孤單是一群人的狂歡
五名舞者身著棕色粗布麻衣,滿是破洞的上衣,有著苦行僧衣衫襤褸的滄桑感,又有著流浪者骨子里放浪不羈與向往自由的態度。當他們感到迷茫不知所措時,他們將手伸進破洞衫中,任游自己在這些破洞中游走穿梭,這些破洞就好像一個個迷茫的出口,擾亂著流浪者的心緒…… 作品中看似是五個流浪者的流浪,實則是一群人的獨白,他們擺脫浮躁的生活,離開喧鬧的城市,行走在流浪的路上,聽溪水潺潺流淌,聽寺廟梵音彌彌,然而這一切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這五個流浪者實則是一個人的心里構建,也代表著一個人看待事物的不同方面。編導巧妙地使用五個人的表達,來襯托出一個人的孤獨。他們就像是分身一樣,在相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里統一著,交錯著。正如劇中五人同時做相同的動作,代表著一個人內心的合體;而當四人與一人在同一時間里伴著相同的音樂,在不同空間做著不同的動作時,則是在分裂與對比中完成對一個人內心復雜世界的描繪。劇中四人用身體疊起人墻,一人站在中心,在雙腳不斷交換重心的過程中使身體隨之左右擺動,忽然,中間的人倒下,隨即人墻坍塌,正如支撐流浪者內心已久的信念突然間崩塌。
三、古老與現代的碰撞
整個舞段中沒有一句對白,編導選擇了舞蹈最原始最純粹的表現形式——用身體語言去訴說。流浪這個話題是亙古不變的,由它可以聯想到幾百年前中國古老民族的悠久歷史以及留在當下的深厚民族文化。中國的民間舞流傳至今,經歷了時間的考驗,作品以中國民間舞的動作元素結合現代舞的身體表達方式,來表現亙古不變的主題“流浪”,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用現代性的方式,既可以保留著本初,也可以說是在表現當下。流浪,是用身體在行動的,確切的說,是用腳在走,用身體去感受。正如編導所說,我們不停的在行走,在得到也在失去。
整個舞段沒有分幕,沒有華麗的服飾、沒有喧賓奪主的舞美道具,編導沒有用這些來局限觀者們想象的空間。編導巧妙地運用了自然、宗教、生活中的聲音,來切換場景和渲染氛圍。用具有著蒙古族特色的馬頭琴、呼麥等音樂,將觀者帶到茫茫無邊的大草原上;用潺潺的流水聲將觀者帶到清澈的小溪邊;用地鐵聲、街道聲、電梯聲、開門聲、放鑰匙、拖鞋、倒水、喝水、嘆息等一系列的聲音,將觀者拉回到繁忙的城市生活中。通過聲音和音樂巧妙地進行場景的切換,雖然舞者一直在舞臺上,沒有道具布景的配合,但觀者的心早已跟隨舞者從荒蕪的沙漠來到潺潺流淌的溪水中,從梵音鳴唱的寺院回到車水馬龍的城市中。以音樂的變化進行場景的切換,在有限的舞臺上創造了無限的空間。
在舞者的身體動作中,融入中國民間舞的動作元素,最為明顯的是蒙古族語匯的運用。蒙古族以圓的身體形態為基礎,肩、臂動作的延伸舒展放大了動作的輻射范圍,提高了空間的占有率,使得五個人的舞蹈也能夠較好地利用整個舞臺空間。配合以現代舞軀干部位的收放舞動,將這些動作貫穿于呼吸之中。動作中行圓的流暢與頓挫的質感對比突出,給觀眾以視覺上的享受。動作編排與銜接有一種呼之欲出、傾瀉而下、暢快淋漓的快感。使觀者在感受舞者動作的同時亦能感受到延伸至指尖、趾尖,甚至于發絲的呼吸,仿佛自己的腳也深深的扎根于土壤中,每一寸肌膚都在接觸空氣,每個毛孔都在呼吸。在靜謐的氛圍中,跟隨著舞者的身體去流浪,去呼吸,去尋找真正的“自我”。
西方現代舞的起源根植于其自身的文化,表現的內容更多為體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者發現“自我”,現代舞在中國的發展除了去學習借鑒西方的動作體系之外,很少有作品能夠讓觀者看懂,從而引起共鳴、引發思考的。而《流浪》這部作品能夠使觀者在無限循環的時間里,透過對自我的觀察,關照“自我”,發現“自我”,從而能夠更深一步地去探討當下社會中所有人的“流浪”。
四、光與影的訴說
整場燈光沒有浮華絢麗的顏色變幻,以暖黃色的燈光為主體。在開場時,透過黃色的燈光和干冰,營造出了黃沙漫天、一望無盡的荒漠效果,仿佛五個流浪者置身于沙漠中,步履緩慢、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著,去追尋抑或是去遺忘……使觀者在寧靜的氛圍中,隨舞者繼續前行。隨后,舞者背向觀眾,向舞臺的后方踱步,舞臺正后方打出一束黃色的光,仿佛是日出或者落日的余暉,舞者向著無盡的遠方行走著,光直射在他的身上,描繪出一個鑲著金邊的孤獨的輪廓。以一束光拉長了整個舞臺的縱向空間,營造出了景深的效果。劇中以舞臺后方的幕布作剪影,將現實中的“我”與其余的“我”劃分開來,將現實中的“我”置于幕前的黑暗中,將其余四個“我”置于幕后, 以剪影的方式訴說著“我”心里的孤獨與寂寞。在全場燈光黑暗時,處于掙扎后迷失方向的“我”突然找到了一個盒子,它就像是一顆救命的稻草,盒子里是一本書,翻開書的那一刻,整本書都是明亮的,仿佛整個世界都被照亮,就像是迷失方向的“我”找到了歸家的方向。作品結束時,來自舞臺正后方的一束刺眼的黃色光柱直射向觀眾席,這種突如其來的視覺上的沖擊,直擊觀眾心靈,仿佛被置身于審訊燈下,有著喚醒并且撼動觀者平靜內心的效果。一方面暗示著作品的結束,仿佛又是一個嶄新的開始。以一束燈光來訴說的方式與觀者互動,用燈光連接舞臺與觀眾席,讓人浮想聯翩的同時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發觀者對于“自我”的思考。仿佛是在說:“我的故事講完了,那你呢?”
舞蹈的結尾是歡快的,舞者們換上了色彩鮮艷的都市服裝,在歡快的音樂下縱情舞蹈,彰顯出年輕的活力和積極向上的態度,因為一切的流浪都是為了能夠更好的去生活。每個人都有獨屬于自己的故事和經歷,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揣測編導的想法,此刻你眼睛看到的《流浪》就是屬于你心中的流浪。你的所見所想正是來自于你的內心和靈魂深處。正如你所看到的抬頭不一定是仰望,也許只是一次呼吸…… 你只需要跟隨著舞者的身體去流浪,從而去發現一個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