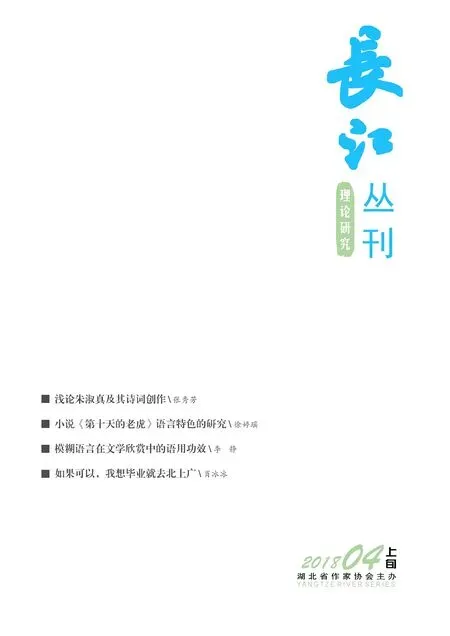試比較“洪水神話”在各民族傳統中的異同及內涵
■/
一、歷史概況
神話是文化的源頭,世界各民族的神話故事都是自己民族的一部史詩,是人類文明誕生、繁衍直至消亡的最好例證,在神話故事中有許多值得思考其現實價值的故事,而各民族雖分處不同的地域,擁有不同的膚色與血脈,有著不同的崇拜物和演進史,但他們仍有許多相似的故事或價值觀。而在世界各地流傳最廣的神話傳說便是洪水神話,其中最為著名當屬《圣經》中《創世紀》里的洪水神話以及西亞文化中和中華民族中的洪水神話。它們之中不僅體現了古代人民對那一時期歷史災難下巨大的生存環境變遷的認識,更展現了他們對那種苦難的深刻記憶和對自身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念的思考。
從目前有關洪水故事的記錄來看,地中海、印度、東南亞、大洋洲、美洲、非洲等均有關于洪水的神話傳說,而最早的文本可以追溯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的《吉爾伽美什》史詩,約在公元前2000年已經存在。這些洪水神話在故事框架上或多或少有著相似性,而能從中看出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中的變遷史,融和了自己對民族災難的記憶與情感,展現了自己獨特的精神傳承與信仰。
據目前學界學者分析,那場大洪水可能是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因為如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話,它們所描述的那場災難的發生的時期大致相同。而也有學者認為洪水神話是一個隱喻——既然每一個嬰兒都是從羊水這一“洪水”中誕生出來,洪水神話就是對人類誕生的若干突出細節所做的一種宇宙起源論式的心理投射①。然而不管那場洪水是否真實存在過,或僅為某一地區性的自然災害,它仍存留在我們古老的記憶中,值得我們去發掘其中的價值。
本文將從《圣經》(猶太民族)、西亞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洪水神話三個角度出發,探討洪水故事在各民族精神傳統中的內涵。
二、洪水故事在《圣經》之中
《圣經》中的洪水故事是從《創世紀》的第6章到第9章,學者們把這部分梳理出來兩段文本,一般意義上認為,這兩個文本都可以獨立成段,都擁有一個完整的故事體系,而且故事的梗概大致相同。如此兩個故事卻被《圣經》的作者捏合在一起,使其中既有相互印證的部分,又有相互矛盾的內容,這體現出了不同的作者對那段歷史的記憶是不同的,但殊途同歸,它們仍然能夠展現古代猶太人對那段歷史的看法以及猶太民族文化的精神傳統。
《創世紀》中對洪水的描寫大致可分為三部分,首先是產生洪水的原因以及神指導挪亞造方舟并帶上生物,然后是洪水的發生直至最后的消退,最后是洪水退去后的結局以及神與挪亞立約。
首先,在《圣經》中,洪水的成因是作者論述的重點,因為“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內心終日所思想的盡是惡”、“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了,地上滿了強暴”,所以神才會通過洪水去毀滅地上的一切。在這里,神具有絕對的權威,他創造了這世界和世上的生物,卻由于人的惡必須將這世界毀滅,神可以任用洪水來對這世界進行徹底的清洗,而在這種條件下,人和其他生物是沒有任何說話的余地的,而挪亞作為最后的生命的傳承者,與神只是立約的關系,這體現了《圣經》中以神為本的思想觀念和古代希伯來人對這場災難的神圣化解讀。
然后,在洪水發生的過程中,挪亞照神的吩咐行了,在大洪水的徹底清洗后,“上帝叫風吹地,水勢漸落”,舟中的生物才得以得救。此處含有救贖的觀念,人因信仰上帝、因按上帝的旨意行事而得救,正因上帝有著如此高的權威,人才能在信仰上帝中得到永生。
最后,上帝和地上的生命立約,“洪水不會再毀滅所有活物”,人和上帝是契約關系,惡行不再發生,洪水就不會再次出現。
在《圣經》的傳統中,上帝作為無所不能的存在,將自己所創造的一切在洪水中盡數毀滅,只留下少量的生物在挪亞方舟里。故事以“創世——問題——洪水——解決”這一思路展開,洪水消滅的不是人類的惡,而是舊的、沒有約束的秩序,因而在洪水后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人性中的惡要通過立法(新秩序)來約束,因而上帝與人立了約,形成了契約關系。這種“創造——毀滅——創建”即是《圣經》洪水故事中的核心思想。
三、洪水故事在西亞文化之中
西亞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吉爾伽美什》史詩對洪水也有一段記載:烏特那庇什廷住在舒魯帕克的一個蘆葦棚里。有天他聽到神對蘆葦棚喊叫,說是洪水將臨,叫他毀掉房子,建造“寬度必須和深度一致”的船,“將一切活物的物種運進船中”,后來果然六天六夜狂風暴雨、洪水滅世,烏特那庇什廷的船停在尼尼爾山頂。在第七天,他分別放出鴿子、燕子和烏鴉探查水情。得知水退后,他下船來向諸神獻祭。主神恩利爾來到船上,為烏特那庇什廷和他的妻子賜福,使他們得到了永生。
《吉爾伽美什》中的這段洪水故事的內容和《圣經》中的洪水故事極其相似,但是在《吉爾伽美什》中,在洪水退去后,烏特那庇什廷向諸神獻祭,而不是向一個神獻祭,這表明了在西亞地區的宗教觀念是多神崇拜,這與希伯來人的一神崇拜不同,而洪水后人神的祭拜后神賜福給人,這也與猶太傳統中的立約思想有著差別,人和神不是一種可以交流關系,人只能感念于神的恩賜,而神在發洪水之后也沒有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只是全憑自己的意志去發洪水再憑自己的意志去賜福給人,因而在《吉爾伽美什》的洪水神話中,缺少了故事的連續性與原因的完整性。
而在《圣經》與《吉爾伽美什》的洪水故事中,都有著共同的框架。首先人類得罪了神,神要通過洪水消滅一切,然后一個人得到了神的旨意,造出了逃生的大船并載上家人和其它生物,接著大雨下了很多天,于是放出不同的鳥去試探洪水是否退去,最后洪水過后人類重新生活。這表明古代西亞人和希伯來人擁有著相同的價值傾向,但不同的是西亞人以人為思考的中心,對烏特那庇什廷也是以類似于英雄人物的方向去描寫,而《圣經》則以神為中心,一切以上帝的意志為轉移,人所遭受的洪水是上帝的懲罰,是由自身的惡行引起的應受的懲罰。
四、中華民族的洪水神話
在中華民族傳統中,也有許多洪水神話,由于中國民族眾多,其所擁有的洪水神話類型也各有不同,比較出名的是以河南為中心的洪水后伏羲女媧兄妹以泥土造人的故事;云貴邊界的洪水后兄妹葫蘆生人的故事;云南四川邊境的洪水后僅剩的男子與天女結婚再造人類的故事;臺灣的洪水后神以遺民身體重新造人的故事。
然而在中華民族的洪水神話中,對于洪水成因的敘述并不多,“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②洪水的成因僅僅是因為兩神爭帝,神無法靠自己的力量讓洪水消失,而人也不是因為自己的錯誤被神懲罰,在這種情況下看來,神與人的關系是比較淡薄的,沒有相互的交流也沒有什么相關性。
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甚至沒有神的出現。鯀和禹沒有借助神的力量,只是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來治理水患,這是一種對人性的高揚,關注點在于中華民族在長期的艱苦奮斗中的不屈精神。大禹作為博愛、不屈、頑強精神的代表,擁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中,不乏這樣的歌頌英雄主義人物的故事,他們通過自己的智慧與不屈的精神品質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奇跡,而在這一過程中很少甚至沒有神的參與。而這種對人性中的善的弘揚正是中國儒家“性本善”觀念的體現,區別于《圣經》中“人性惡”的觀點,中國的神話中很少有展現罪與罰的觀點的故事,大多是對英雄人物的謳歌。
五、結語
雖然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中都曾出現洪水神話,但它們所展現的文化傳統和精神內涵是不同的。這些洪水故事大致可分為三部分:洪水的成因、解決辦法和解決后的世界。在西方的洪水故事中,尤其是《圣經》中的洪水,作者更側重神性的彰顯,洪水的成因是人的惡,上帝通過發洪水來對這世界進行徹底的清洗和毀滅,而洪水退去后,就是以人神立約的方式使一個新的秩序的誕生。在西亞文化中,洪水的產生則是因為神對人的行為惱火而意圖消滅人類,而這時其他的神出來幫助人,當洪水退去,人便獻祭神,神也賜福給他,但人神之間并沒有更多的聯系,也沒有對新世界的重塑。在中華文化中,洪水依然是神引起的,卻不是神刻意為之的,人與神之間更沒有交流,神不具備消滅洪水的辦法,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品質來克服一切困難治理洪水,這體現了中國思想中的人本主義和人文關懷,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觀點,中國自古以來即對于鬼神觀念淡薄,因而在中華民族的這場大洪水中幾乎沒有對神的記憶。
各民族文化和歷史傳承的不同導致了對大洪水不同的記憶,但這些帶著民族記憶的神話故事卻有著深刻的內涵與價值。
注釋:
①[美]阿蘭·鄧迪斯.洪水神話[M].陳建憲,等,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②劉安《淮南子·天文訓》。
參考文獻:
[1]阿蘭·鄧迪斯.洪水神話[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2]吉爾伽美什[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
[3]全群艷.比較視野中的中國洪水神話[J].社會科學家,2010(5).
[4]李景琦.從洪水神話看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異[J].天津大學學報,2013,15(2).
[5]武保勤,傅廣生.從中西方洪水神話看中西方價值觀差異[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33(4).
[6]張亞輝.大洪水催生人類社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6-12.
[7]陳建憲.多維視野中的西方洪水神話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6,45(2).
[8]徐露.鯀禹治水神話和諾亞方舟神話的同異比較[J].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2,28(6).
[9]陳建憲.洪水神話:神話學皇冠上的明珠——全球洪水神話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J].長江大學學報,2006,29(2).
[10]裴浩星,安貞慧.洪水神話的世界傳承與民族特性研究[J].東北師大學報,2012(5).
[11]向柏松.洪水神話的原型與建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25(3).
[12]劉瀲.美索不達米亞洪水神話——版本問題與文本探析[J].民間文化論壇,2016(5).
[13]鐘巧玲.試論中國洪水神話[J].新世紀論叢,2006(3).
[14]王三義.試析洪水神話的世界性及其認識價值[J].遼寧大學學報,2006,34(1).
[15]黃文英.中外洪水神話的母題及其變異[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