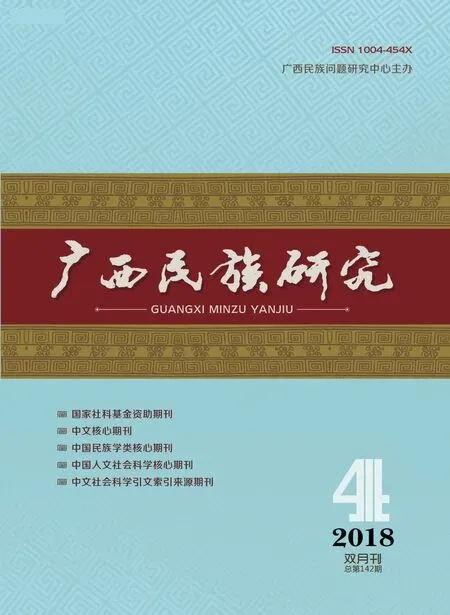房族組織、秩序生產與鄉村治理法治化*
陳寒非
一、問題及進路
鄉村是國家治理體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單元,國家治理的重心在基層社會治理,而基層社會治理的關鍵又在于鄉村治理。鄉村治理主體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鄉村治理體系的根本,大體可分為內部型主體、外部型主體以及內—外聯合型主體三種類型。其中,宗族是鄉土社會傳統組織,是鄉村治理中不容忽視的內部型主體。
早在20世紀30年代,林耀華、費孝通、陳禮頌等學者就已經開始關注宗族問題,提出了“宗族鄉村”“家族社群”等理論范式并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內學術界關于農村宗族問題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三個議題展開:第一,農村宗族復興及其原因研究。關于農村宗族復興原因大體形成了“功能需求論”與“深層結構論”兩種解釋模式。王滬寧較早關注宗族復興問題,認為宗族復興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對宗族功能的需求;[1]231—239唐軍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上透視家族復興的社會背景條件,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村民委員會的設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為家族復興提供了需求、空間、機遇和資源”[2];王銘銘認為鄉村宗族復興與民間儀式復興的原因一致,都是“傳統的再造”,即“民間再創造社區認同和區域聯系的行為”[3]154;郭于華認為宗族復興的原因在于具有生物及社會雙重屬性的“親緣關系”的內在驅動,構成鄉土社會“人情關系網的基礎和模本”[4]。第二,宗族組織類型及其轉型研究。宗族組織類型與其結構功能密切相關,一些學者在類型化的基礎上探討現代轉型問題。莊孔韶將農村血緣性親屬團體分為宗族、房及家族等不同形態,認為它們“均是親屬關系生物性與人倫哲學及社會秩序整合的結果”[5]4;肖唐鏢將“宗族”概念分為“實體的宗族”與“文化的宗族”,前者主要是指宗族組織、制度等,后者主要是指觀念意義上的宗族,即宗族意識、觀念等;[6]8石奕龍等人區分為“理念性宗族”和“實踐性宗族”[7]。第三,宗族的村治功能研究。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主要強調宗族對鄉村治理的負面作用,2000年以后逐漸認可宗族對鄉村治理的積極作用。賀雪峰認為在宗族意識比較強的村莊,村民會選本族人當村干部,因為“強烈的宗族意識使同族的人成為自己的人”[8]102—103,便于組織和管理。肖唐鏢系統研究了村治中的宗族力量,認為宗族“已內化為鄉村治理規則與邏輯的重要元素”,在當前農民組織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實際上有助于基層民主政治發展。[9]22—23
海外漢學關于中國宗族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主要涉及議題包括宗族的概念、組織結構、特點、類型以及宗族相關的婚姻家庭制度等,調查區域主要以華南、東南為主。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考察了廣東地區鳳凰村的家族制度,認為“家族主義”(Familism)是鄉村社會核心的社會制度,進而概括出“宗教的家族”“自然的家族”“經濟的家族”以及“血緣的家族”四種類型;[10]90—94胡先縉(Hsien Chin Hu)分析了中國宗族、房族及家庭之間的內在關聯,對宗族祭祀、祖先崇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強調宗族對于鄉村社會結構運行的積極意義;[11]科大衛(David Faure)、劉志偉考察了明清時期華南地區宗族的發展過程,超越于一般的“血緣群體”或“親屬組織”研究視角,認為“宗族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意識形態,也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關系”[12],更是地方與王朝中央之間的正統紐帶[13]11—18;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建構出中國宗族研究的經典范式——“世系群”(lineage)分析模型,認為中國宗族是父系實體性組織,屬世系群單系親族組織,族譜是明確世系群成員范圍的基本制度,族產則是維系宗族關系的紐帶;[14]161—178在弗里德曼研究的基礎上,又有貝克爾(Hugh D.R.Baker)、波特夫婦(Sulamith Heins Potter&Jack M.Potter)、帕斯特耐克(Burton Pasternak)、孔邁隆(Myron L.Cohen)、華如璧(Rubie S.Watson)、華琛(James L.Watson)等人對華南、香港、臺灣等地農村宗族問題展開了研究。
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農村宗族的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建構出一些經典的理論范式,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已有研究大多關注漢族宗族,較少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族問題;所選區域多為東南、華南地區,較少關注西南地區;研究的內容多為宗族組織結構、世系群類型、內部分化、復興原因、祭祀儀式等方面,較少關注宗族在鄉村治理中的運行及秩序維持功能;所涉學科多為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法學學科關注較少。鑒于此,本文擬從法律人類學角度探討宗族治理規則及其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進而討論鄉村治理法治化過程中如何合理嵌入宗族等自組織資源問題,旨在通過多元主體合作共治路徑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
筆者所在研究團隊曾于2016年7月22—28日、10月1—7日、2017年8月23—31日進駐黔東南地區錦屏縣文斗、魁膽、黃門、平山等村寨調查村規民約問題,調查過程中收集到“清明會”“桃園節”“阿瓦節”“嘗新節”等節慶活動的組織資料,發現各項活動中均有“房族”身影出現,房族是當地各項公共活動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力量。不僅村寨內部,房族也會跨村參加并支持其他村寨的活動。這一現象引起了筆者濃厚的興趣。筆者深入田野調查并收集了平山、魁膽等侗族村寨的房族資料(族規及案例),這將是本文展開研究的資料基礎。
二、屋山頭:房族組織結構及其特點
平山村地處貴州省錦屏縣西北部九寨地區侗鄉腹地,①“九寨”是貴州錦屏縣西北部彥洞、瑤白、黃門、石引、高壩、皮所、平秋、魁膽以及小江九個比較大的村寨以及一些小村寨的統稱。侗鄉九寨地處清水江與小江之間較為平緩的高地,東起各龍,西起救王,各村寨像珍珠一樣點綴于高地平緩壩子之中。現屬平秋鎮,是該鎮第二大村。全村512戶2132人,其中99.3%為侗族,轄14個村民小組。全村幅員面積25平方公里,為全鎮第一。在與當地人交談過程中,“房族”是出現頻率比較高的詞匯(如“某某房族”“我們房族”),甚至見于官方正式文件表述。那么,當地人說的“房族”是什么意思?其組織結構是怎樣的?
漢人宗族話語體系中,“房”是宗族內部分裂后的次級組織,是宗族的下位概念。漢人宗族組織結構從大到小大致可列為“宗族—房—分支—戶—家”。“房族”在侗語中有多種表達方式。湘西南侗語“wangc”即“房族”之謂,表示“‘聚族而居’即‘聚房而居’”[15]。南侗同一曾祖的“房族”稱“卜(補)拉”(bux ladx),意為“父與子”[16]。北侗九寨社區“最小的社會基本單位是家庭;比家庭大的社會單位是宗族,九寨人稱之為屋山頭;比宗族大的社會單位是款組織”[17]60,“族”繞鼓樓而居,形成較大的群落。平山位于北侗九寨,亦用“屋山頭”表達“房族”“宗族”,“屋山頭”意指某個血緣群體聚居于一個平緩山坡。相較而言,侗族“房族”比漢人宗族中的“房族”要復雜,內涵相對較為模糊。“屋山頭”是聯系家庭的組織,其組織形式既包括了基于血緣關系的同宗同姓,也包括了小姓之間通過盟誓結拜而成,還包括同一姓氏內部派系之間聯合而成。因此屋山頭組織的范圍甚廣、伸縮性很大,可能含有較近的血緣關系,也包括已出五服的同姓成員,還有可能包括非血緣關系的成員。
平山村有劉、吳、陸、龍、陳、任、徐、邵、傅、全10個姓氏,陸、劉姓人口較多。[18]225經過10多年發展,陸、劉兩姓仍然是村中人口較多的姓氏,房族規模也相對較大。劉姓有3支房族,分別為L1、L2、L3;陸姓有3支房族,分別為M1、M2、M3。劉姓“哦先恩”房族(L1) 是3支房族中較大的一支,具體包括72個家庭,這72個家庭又組合為40戶,一戶又由1—4個家庭組合而成,是否分家是“戶”設立的依據,每一戶又設有戶長。“哦先恩”房族成員主要集中在平山村二組、三組,另在十一組、十二組也有一些房族成員。房族成員并不都是劉姓,個別也有全、陸等其他姓氏。陸姓“高步房族”屬于3支房族中較大的一支,共計20戶,包括52個家庭,房族成員主要集中在平山村四組、五組,也有一些房族居住在鄰村。
值得注意的是,劉姓3支房族并不都供奉同一先祖,相互之間彼此獨立,各修有自己的族譜,這與漢人宗族中“房”的區別比較大(同一先祖之下的次級組織)。換言之,劉姓“哦先恩”房族(L1)與L2、L3之間盡管姓氏相同,但并不是同一先祖之下發展出的3個小宗。根據L1房族族譜記載,其有據可查的先祖為湖南靖州邵越公,邵越公的兩個兒子分別為鈺湘公、鈺明公,鈺明公于嘉靖四年(1525年)遷往黎平府天甫地區,其后人又于乾隆四年(1739年)遷到錦屏縣銅鼓地區。同治八年(1869年),L1房族與固本、大同兩地的劉姓聯合修譜,固本、大同兩地劉姓族人認為其先祖來自于銅鼓,于是L1就作為先祖邵越公下的第一支房族,固本的劉姓后人為第二支房族,大同的劉姓后人為第三支房族。由此可見,L1與該村L2、L3房族之間本無宗族淵源,只是后來出于現實需要(也有可能是基于“天下劉姓為一家”的觀念)才于20世紀40年代進行聯合修譜,L2、L3續上 L1族譜,但L2、L3族譜上仍然保留著各自的先祖。①張銀鋒考察錦屏縣魁膽村王姓房族時也有類似發現,當地王姓兩支房族主動將自己族譜接續在別人上面,實現房族之間的“聯宗”。這種情況在北侗九寨房族形成過程中較為常見。參見張銀鋒《“屋山頭”的文化嬗變:對清水江流域一個侗族村落的歷史人類學考察》刊于《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1年第4期.更為復雜的是,“房族”同時還指稱原有房族(宗族)分裂后的分支,如L1分裂出L1-1和L1-2兩支(分別處于不同村寨),這兩支也可相互稱為房族,但有共同的先祖。陸姓3支房族的情況較為類似。筆者在錦屏縣彥洞鄉瑤白村調查時也有類似發現。瑤白有龍、滾、楊、范、龔、耿、彭、宋、萬、胡10姓,滾、楊姓人口較多。瑤白目前共有悶銀龍、時公、三包卷、奧包巖、海龍姣、銅錢網、富寧親、鏡臺滿、三解丘、銅錢關、寧富你催、保公、漢公13支房族,每支房族之下的姓氏都比較雜亂,基本上每支房族存在兩個以上的姓氏,沒有單獨由一個姓氏組成的房族。由于歷史上楊、王姓曾改為滾姓,王姓后來又復為耿姓,龔姓原為漢族,與侗族雜居后成為侗族。[18]236所以,楊、王、耿、龔幾個姓氏與滾姓都是接續族譜之后的房族分支。黃門村以王姓人口為主,該村王姓分為上、中、下3支,3支房族各自有其宗祖,互相可以通婚。①有些房族的產生甚至基于某個關于先祖的傳說,將本無聯系的同姓房族接續在一起。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北侗房族組織結構存在三個特點:首先,房族結構較為簡單。平山侗寨房族并不同于漢人宗族世系中的次級組織“房”,當地房族組織是“房族—戶—家庭”三級結構,而漢人宗族的“房”存在于“宗族—房—分支—戶—家庭”五級結構之中。侗族房族范圍可大可小,既可以大到類同于宗族,又可小到僅有十幾戶的房族世系分支,但在實踐中多以“房族—戶—家庭”三級結構為主導,一般房族之上并無宗族。其次,房族的姓氏構成相對較為靈活復雜,既包括“同姓不同宗”情況,也存在“同宗不同姓”現象,同姓之間可以通婚,不同姓氏也可以是同一房族,房族與姓氏之間是動態調整關系,一個姓氏群體可以根據某個傳說或現實需求接續上本無血緣關聯的房族族譜。最后,房族組織結構有一定延伸性,包括房族發展演變過程中分裂出的小宗,房族也可以向村寨之外同姓族群拓展,吸收更多的房族成員。侗族房族組織結構呈現如上特點與其歷史發展及現實需求有密切關系。房族采用“三級結構”可以避免鋪陳過寬、范圍過大,本房的人長期聚居、情感相通、利益相連,方便組織活動和有效管理,這也是侗族傳統組織與漢人宗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果。房族姓氏構成靈活復雜的直接原因在于改姓、續譜等方式的運用,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宗的同姓以及其他小姓氏為了更好地融入當地社區,獲得某種宗法血緣上的正當性。符號人類學(Symbolic anthropology)認為,符號本身承載著一定的文化意義和功能。格爾茲對巴厘島斗雞儀式的研究表明,雄雞(當地人稱為“Sabung”)一詞在當地有著豐富的含義[19]491,因為雄雞是巴厘島男性的象征表達與放大,是自戀的男性自我的動物性表達。通過改姓、續譜等方式獲得某個姓氏的做法同樣是出于對姓氏符號背后代表的權力體系和文化意義的認可,意味著族群的文化認同、歸屬及區分,以便本姓氏在當地的生存和發展。“房族”概念還包括分裂之后的小宗,這種現象如同漢人宗族中的“房”支系的分離,盡管稱之為“房族”,但是更多地是代表原有房族之下的“次級組織”。對于次級組織統稱為房族,或許能夠更好地團結族內成員,防止房族頻繁分裂削弱宗族力量。綜合來看,平山侗寨房族組織結構特點都是在房族日常治理實踐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由房族的治理功能決定,有很強的實踐意義。
三、房族之治與鄉村社會秩序生產
黔東南錦屏地區苗侗村寨中普遍存在房族組織,房族已經深入平山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植根于當地文化傳統,得到村民的普遍認可,是鄉村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那么,房族如何參與鄉村治理進而生產出何種鄉村社會秩序?
房族參與鄉村治理的方式首先是協助村務。筆者觀察到,近兩年平山村組織的桃園文化節、春醮會等大型活動都有房族參與,“村兩委”在活動策劃、募捐錢款、活動分工時基本上都召集各個房族“房長”(相當于漢人宗族的“族長”)進行商議,由房長向房族成員進行傳達和動員。村里公共事務需要通過房族協助完成,而不完全是村民小組。在黃門村的嘗新節、瑤白的擺古節也都有房族協助和參與。除了協助村務之外,房族也積極參與鄉村公益事業。為了給村民提供納涼聚敘之便,平山“哦先恩”房族主動組織修建“和興亭”。①《和興亭(序)》,平山村村民委員會提供,資料編號:20170823002。和興涼亭動工之際,有眾多仁人志士自愿出工捐款,不足之數由房族成員補齊。亭子名稱“和興亭”也是經與房族成員征求意見后確定(如通過“考哦家人”房族微信群征求意見)。建亭的整個過程沒有“村兩委”參與,全部由房族自發組織。
房族通過制定族規約束引導房族成員,這是一種較為常見、有效且比較重要的方式。《哦先恩房族族規》共計16條,內容涵蓋較廣,規定得非常細致,涉及移風易俗、清明會掃墓、村集體活動人員安排、大小工雇傭以及山林土地轉讓等方面。②《哦先恩房族族規》(2017年1月27日全房族各戶在家人員議定),資料編號:20170827003。為了移風易俗、遏制鋪張之風,族規第一條對舉辦酒席、送禮行為進行了規定;族規第二條至第六條是關于房族成員之間紅白事互助方面的規定;族規第七條、第八條是關于清明會掃墓的安排;由于村集體活動的分派一般以房族為單位,因此族規第九條規定村集體活動費用由各戶均擔;族規第十條是關于房族成員遵紀守法、遵守規章制度、愛護集體等方面的概括式規定,尤其是關于矛盾糾紛解決方面的規定;族規第十一條規定房族中不許同一天辦兩筆喜事;族規十二條是關于族內去世老人輪流安排守夜的規定;族規第十三條、十四條是關于族內大小工雇傭和山林土地轉讓方面的規定。陸姓《高步房族族規》相對較為簡單(共計六條),與《哦先恩房族》族規類似,內容大致包括紅白喜事互助、清明會組織、村集體活動安排、糾紛解決以及紅白事舉辦時間沖突的處理等方面。①《高步房族族規》(2016年10月31日全房族集中議定),資料編號:20170827004。與《哦先恩房族族規》不同的是,《高步房族族規》對違反族規的行為明確規定了處罰措施(處罰人民幣1000元)。
房族族規調整的范圍是比較廣泛的,主要涉及互助合作關系、山林土地轉讓、村集體活動承擔以及糾紛解決等方面。糾紛解決是比較重要的村莊公共性事務,也是房族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方式。實踐中房族可以解決房族內部成員之間、房族與房族之間的糾紛,其解決糾紛的方式以調解為主。筆者在調查過程中接觸到一起房族調解族內成員糾紛的典型案例②根據房族成員陸正華的訪談錄音整理,資料編號:20170827LXB001。調解協議可參見《家庭責任山責任田調解紀事》,資料編號:20170827005。,該案中責任山林、田地糾紛延續了30多年,由于關系錯綜復雜,村里面也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好,最終房族介入才得以解決。房族可以利用基于血緣產生的信任關系(本案當事人是同父異母兄弟,糾紛屬于家事,先在房族內部解決),以房族傳統權威為基礎,秉承公平公正的方式調解,其結果更能讓當事人信服和接受。
房族主要通過協助村務、主導公益、族規引導和糾紛解決四種方式參與鄉村治理。從房族參與村治過程可以看出,房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鄉村社會秩序生產。房族生產鄉村社會秩序的基礎是自治,生產出的秩序是一種內生性秩序。如同傳統社會宗族治理,房族首先是傳統鄉村社會組織,基于血緣、地緣、情感認同以及共同利益等進行自我管理,一直是傳統鄉村社會中重要的治理力量。房族自治規范(族規)完全產生于民治系統,是典型的非正式規范。法律人類學從法律多元的角度討論非正式規范,將其視為特定共同體內部的“地方性知識”[20]278—295,或稱“非官方法”[21]190。非正式規范經由社會互動和實踐演化而生,具有自生自發性與內在性,基本上沒有國家權力的介入,主要包括習慣規約等自治性規范形式。平山侗寨的房族族規就是典型的非正式規范。
盡管如此,房族生產秩序的過程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式的,這主要體現在房族與村級“半行政化”自治組織、國家正式權力之間的互動。房族在運行過程中一般會將村兩委議定的相關政策、建議等融入房族規約之中。例如,《哦先恩房族族規》第一條就是關于“移風易俗”的,這主要是根據“村兩委”移風易俗會議精神修改議定,而“村兩委”又是根據基層黨政機關部門的文件要求推行移風易俗。為了響應村里建設文明村寨的要求,達到“革陋習,樹新風,厲行節儉,共建文明”的目的,哦先恩房族根據村兩委的建議,專門向房族親友發布公告,勸告大家在吊唁期間“不要燃放煙花爆竹、不要送花圈”。③《“哦先恩”房族敬告親友戚》(2015年8月4日),資料編號:20170827006。與此同時,房族也會與國家正式權力進行互動,號召房族成員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例如,哦先恩房族族規第十條明確要求房族成員“遵紀守法、遵守規章制度、愛護國家、愛護集體、愛護村寨”,要求成員之間和諧相處,不要產生糾紛。在山林、田地轉讓時不允許強行買賣,同等價錢下本房族成員可以優先購買,由買賣雙方意思自治。換言之,房族族規雖然主要體現出自治性,但是也會考慮到法律法規及“村兩委”決策,在與村民自治制度、國家法律互動、調適過程中生產出一種新型的內生性秩序。
四、鄉村治理法治化中的自組織資源
鄉村治理法治化是當前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關鍵,是解決法治社會建設“最后一公里”問題的重心,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更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中“治理有效”目標的主要方向。鄉村治理法治化區別于傳統的治理方式和理念,突出國家法律法規在鄉村治理規范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強調將現代法治觀念、思維、規則等融入鄉村治理全過程。對于鄉村社會內部自生規則而言,鄉村治理法治化依靠的法律制度屬于典型的“外來規則”,在向鄉土社會強行輸入過程中很有可能會造成“語言混亂”(confusion of tongues)問題。整體性進路需從日常生活實踐入手理解草根社會如何融貫“外來規則”,進而消除“語言混亂”問題。鄉村自組織則是鄉土草根社會融貫“外來規則”的重要力量,鄉村治理法治化需要探索“嵌入”自組織資源。
組織社會學認為,社會組織是由相互關聯的眾多個體有機結合組成的協作系統,組織化過程就是事物有序化的過程和結構方式。組織化過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自身力量組織實現有序化,另一種則是通過外部力量干預走向有序化,前者稱為自組織(self-organize),后者稱為他組織。[22]9“自組織是一群人基于自愿的原則主動地結合在一起,它有以下的特性:(1)一群人基于關系與信任而自愿地結合在一起。(2)結合的群體產生集體行動的需要。(3)為了管理集體行動而自定規則、自我管理。”[23]自組織是介于市場與層級之間的第三種治理方式,個體基于意思自治自愿組合成小團體,小團體形成后會明確成員身份,團體制定內部規范以確保團體目標達成。根據自組織理論,本文所討論的房族就是典型的自組織。首先,房族基于血緣、地緣及共同利益等紐帶自發而生,房族內部組織結構清晰有序(三級結構),具有共同的價值或身份認同,自主制定房族規約進行管理,集體行動動員快捷有序。除了房族之外,鄉村社會還有很多自組織(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會組織)。平山侗寨于2011年10月10日成立“互助會”,搭建起家鄉和外鄉務工人員的橋梁,制定了“興村、交流、互助、共進,團結友愛、互助互惠、聯系鄉情、共謀發展”的宗旨。“互助會”在募捐、助學、幫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①《鄉鄰互助助人助己——記錦屏縣平秋鎮平山村互助會》,平山村民委員會提供,資料編號:20170827008。同縣茅坪鎮上寨村的“長生會”也是當地村民自發形成的互助組織。“長生會”組織于1982年恢復,兩年一屆,至今已經到17屆。“長生會”的宗旨是:“一戶有難全會相幫,‘老有所終,安息無憂’,做到破舊立新,移風易俗,增強團結,互相幫助;協助孝家,以儉辦喪事,全心全意圓滿地把亡者送葬登山安息,做到陰安陽樂。”②《茅坪上寨長生會會章》(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會委修改通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執行),資料編號:20160930MP3796。當會員家中有人去世,長生會就會組織其他會員幫助孝家辦理喪事。鄉村自組織的形成過程基本上都是由村民根據需要自發成立,圍繞自組織行動目標制定相關規范制度,依托這些規章制度進行自我管理。
自組織運行需要構建制度規范及實施機制,自組織運行的過程就是從事社會治理的過程,因此自組織在鄉村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鄉村自組織對于鄉村治理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鄉村自組織協助村務,有效彌補村民委員會、鄉鎮政府在公共職能行使上的不足。如平山房族協助村里組織、舉辦大型節慶活動,積極參與村里公益性活動,完成村里下派的各項任務,配合縣里移風易俗、清潔風暴等行動。
第二,鄉村自組織制定自治理規范,約束成員行為,生產鄉村社會秩序。鄉村自組織一般都會根據需要制定切實可行的自治理規則。這些自治理規則不同于國家法律和村規民約(狹義),基本上都由具有特定聯系紐帶(如血緣、利益等)的小團體根據實際需要自行制定,調整的事項非常具體,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施效果往往也比較好。所制定的制度規范及運行策略能夠比較好地被共同體成員接受遵守,因此在鄉村社會生產出一種內生性秩序。
第三,鄉村自組織的秩序生產具有一定開放性,與外部力量之間保持一定的互動關系,可以消除鄉村內外治理力量之間的緊張關系。如平山房族族規中積極引入國家法律法規、村兩委相關決議等,體現出與外部力量積極互動且保持一致的努力。可見,鄉村自組織治理不同于政府的層級制治理,也不同于市場的契約式治理,而是基于自治規則的自治理。鄉村自組織踐行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相對而言比較符合村民的實際需求,基本上能夠實現良性運行。
鄉村自組織的秩序生產功能及自治理特點,在特定條件下極有可能會成為鄉村治理的主導力量,因此在鄉村治理法治化過程中應該合理“嵌入”鄉村自組織資源。更重要的是,鄉村自組織本身并非與國家權力主導推行的法治為敵,而是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存在相互銜接容納的空間及可能性。國家權力如果不重視鄉村自組織資源,合理處理與鄉村自組織之間的關系,很有可能增加鄉村治理法治化過程中的巨大成本,法治難以在鄉村社會扎根生長。如果重視并合理嵌入鄉村自組織資源,鄉村治理法治化很有可能會節約成本、事半功倍。筆者認為,當前鄉村治理法治化“嵌入”自組織資源的方式有三種:
第一,制度保障。鄉村自組織的地位需要進一步明確,宜界定為“法治之下的完全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為“半行政化組織”),應從制度設計層面緩解自治與法治之間的緊張關系。只有明確其法律地位,將其納入到現行鄉村治理體制之中(如人民調解、基層群眾自治等),才能更好地發揮其鄉村治理功能。
第二,規制引導。鄉村自組織具有自治性,容易脫離法治軌道,因而需要進行規制引導。平山高步房族族規對違反族規的成員“處罰人民幣壹仟圓(1000元)”,再如紅白理事會章程對于違反移風易俗規定的行為同樣也是處以罰款,這些規定的合法性顯然值得討論。鄉村自組織制定的規約也有可能與村規民約相沖突。例如,平山村移風易俗管理制度第一條規定:“除新屋上梁(或兄弟同建一幢房屋喬遷)、男婚女嫁、高考升學二本以上、老人百年大事允許辦酒,辦酒桌數控制在30桌以下,辦菜碟數在12碟以下。其余的一律不準辦酒”。①貴州錦屏《平山村移風易俗管理制度》(2015年3月14日),資料編號010172。但是“哦先恩”房族族規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變通規定(見前引族規第一條),允許辦酒,只是限制成員送禮。可見,鄉村自組織規則的確可能與國家法律、村規民約之間存在沖突,而消除這種沖突的有效方式需要基層黨政部門和村兩委通過建議的方式予以規制引導,如果引導超出必要限度則會破壞鄉村自組織的自治性。
第三,融貫規則。鄉村治理法治化過程中“嵌入”鄉村自組織資源,還需要注意不同治理規則之間的吸納融貫。鄉村自組織盡管遵循自治方式,但是并不完全是封閉的,會在一定程度上融貫外部規則,吸收、援引國家法律等正式規則及村規民約等準正式規則,為自身運行尋求合法性基礎。如前引房族族規中對國家法律、村兩委決議的概括性援引。與此同時,國家法律政策、村規民約等也應尊重鄉村自組織的治理規則及運行規律,在實施過程中盡可能將自組織規則融貫其中,尊重鄉村自組織運行的基本規律,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依托鄉村自組織的法治化才能真正落地。實踐表明,國家法律政策的貫徹執行需要鄉村自組織與之對接,通過借助鄉村自組織內部規約、輿論、面子等自治理機制實現“正式權力的非正式行使[24]42。
當前鄉村治理法治化的一般化進路是國家單向度的自上而下簡約推進,這種推進進路的效果并不理想,實踐中出現了諸多問題。隨著國家治理能力與鄉村社會性質的轉變,鄉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徑創新日漸凸顯,合理“嵌入”鄉村社會中的自組織資源可以有力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鄉村自組織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對接國家法律政策。此舉不僅增強了鄉村自組織的權威性,而且也將國家法治精神引入鄉村社會深處。
五、結語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鄉村實現“治理有效”的基本方向是鄉村治理法治化,而鄉村治理法治化亦需充分發揮“主體”的作用。通過在黔東南平山侗寨調查,本文試圖得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平山侗寨房族組織結構相對簡單,但是內涵較為復雜,具有明顯的治理功能。當地房族在鄉村治理中頻繁出現,是一類頗為重要的治理主體。平山侗寨房族的組織結構一般是三級結構,即“房族—戶—家庭”,相較漢人宗族的“房”要簡單。但是,侗族的“房族”內涵比較豐富,既包括類似于漢人宗族中的房支,同時也指涉類似于漢人宗族的組織。在房族范圍、姓氏組成、血緣淵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如通過改姓、續譜等方式向外拓展),而這種靈活性恰恰形成于侗族日常治理實踐,具有強化和實現房族治理功能的目的。
第二,房族參與鄉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鄉村社會的秩序生產。房族主要通過協助村務、主導公益、族規引導和糾紛解決四種方式參與鄉村治理,其中又以后兩種方式為主。房族治村的方式是自治,即通過房族成員自治生產出一種內生性秩序。但是,這種內生性秩序并非傳統宗族組織所生產的“原生秩序”,而是融入一些外部規則(如國家法律、政策、村規民約)之后的新型內生秩序。因此,房族主導下的鄉村社會秩序生產并不是封閉式的,而是開發式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嵌入”國家政權、村級政權等外部力量。在房族賴以存在的傳統權威日漸衰退的今天,選擇性地“嵌入”包括國家正式權力在內的外部力量,也可以為房族治理提供新的權威基礎,有利于其秩序生產。
第三,合理嵌入自組織資源是鄉村治理法治化推進的關鍵。鄉村自組織的本質特征就在于,村民根據需要自發成立,圍繞自組織行動目標制定相關規范制度,依托這些規章制度進行自我管理。鄉村社會中存在很多自組織,這些自組織多以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組織為主,除了本文討論的房族之外還包括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長生會、互助會等鄉村自治性組織。當前鄉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就在于,由國家自上而下單向度推進的法治在鄉村治理實踐中遭遇到“語言混亂”,受制于多種結構性因素,導致其推行成本很高。解決鄉村治理法治化困境的有效途徑是嵌入鄉村自組織資源,具體包括制度保障、規制引導以及融貫規則三個方面。在鄉村治理法治化過程中“嵌入”自組織資源不僅有利于國家法律政策在基層社會的推行貫徹,而且還有利于鄉村自組織在法治化軌道下運行。因此,“嵌入”是國家政權、村級政權以及自組織三者之間互動調和的結果。
反思以往鄉村治理法治化進路,本文認為,鄉村治理法治化不能脫離特定的時空條件,需要依靠鄉村社會固有資源,而鄉村自組織正是當前鄉村社會最為重要的自治資源,它們完全產生于民治系統。由于國家正式權力在基層社會的有效運行必須依靠鄉村自組織生產的非正式運行系統,因此在鄉村治理法治化的過程中應注重運用自組織資源,這正是實現鄉村治理法治化乃至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