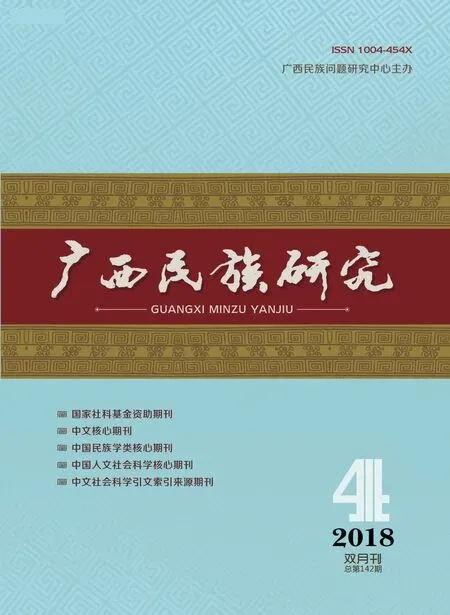村寨外交與“功能性村寨”生成
——以都柳江流域苗寨為例
盧 曉
村落不只是人們聚居、生活、繁衍的“空間單元”,更是一個“社會單元”,能稱之為“村落”的則必定是一個完善的社會組織。國內外學術界對于村落的研究,多將其放在“村落共同體”的視域中考察,然而這一外來概念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社會學的“共同體”概念最早源自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Fernand Tonnes) 的《共同體與社會》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在以滕尼斯為代表的德語圈中,“共同體”側重于指代一種與現代都市生活相反的傳統鄉村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主要以情感和精神為紐帶將人們聯結成“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的共同體。[1]53-67滕尼斯的“共同體”概念引起英美國家社會學對于“community”的關注。“community”內涵不斷延展豐富,美國社會學家G.A.希勒里(G.A.Hillery) 收集了有關“社區”的94個定義,概括三個基本的共同要素:地域、共同紐帶和社會互動。[2]27-29具有地理邊界的地域共同體則是英美圈對于“共同體”理解的重點。受帕克(Robert Ezra Park) 的“Community is not Society”思想影響,學者黃兆臨將“community”譯作“社區”,并經吳文藻、費孝通等人的采用、提倡而逐漸流行。[3]78中國早期的“社區”研究因“微型社區”研究方法的提倡而多集中于對村落的整體研究。中國學者對于“村落共同體”關注則直接源于日本學者平野一戒能“村落共同體”的論戰。[4]在日本學界,對于德語“Gemeinschaft”和英語“Community”有不同翻譯,將Gemeinschaft翻譯為“共同態”,Community譯為“共同體”。“共同態”(或者共同性)指的是特定的人際關系的樣態,而“共同體”是指以其樣態為基礎的集團或結合體。[5]226-235也就是說以“共同態”表征精神的共同體,而用“共同體”辨識具體區域范圍內的群體結合方式。
村落“共同體”概念幾經周折從德語、英語、日語圈進入中國,“共同體”的學術傳統,以及不同語境下的漫長對接,使得我國對于“村落共同體”的研究只關注村寨的內部聯系,而忽視了外部社會對村寨擔負社會責任和義務能力的要求。都柳江流域村寨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村寨共同體特性是在區域社會內與他寨的交往互動中形塑和被檢測。這種由外而內形塑、檢測村寨獨立的方式,已經超越了傳統“村落共同體”的概念內涵,本文嘗試使用和闡釋“功能性村寨”概念,以田野、民間口述和地方文獻為基礎,展現一個功能性苗寨的形成史。
一、“功能性村寨”概念的提出
有關“功能性村寨”概念的提出,最早費孝通在論述村落是社區研究單位時說:“我們所研究的單位必須是實際存在的職能單位——村莊。我們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人民生活”。[6]6“職能”一詞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即譯為“功能”,功能主義學派從整體論視角出發,認為“一切文化都具有特定的功能,無論是整個社會還是社會中的某個社區,都是一個功能統一體”[7]122。在此意義上,費孝通把村寨稱為“職能單位”,實為一種整體論思維,不僅關注村寨自身特性,還需關注村寨在整體社會環境中所擔當的角色。
不過本論文認為,賈仲益教授提出“功能型村寨”的概念,至少有兩點是較為模糊的:一,子寨是功能型村寨,那么母寨是否為功能型村寨呢?二,“功能型”村寨的表述,似乎是將黔東南區域苗族村寨作為一種特殊村寨類型而描述,那么與其相對的其他類型村寨是什么呢?本文認為黔東南、都柳江流域的村寨不是和他區域相比的一種特殊的村寨類型,而是對“村寨共同體”性能檢測的區域性、民族性表達,所有的“村寨共同體”都應是“功能性村寨”,能否成為“共同體”不是“自定義”,而是由區域社會、由村寨外交來定義、檢測。村寨外交,不是簡單的寨際娛樂,而是地方社會對村寨負擔義務和責任能力的一種檢測。
二、功能性村寨的形成與裂變
本文所研究的村寨位于都柳江流域黔桂交界區域,據道光十一年《融縣志》載,都柳江,“發源貴州至懷遠縣老堡口合古宜江潯、榕二江,又名牂牁江,由牂牁夜郎至縣治至柳城會龍江南下經柳州,左,合雒容江通象州,右,合來賓濁水江至潯州府,合左江、秀江至梧州府,合府江南下廣東。”①道光十一年《融縣志》手抄稿.卷之二·山川。都柳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連通黔、桂、粵三省的重要水運通道,便利的水運,自然成為商業、軍事、人口流動的通道。自宋以來頻繁的移民,使得該區域基本呈現為以村寨為單位的“高山瑤、半山苗、壯侗住山槽、客家住街頭”多族群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PD②按照人類學傳統,為保護村寨,隱去村寨真實名稱,以字母替代。寨在20世紀50年代民族識別中定為苗族村寨,但根據村寨口述來看,該寨實為一個苗、侗、漢、壯等多族群歷史融合為苗族的村寨。據苗族、侗族的父子連名代際推算,據《安太鄉志》記載和村寨口述,PD寨開寨距今已有29代(大約在元初),其裂變子寨LD寨、X寨。
(一)功能性村寨的建構:PD苗寨形成史
1.生存合作:楊、賈兩姓共居建寨
據村寨口述,PD寨的開寨始祖為侗族楊家,楊家原居住林峒①“峒”常與“洞”通用,唐宋時期對湘黔桂邊境羈縻州地區稱為“洞”或“溪洞”。祖寨——大寨,楊姓兄弟在打獵追趕一頭野豬時,發現PD古樹參天,且山坳中有大塊平緩之地適宜開田。山坡上有一口水塘,塘水清澈,周邊草木茂盛。于是就在水塘中撒下隨身攜帶的谷種。②在調研中,諸多苗侗村寨都有打獵、撒谷種,以確定適宜居住的類似開寨故事。并祭祀發誓:“來年秋天,塘中谷種長成稻,結有360顆谷粒,野獸不吃,風吹不倒,我們就來此居住。”③在都柳江流域黔桂交界地帶,苗、侗、瑤、壯各族群開寨都十分慎重,通常對于所發現的新地要舉行宗教儀式,許愿發誓,一周年或者二周年期結束后驗證誓言,若誓愿成真,則認為這不僅是風水寶地,且是祖先顯靈昭示可居住之地,如此才會正式遷徙建立新寨。第二年秋天,果真塘中水稻顆粒飽滿,且不多不少,剛好360顆。于是楊家兩兄弟(2戶)開寨PD,所以當地有“PD侗族兩家人”的說法。
PD處于林峒邊緣(據林峒大寨3公里左右),林木茂盛,野獸出沒,禍害莊稼,楊姓在PD生產生活得不到保障,人丁不旺,難以留居。于是在居住2代人后,邀約原同居大寨的賈姓來PD居住,賈姓苗族,擅長山地狩獵。大寨人口多,地方小,姓氏雜,矛盾多,賈姓也樂意搬到PD居住(居PD寨27代)。從此,楊姓、賈姓共居PD。
2.村寨秩序:開寨始祖崇拜
共居需要合作,但也需要通過競爭確定合作的秩序與權力。苗寨最傳統的秩序為“開寨始祖崇拜”。萊曼(F·K·Lehman)曾以“開寨始祖崇拜”解釋東南亞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他說,在東南亞,原住民認為土地原初及最終的所有人都是“鬼”,開寨始祖們為了利用土地,和地鬼簽訂了相應的契約。據此人神(鬼)之間保持溝通,鬼主的要求可以適時得到滿足(如供物、祭品、禁忌等)。且這契約以及與地鬼溝通的權力將傳至定居地創建者的后代和繼承人,直至永遠。[10]191正因為“開寨始祖”具有和地鬼溝通的特殊權利,所以在寨子內享有優先的權利和至高的榮譽。開寨始祖優先權最明顯地保留在祭祀儀式中,每年初一敬蘆笙坪,作為開寨的楊姓具有優先進蘆笙坪的權利,楊姓沒有進蘆笙坪,賈姓只能在外面等著;且在敬獻犧牲祈福過程中,唯有開寨的楊姓可以敬獻豬頭,而賈姓只能敬獻酸魚、酸肉、糯米飯,且祭祀儀式的主持人也必須是楊姓老人。除苗年外,苗族較大的節日莫過于新禾節六月六,這一天大家要吃新谷,開田魚,宴請親朋好友。在PD寨,根據開寨始祖崇拜,新禾節,楊姓先過,中午吃節,賈姓后過,晚上吃節。對開寨始祖崇拜的遵守,是楊家與賈家合作的表現之一。
1.2 研究方法 該試驗為長期定位試驗,于2017年進行,試驗設3種耕作方式:秸稈還田深松耕(DPT)、秸稈還田免耕(NT)和秸稈還田常規耕作(PT)。試驗設3個重復,3個小區,每個小區面積225 m2(15 m×15 m)。種植制度為夏玉米一年一熟,供試品種為鄭單958,于2017年5月播種,密度為66 600株/hm2,于10月收獲。其中,夏玉米基施氮200 kg/hm2,P2O5150 kg/hm2和K2O 150 kg/hm2。
3.權利競爭:聯宗策略
開寨始祖除具有儀式上的優先權外,在居住空間上也應居住村寨中心。該區域苗侗瑤建寨在空間格局上都保持開寨始祖崇拜的原則,建寨圍繞開寨顯靈地,建蘆笙坪、建屋,開寨始祖居于村寨中心,后來者則依次向外排列,這一“先來后到”的階序在居住空間格局上得到保存,在宗族名稱上得到表現,苗侗族群村寨中宗族名稱基本是依據其在村寨中所處的空間位置來命名,如目前PD大寨賈姓有5個宗族,苗語分別稱為“厚養”(漢語意為寨頭)、“故翁”(寨心)、“彌東”(夾縫)、“碭夏”(臨河)、“歐信”(臨渠) 5個宗族。PD大寨的空間格局至今仍然保持著傳統苗族村寨布局原則:寨心為開寨時發現的水塘(村民稱為龍塘,每年初一或者天旱祈求風調雨順的地方),在龍塘的東邊,有一塊形似駿馬的大石,村民稱之為“龍墳”(具有驅邪安寨,安定村寨龍脈的功能),龍墳邊的空地則是開寨初建的蘆笙坪(堂)。苗族建寨習俗是“建寨先建(蘆笙)坪”,蘆笙坪既是祭祖的地方,也是祭祀土地公的地方,每年大年初一,全寨人都要聚集在龍塘、龍墳、蘆笙坪祭祀祈福。當地苗族的“扮磨個”①“磨個”是當地苗區妖魔鬼怪、邪惡、骯臟事物的統稱,每年大年初一,村寨都有一群年輕人扮演“磨個”,在村寨中的鬼師帶領下敲鑼打鼓清寨,一邊清寨一邊嘴里喊著“賴雜花炮哦”,所經過之處,或者能聽到聲音的地方,各家戶都放一串鞭炮,以示驅邪,趕走邪惡與骯臟,保護家戶平安。其行走路線即為村寨房屋邊界范圍。的清寨儀式也須以龍塘為起點。可見,龍塘、蘆笙坪是苗寨中心,寨心應為開寨始祖居住。
然而目前居于龍塘——村寨中心的是賈姓家族,而非楊家,為何不符合苗侗傳統苗寨格局呢?據村寨老人講,原來楊家的確住在寨心,但苗族有“拉鼓”傳統,②拉鼓,為苗族傳統節日,同一血緣宗族為維持內部的聯系,相互支援,定期舉行聚會的活動,據村寨老人口述,村寨最后一次拉鼓大約在100多年前。在拉鼓節時,賈姓家族來了很多客人,不小心踩壞了楊家好幾只小雞,楊家人很心疼,于是決定離賈家遠點,逐漸從中心(龍塘邊)向外建房。現在村寨中楊家的祖基地大約距龍塘有20米寬。這是共居所需的權利與秩序的調和。
居住空間的競爭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競爭表現在以各種策略壯大自己的勢力方面。吸納他姓、他宗是壯大姓氏、宗族實力的重要途徑,賈姓、楊姓都在此途徑上積極運作。從宗族結構上看,目前PD寨楊家有兩個宗族,且無血緣關系,分為“上楊”和“下楊”,“上楊”又稱為“清凈楊”,意為為人正直,不亂開玩笑,以此作為和“下楊”的區分。楊姓兩宗族原本相互開親,但在村寨權利結構較量中(據說PD寨始終保持20%楊姓,80%賈姓的人口規模格局),楊姓逐漸實行“同姓不婚”的婚姻禁忌,那么在當地村寨內婚是其主要婚姻范圍的情況下,楊姓實為通過聯姻與賈姓緩和競爭,且更多合作。
賈姓最初有兩宗支搬進PD居住,不久又邀約同姓不同宗的另一支苗族賈姓前來共居(具體年代不詳)。賈姓苗族因擅長山地狩獵、采集,野外收成頗豐,且人丁興旺。因此,在PD,賈姓人口規模、族際政治勢力、經濟勢力都遠遠超過侗族楊家。在PD,楊家因開寨擁有儀式優先權,而賈家逐漸獲得世俗權力。為穩固在村寨中的權力結構,賈家先后接納了在此地打工的漢族廖姓、謝姓,壯族韋姓共居。
廖姓(在PD居住16代),漢族,逃荒流落至此,原為賈姓打工種地,為人厚道、勤勞,被賈姓收留,并成上門女婿,依女方繼嗣,改姓、該族(民族與宗族)而留居繁衍為賈姓宗族的一支。韋姓(居住PD、LD10代),壯族,三防才杰村人,逃荒、打工流浪至此,多年為PD賈姓種田,因長久不回老家,擔心家人不在,愿意留下居住PD。謝姓(居住LD8代),據村寨口述史和《安太鄉志》載,謝姓原為漢族,白云鄉人,在PD賈姓家族打工種田,在回家途徑紅水良雙村時,闖進苗寨觸犯了該寨的拉鼓儀式。按照苗俗,謝家要么用母鼓救鼓,要么被罰120頭牛。在萬般無奈之際,謝家轉回PD請求賈家解救,苗族賈家素明鼓型大小和救鼓方法,于是替謝家消了災。謝家為了感激賈家的恩情,愿留居PD,并改姓為賈,與賈家結為兄弟,并承諾謝家永世都尊敬賈家。
學者錢杭認為“聯宗”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同姓或異姓之間的功能性地緣組織。聯宗有兩種形態,一種為同姓聯宗,“兩個或多個同姓宗族之間,在對某一(或一組)共同祖先加以認定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正式的約定,以聯宗譜或聯宗祠的形式取得穩定的成果,在某些具體的功能目標上實踐宗族間的充分諒解與密切合作。由此形成一種同姓的地緣網絡結構”[11]2,20在PD寨,賈姓和楊姓都使用同姓聯宗策略,賈姓內部只以居住空間格局來區分,對外則模糊為同一宗族分支;楊姓內部分為上下楊,但將“同宗不婚”的婚姻禁忌擴展為“同姓不婚”,實為對聯宗的操作。此外對于廖姓、謝姓的聯宗,則為改姓聯宗,“姓氏在某種情境下,成為人群合法居住的身份符號,改姓是對姓氏符號的一種合理而巧妙的策略性運用”[12],人口較少群體獲得村寨“入住權”的普遍方式。
“聯宗”“建構”了一個對內有區分、對外高度統合的族群共同體。在都柳江流域,聯宗宗族不必遵守“同宗不婚”的婚姻禁忌,村寨內不同宗族之間的聯姻又密切了他們內部的聯系,擴大了親屬范圍。而在PD苗寨的形成過程中,聯宗是漢、壯族群融入苗族的重要策略;賈姓逐漸獲得村寨主導權,也引導楊姓侗族逐漸融入苗族,聯宗和優勢權利共同促進多姓、多族(宗族與民族)在PD苗寨的融合。
(二)功能性村寨的自我調節:裂變子寨
所謂“村寨裂變”是指一個祖寨(母寨)在自我勢力范圍內分裂或衍生出多個子寨,子寨若獨立成寨,則在地權、經濟權、政治權、外交等方面獨立于母寨且與母寨平等,當然母子裂變寨在情感聯系、婚姻交往方面較為親密,在祭祀儀式上保持著開寨始祖崇拜秩序。黃忠懷將這種母子寨關系稱為“同源村落”,“同源村落大多是由早期的同一個村落分化裂變而成”[13]。同源村多指向子寨之間的關系,難以表明母寨與子寨之間的關系結構。
接納的韋姓在PD寨中生活了近2代,但族中出孽子,愛惹是生非,不僅村寨不得安寧,外寨經常找上門來算賬,PD寨對此意見很大,于是決定把寨東北角一片山坳給韋姓建寨,即為現在的LD寨。為減少日后麻煩,同時把剛接納的謝姓(改姓為賈)也安排居住LD寨。LD寨作為PD附屬寨存在,PD寨和韋姓、謝姓約定:其一,韋姓、賈姓(謝姓)需說苗話、習苗俗;其二,作為擬血親兄弟,需履行兄弟義務,大年初一要到祖寨去祭祖、祭蘆笙坪,參與PD坡會等;其三,居住LD,房屋建筑不能越過寨頭的古楓樹,房門不能正對PD寨開;其四,日后若發達能騎上高頭大馬,途徑PD,必須下馬牽馬而過,世代保持對母寨的尊重。若違背契約,韋姓、賈姓(謝姓)則“斷子絕孫”。
1942年PD寨發生一場大火,燒毀諸多房屋后,另建X寨。表面上是因災害而裂變子寨,當地人解釋分出X寨的原因,一為人口增多,老寨容納不下新的房屋;二為人多手雜,事情多,有部分人不愿意住一起。于是老寨把對面山坡的柴山辟出來建立新寨,新寨為母寨的均值分裂,在姓氏比例結構上和母寨幾乎一致。
不論是LD寨,還是X寨,表面上看從母寨中裂變的原因不同,但其本質都是母寨難以維系內部的團結穩定,需要借助分裂自我調節共同體性能。裂變后的母寨借分裂契機重新組合、重整秩序。子寨從母寨中分裂,可刺激內部快速發展,盡快從母寨附屬的聚落成長為與母寨平等的獨立的村寨。
三、村寨外交:功能性村寨形塑的催化劑
一個功能性村寨的形成,不只是人群、房屋、田地組合的聚落,①田野調查發現不僅單家兩家人不能稱為寨,就是10多戶人家,沒有外交或參加坡會的,本地人都不會稱其為寨。還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一個保障村寨安全的防衛單位;一個有明晰地域邊界空間單位;一個有共同的祭祀空間、能夠獨立舉辦民俗活動的組織單位;一個可以平等和外寨交往的外交單位。唯有在與他寨交往中,才被區別、被認定為是一個獨立的村寨。
(一)保障生存的安全防衛單元
在都柳江流域,其地貌格局基本為“九山半水半分田”,目前該區域村寨人均水田面積僅有0.2-0.6畝,人地沖突明顯。聚族而居是人群聚集的基本形式,但為何多姓共居是該區域村寨的基本結構?這是因為惡劣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使得單家獨戶難以獨存,據道光十一年《融縣志》記載,自元大德九年至雍正元年,(筆者統計)融縣發生旱災1次;雨雹3次;虎災4次;大水5次;饑荒5次;鼠災2次;蝗災1次;大疫5次;地震2次等。此外“盜賊猖獗”,“肆行剽掠”,“恃邊為患”等動亂事件也多地、多次發生。②統計數據來自道光十一年《融縣志》手抄稿。《黎平府志》也記載:“當地土匪、游匪,數百為群,聚散無定,搶劫拒捕,民不聊生”。[14]惡劣的生存環境已經超越家戶自足的范圍,“家戶雖然能夠自主解決部分日常生活生產事務,但是卻無法有效解決超越家戶的公共事務,這就需要家戶之間彼此聯結,集體行動,共同治理”[15]。因聯合防衛、聯合狩獵的需要而接納他姓是該區域建寨的普遍模式。
而這種聯合防衛在與他寨的較量中顯得更為亟需。在PD寨的東南面的山背后,相傳200多年前,曾有“白苗”居住,①清代多根據苗族服飾的顏色,將苗族分為“白苗”“黑苗”“紅苗”等,都柳江流域主要為黑苗,但在黑苗入住之前,已有少量白苗定居,在田野訪談中,在ZH寨、PD寨都流傳有和白苗爭奪地盤的械斗故事。PD寨和白苗為爭奪地盤常有械斗發生,且持續時間較長。正是村寨力量薄弱不能自保的情況下,PD寨接納異姓、異族的韋姓、謝姓入住,默許高段王家定居,賣地給鄭姓商人開辟鄰近友邦寨SH寨。安全防衛是村寨立足的重要任務,接納他姓、他族入住,合作防衛是都柳江流域早期村寨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具有明晰邊界的空間單元
在都柳江流域,自古至今,寨際之間的沖突基本都與“村界”有關。南方山地族群均有“號地”傳統,最初村寨建立,圍繞房屋中心,依據地形、山脈、河流等自然屏障對外阻隔、對內交通的地盤(山、林、河、田、地)都屬于該村寨的勢力范圍,村寨成員可以在勢力范圍內狩獵、采集、開荒種山、放牛割草等。為避免因權界而生發村寨、族群沖突,在當地習慣法——埋巖②都柳江流域黔桂交界的榕江、從江、三江、融水4縣,當地苗族都稱“習慣法”制定稱為“耶脊”,“耶”在苗語中為“石頭”意,“脊”在苗語中意為“樹立”,合起來為“樹立石頭”。當地也有根據西南官話音譯為“依直”。而黔桂兩地學者普遍將其漢語意譯為“埋巖”或者“栽巖”。因為開會商議的法規制定后,要在開會地點栽種一塊平面平整的條石(大小不論),一般2/3或1/2的石頭埋在地下,1/3或1/2露出地面,以作標記。暗含制定的法規如同石頭堅固不移,石在法在,必須嚴格遵守。若在同一地點埋巖,也可以在原有巖石上刻刀痕作為標記,不必次次栽巖。中,很大一部分內容都與村寨劃分地域界限有關。即便土地改革,也沒有因行政力量推動村寨間財產均分,各村寨財產大都與祖產地有關,是村寨共有的財產。即便分田到戶,到戶的也只有一定年限范圍內的使用權,且河流、風水林、護寨林、墓地這樣的地盤絕不會分到家戶。所以村寨權界意識并不會因分田到戶而減弱。
在訪談中得知PD寨因地界問題曾經和兩個寨子發生了大的沖突,一次因為鄰近PX寨經常到PD寨的山林中放牛,破壞林中樹木,PX寨還有意挪動界石,兩寨在商議無果中發生沖突,PD寨還因此被打死兩青年;一次因JR寨和PD寨河道相接,但JR寨常到PD寨所屬河道中鬧魚,結果兩寨沖突持續多次。正因為和他寨的沖突,才更明晰村寨權界、村寨獨立,同時極大地激發了村寨成員的集體責任感,使得村寨共同體更為緊密和牢固。
這種明晰的權界意識還延伸至村寨成員資格。村寨中的成員可分為:“事實成員”和“形式成員”兩種。所謂的“事實成員”,即被村寨認可的成員,允許參加村寨活動,賦予其承擔村寨責任和義務,而其自身也以村寨集體為重;“形式成員”雖然在村寨居住,村寨不邀約或通知其參加集體活動,也不賦予其村寨義務,不向其募捐村寨集體事業的資金。從“形式成員”轉變為“事實成員”過程是村寨對個體、家戶道德品性以及集體意識的考察和篩選過程。每一個村寨的獨立,都是在內外交往中地域邊界和成員邊界不斷被確定、維系的過程。
(三)擁有獨立的祭祀空間和舉行民俗活動的祭祀單元
蘆笙是苗侗文化的表征,是族群凝聚的靈魂,當地有“蘆笙一響,腳板就癢”的說法。蘆笙是苗侗族群村寨,內部凝聚、外部聯誼交往的媒介。而蘆笙坪是蘆笙活動的專門空間,位于寨心,是村寨心臟和靈魂。寨內祭祀、寨際交往都在蘆笙坪上進行。正月初一全寨要在蘆笙坪吹蘆笙、祭祖祈福。蘆笙一響,全寨各家各戶,男女老少,攜帶祭品(酸魚、酸肉、糯米飯和3杯或12杯米酒)齊聚蘆笙坪,圍著蘆笙柱(或“龍墳”或蘆笙坪中心)擺放好祭品、香根、冥紙,在儀式主持人的帶領下,全寨男女手持香根,面向東方,面向蘆笙柱,向祖先、天地神靈三拜鞠躬,感恩祖先、神靈保佑,祈福風調雨順、人丁興旺。祈福結束,全寨人分享各家戶帶來的美食與美酒,你敬我酒,我喂你肉,村寨一年的歡樂、幸福在此刻爆棚,一年中的糾紛、不快也在此刻化為輕煙。村寨要出行趕坡③坡會是廣西苗、侗、瑤、壯族群共居地區在年節期間多村寨聚會、娛樂的民間傳統節日,節期一般在農歷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七,活動兼有悼念先祖、爙災祈福、交流感情、娛樂游玩等多種功能。之所以稱之為“坡會”,是因為這些活動地點主要選取在山坡中間較為寬敞的平地,便于群眾觀看民俗表演。、到他寨打同年④打同年,苗語音譯為“阿幾隊”,漢語意為“做兄弟”,是一種兩村寨輪流到對方家做客的聯誼活動。、賽蘆笙,都需在蘆笙坪上集體吹奏蘆笙三曲,祈福祖先保佑村寨平安,出行男女老少健康平安。從外面回到本寨,也要到蘆笙坪吹奏蘆笙三曲,向祖宗報平安,感恩祖先保佑。他寨到本寨交往,必須首先到寨子的蘆笙坪祭祀、吹奏敬蘆笙三曲,然后才能在村寨其他空間活動。蘆笙坪是村寨福祉之源、凝聚的靈魂。
除祭祀外,蘆笙坪也是村寨最活躍的公共空間,村寨成員日常閑暇都集中在這里,聊天說笑、傳播新聞、刺繡編織、孩童玩耍,而節日期間村寨集體聚餐、晚會、游園、對歌等也必然在蘆笙坪舉行,正如賀雪峰所言:“舉辦文藝體育活動,通過各種健康的活動將農民組織起來,相互交流、互相欣賞,甚至相互幫助,這些活動大大提高農民福利水平。”[16]集體活動不僅增進村寨成員交流情感,神圣空間中更易形塑村寨品德,形成成員的歸屬感和幸福感。現在各村寨蘆笙坪又成為村寨政治公共空間,村寨委員會大樓幾乎無一例外地依蘆笙坪而建。蘆笙坪是村寨集會、寨際交往的物質基礎,是成寨與否的形象標志。
以蘆笙為媒介的民俗活動是村寨實力的表征,也是衡量村寨能否獨立的標桿。正因為人力和財力的欠缺,X寨從1942年建寨以來,一直到1998年才第一次和他寨打同年外交而顯示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村寨。苗侗的蘆笙活動是一種集體性活動,蘆笙隊的建立除了需要購買蘆笙的高額資金之外,①按照黔桂蘆笙售賣市場行情,購買一把新蘆笙需300元,維修一把蘆笙連帶維修費、師傅的招待費需100元左右,一般蘆笙使用壽命僅三五年,因此購買一堂新蘆笙約1萬元左右,每年維修費則在1-2千元左右。熱愛民族文化,懂蘆笙曲調的人才是村寨舉辦蘆笙活動的基礎。一堂蘆笙至少還需30位技藝精湛的蘆笙手,小號、中號、大號和芒筒四種類型對于吹奏技能的要求都不一樣的,各擅其能且善于配合,才能吹奏最響亮的蘆笙,顯現村寨實力與活力。
(四)寨際交往的外交單位
正如上文所述,不論是因自衛、權界的寨際沖突,抑或埋巖的寨際聯盟,再或者坡會、打同年、籃球賽的寨際聯誼,村寨都是外交的普遍單位,是否有外交欲望、能否外交、外交的頻率都是對“村寨性能”的無言檢測:其一,對村寨凝聚力的檢驗。村寨集體的外交需要村寨成員參與的意愿,而參與集體活動可能就意味著放棄個體利益,放棄自我個性,服從村寨集體行動。如蘆笙外交,比拼的不僅是蘆笙好壞、吹奏技能、個體力量,更是團隊合作和集體榮譽感;其二,村寨組織力的檢驗。任何一次外交,都需要村寨的周密組織和準備,需要有服眾的領導,需要成員的積極配合,在集體外交活動中個人平日恩怨都需擱置一邊,服從安排,合作配合。村寨外交活動能否舉行,是否頻繁舉行都是對村寨干群關系的檢測,對成員關系好壞的檢測;其三,村寨口碑好壞的判斷。寨際交往欲望是村寨口碑的無言傳遞,沒有那個村寨愿意因外交而惹出麻煩。所有的外交都需要遵守社會交往的道德規則,尤其在娛樂狂歡的酒宴中能把持自己的行為,以村寨形象、大局為重。因此每一次外交,村寨老人都要反復進行村寨道德教育,要求大家遵守規矩,相互監督,不要壞了村寨口碑;其四,村寨實力的檢測。趕坡需要鞭炮、禮花、交通等費用,打同年需要接待同年的食宿、贈送同年禮物等費用。②據田野統計,小村寨打同年花費一般在2萬元左右,大寨則花費在5萬元左右。這些高額花費甚至相互攀比是對村寨成員努力的激勵,是吸引聯姻的手段,經濟實力是村寨實力的明顯表征。外交是對村寨性能的檢測,是村寨被地方承認、認證的必經程序。
四、結論
一個苗寨的形成史是都柳江流域苗、侗、壯、瑤村寨形成的縮影,每一個從聚落到村寨的演化過程實為村寨性能(共同體)完備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很多時候不是內生的,而是在與他寨交往的外部壓力下促生和激發出來的。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村寨,不是村寨自我確定,而是在外交中對于村寨性能進行檢測,是否有他寨愿意與其交往、是否有能力承擔外交,外交的頻率、外交的范圍都是對村寨性能的一次次檢測和一次次的修復、增強。在都柳江流域,正是因為熱衷于村寨集體交往,即使村寨分散、多為小規模的、多姓共居的村寨,村寨內部團結緊密、地方社會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