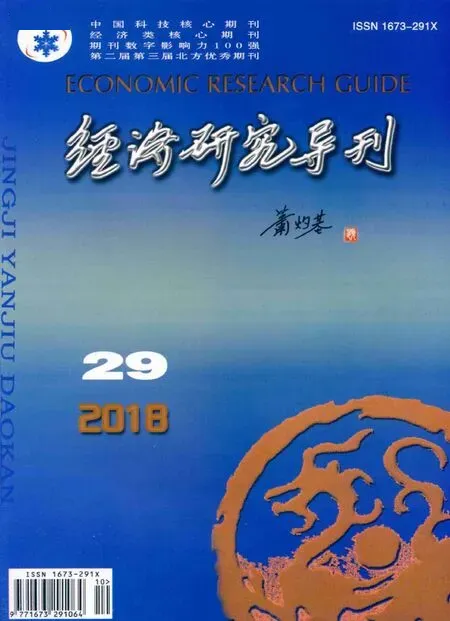基于垂直分工視角下的分行業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以電子設備計算機行業為例
費曉暉
(江蘇省鹽城工學院經濟學院,江蘇 鹽城 224051)
引言
實際有效匯率(REER2)自發布以來,一直被作為世界貿易競爭態勢的風向標。當前,IMF、BIS和美聯儲等主流機構都定期公布該指數。在計算方面,雖然各個機構選取的參照與細微準則存在一定差距,但其計算方法多年來都未有顯著變化。隨著國際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學術界對原先的方法質疑的聲音日益加大。這種質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關于REER權重的設定框架;以及相對價格異質性的問題。目前國內關于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的計算主要集中在對行業價格水平與總體存在差異的研究,但是在最重要的權重計算環節卻較成熟的國家總體層面的方法有所退步。本文使用趙永亮等(2017)基于全球產業鏈視角的實際有效匯率測算方法,在充分考慮了產業鏈垂直分工與第三方市場效應的基礎上構建分行業權重,結合之前研究的分行業相對價格指數,以機電行業為代表,構建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
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如下:1.綜述當前學術界關于REER及分行業REER的研究;2.模型推導和對機電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計算;3.結論。
一、文獻綜述
(一)權重系數的研究
最初,學者從最簡單直觀的角度來嘗試計算REER的權重,即用貿易伙伴國雙邊貿易量占一國總貿易量的比例作為權重(比如以中美貿易量占中國整個貿易量的比重作為計算中國REER時美國的權重)來計算。但這種方法存在一個嚴重缺陷:一國或者某一行業的國際競爭態勢,并不僅是其與其他國家或者行業的雙邊直接競爭關系的加總。舉3個國家的例子來說,中韓之間產品的競爭除了體現在兩國產品在雙方市場的貿易量,還發生在其他國市場,當中國的貨幣相對韓元升值時,在美國市場上中國的出口商品因此會相對韓國的同類商品變貴,從而降低相對競爭力,這種效應被稱為第三方市場效應(third-market competition)。McGuirk(1987)的研究發現,如果忽略掉第三方市場將會產生嚴重的系統性偏差;徐奇淵等(2013)在之后的研究中有詳細闡述。
事實上當前以IMF和BIS為主導的國際機構在計算實際有效匯率時均考慮了第三方市場效應。IMF的權重計算的理論基礎是根據McGuirk(1987)的研究;而 BIS的權重計算則是基于Turner&Dack(1993)的研究。這兩種方法雖然在細則和表述上存在差異,但在權重計算時都出自Arm ington(1969)關于從需求方分解不同國家產出的理論。然而,Armington從生產國源頭定義商品的這一劃分方法在當今已不能反映現實經濟環境:將商品按最終出口生產國,并不涉及國家之間同一產品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由此產生的國家間進出口貿易也僅僅限于最終產品貿易。①國際化垂直分工和產業鏈貿易真正從20世紀70年代迅速發展,該分工在當時的國際貿易環境并非不合理。在當今全球價值鏈革命造成中間品貿易迅猛增長的背景下,國家與國家之間貿易額所包含的信息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國際分工格局已逐漸從單一產品細化到產品的生產環節,相應地,各國已逐漸從生產自身比較優勢的產品轉為從事與自身比較優勢相符的生產環節。
Bayoumi等(2013)在傳統Armington方法基礎上加入價格調整指數以包含中間品對實際貿易的影響。如前面所述,價格因素并非權重中的一部分而是計算公式中其他變量,因此該方法只是對傳統模型的簡單修正。Bems和Johnson(2012)認為,為準確地測算雙邊商品價格變動對一國增加值貿易的影響,梳理全球產業鏈生產的基本過程是必要的。他們提出,垂直專業化分工基礎上提出的產業鏈實際上是以最終需求為導向定位的產業鏈。Bems和Johnson(2015)在隨后的實證研究中發現,由于生產鏈往往較為固化,因而各國的投入品之間、投入品與增加值替代彈性相比傳統的最終品需求彈性小得多。
(二)側重相對價格指數的文獻
目前,文獻中經常用到的價格指數有以下幾種:相對出口價格、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工業生產價格指數(PPI)勞動力成本指數(ULC)和GDP平減指數。肖立晟(2014)通過匹配中國與主要經濟體的雙邊金融聯系,構建了金融資產權重運用資產價格作為平減指數,不失為一種創新。
(三)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的研究
以往實際有效匯率的計算都是停留在國家整體層面,用整體層面的指數來解釋引導部分行業的時候可能會產生異質性問題。徐建煒(2013)等采用CEIC和OECD的STAN數據庫中的價格數據;鄒宏元(2014)等采用細分行業的批發價格指數和生產者價格指數(根據各國數據的可得性進行選擇)作為計算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的平減指數,使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更真實和準確地反映各行業出口競爭力的變化。但是,權重部分計算較已經顯得陳舊的IMF和BIS的傳統方法進一步退化(沒有考慮第三方市場效應①分行業后無法按照Armington的框架分品類和商品),更沒有考慮產業鏈垂直分工等最新研究成果。
二、模型推導和對機電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計算
行業實際有效匯率指數(Sector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以下簡稱S-REER)構建的基本思路來源于McGuirk(1986)的雙重貿易權重。下文將簡單陳述其核心結論,分析其理論缺陷,并在此基礎上重構S-REER。
(一)行業REER(S-REER)權重模型的推導
Armington(1969)提供的模型解決了這樣一個問題:某消費國c消費的各國出口的產品t相對價格變化率已知,求解c國對j國t產品的需求量的變化率。而構建REER需求解決的問題是:各國出口的各品類產品相對價格變化率已知,求解全球對出口國j生產的所有產品的總需求量的變化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McGuirk(1986)對log變形后進行了關于消費國和品類的加權運算,建立了雙重貿易權重模型,見公式(1)。

雙重貿易權重綜合反映了k國產品與j國產品相對價格變動對j國總產出的影響程度,又被稱為競爭力權重(Competitiveness weights)。該權重也被IMF作為計算REER的貨幣權重。
構建垂直分工背景下的S-REER,首先需要厘清全球價值鏈。在全球價值鏈生產方式下,一個產品由一國出口,卻有可能由多國共同生產。趙永亮等(2017)利用利昂惕夫逆矩陣將全球投入產出表(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以下簡稱“WIOD”表)轉化為全球價值鏈增加值表。本文將采用其WIOD表的分解方法和構建“Va-REER”的基本思路,進一步推導出具實踐指導意義的S-REER。S-REER和國家整體層面REER一樣,是加權平均雙邊匯率指數。為了更簡潔地說明問題,我們以人民幣機電行業S-REER為例來分析其貨幣權重的經濟學意義。假設中國、美國、日本等多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存在著競爭關系,這種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若美元相對于人民幣的雙邊匯率升值,且所有其他國家的雙邊匯率保持穩定,則各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中包含美國這一生產環節的,其人民幣價格都會上升。各市場的消費者將根據各國出口的機電產品的最終價格調整其消費結構,一部分機電產品需求價值量提高,另一部分不變,還有一部分減少。這些由各國出口的機電產品中,有一部分由中國機電行業提供了增加值,則價值鏈末端的需求價值量的變動將傳導至中國的機電行業,其影響程度和全球價值鏈結構以及價格競爭結果有關。這種影響程度實際上就是美元占人民幣S-REER的貨幣權重。基于這樣的分析思路,可以很容易推導出S-REER的貨幣權重模型。
(二)電子設備計算機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計算
本文依據聯合國的主要國家分行業分類標準(ISIC Rev.4),選擇了電子設備計算機行業來進行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的計算和分析。為了與其他國家數據統一,本文將國內劃分均參照聯合國標準進行調整。
權重部分的計算主要依賴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以下簡稱WIOD)數據庫發布的以核算貿易增加值(TiVA)為導向的國家間產出投入表。數據表中,縱向為國家項,橫向為行業項,除去預先界定的35個行業外還包括最右側的“最終使用”項,按照WIOD的分類方法,包括家庭的最終消費、服務于家庭非營利組織的最終消費、政府的最終消費、總資本形成、存貨變動。
相對價格變動部分的數據,國內價格使用中國統計年鑒2010年4月到2017年1月的分工業生產者月度出廠價格指數并計算出年度平均值,國際價格使用同時期OECD的STAN數據庫年度數據;名義匯率來自嘉盛Forex交易平臺上觀察期的月度平均數據。在此需要指出,雖然國內價格數據等其他可以獲得更高頻的數據,因為STAN數據庫中的國家間價格數據為年度數據,基于數據精確度測度中的“木桶效應”,在此測度的分行業人民幣實際有效指數均為年度數據,與總體層面的數據在頻率上并不相同。
下面展示了本文計算的電子設備計算機行業的行業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以及與總體層面REER的結果。

圖1
三、結論

圖2
本研究基于全球產業鏈視角的計算方法,分行業測度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結果顯示,中國電子設備計算機行業實際有效匯率較傳統計算方法存在差異。本文運用前沿理論,在考慮了第三方市場效應、產業鏈垂直分工等因素的基礎上測算我國分行業實際有效匯率,為國際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啟示:分行業的實際有效匯率表明各個行業的國際競爭態勢并不一致,傳統的匯率政策將對部分行業產生非預期的影響,而局部產業的調控政策可能會是一個經濟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