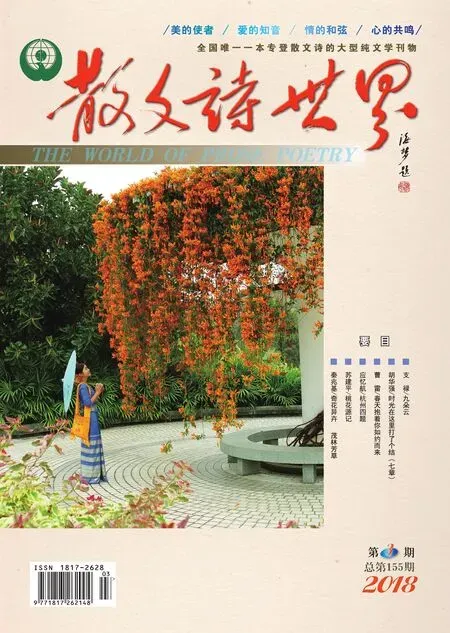我越來越喜歡簡潔(四章)
浙江 任澤建
搬運工
我總是喜歡搬運泥土,從這邊的陽臺到那邊的陽臺。細細的土粒從指間滑落,它們是果蔬、莊稼的母體。盡管冬季風有些刺,土里依舊溫暖,吸足了陽光。我在這簡單的勞作里也體悟著幸福的滋味。
這些年,我總是不停地搬運,從老家,從鄉村,從北方,一次次搬運各種各樣的種子,最后全在我的陽臺上安家。兩只細花碗,是母親的嫁妝,母親生前用過的物件總有散不去體溫,母親的身影偶爾出現在夢里,始終沉默著。我還搬運過一盞罩子燈,它曾伴我讀書。還有幾個空酒瓶,孔府家酒讓人想家……
也許,有一天我會把故鄉搬空;肯定,有一天這些東西會把自己掩埋。
冬藏的秘密
冬藏,本身就是一個秘密。跟著地老鼠找啊找,挖開土層深處的洞穴,發現堆滿黃燦燦的大豆,連太陽也被欺騙了。誰說鼠目寸光,這分明就是一個高手的布局。這無邊的土地上,還有多少不曾被發現的秘藏?
冬藏的秘密還在水里,門前的水面封凍了,“三九四九凌上走”。砸開一個冰窟,一條鯉魚,再也藏不住,剛冒出頭,就成了我的俘虜。
其實,更多的秘密在凋謝的葉子里,在沉睡的草根里,在搖晃玻璃窗的寒風里。曾經,我在冰雪的道路上騎行,伴著雪粒推開一扇門,教孩子打開課本,我青春的秘密就隱藏在那些單調平靜的日子里……
畫出一縷風
風吹過,綠色的葉子搖晃起來。我停下手中的書本,凝望。遠山的樹林也在搖晃,這只是一種感覺,感覺風的力量在加大。
我隨手畫出一縷風。風,吹彎樹枝,這該是家門口父親種下的垂柳。那時,我正好從樹下走過,柳絮沾滿了我的棉襖;我又在樹枝上畫出一只鳥,一只只笨笨的燕子,我能叫出它的名字,“燕子歸來尋舊壘”,它在屋檐下坐窩鳴叫。
我繼續畫,我看見自己的眼淚在風中飛。我看見陽臺上的花在風中開了,滿滿的。
我越來越喜歡簡潔
我越來越喜歡簡潔的文字,越來越。當簡潔成為生活方式,你只能選擇一切從簡。
該忘記就忘記吧,你看不懂就看不懂吧。虛擬的故事都在夢境,一一呈現又當如何?
就像陽臺上的這株桃樹,我見過了它由桃仁發芽的全部,當它以樹的形象在風中堅強,葉子泛紅,在陽光下閃亮。你猜不透,它隱藏了彎曲的憂傷。
更多的人與事,只要想明白了就好,說與不說都是一樣,何須在詩句里饒舌,那可是浪費了樹木與糧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