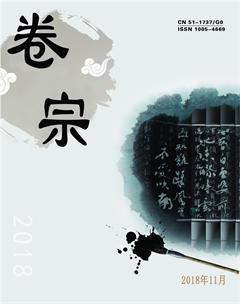淺論企業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之限額
秦婧悅
摘 要:企業所得稅中關于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的規定,其立法目的旨在促進企業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同時,基于可稅性原則及國家稅收收入利益的保護,稅前扣除應具備限額規定。然而,從內容及制度角度進行審視,相關限額規定存在局限性,需要尋找優化路徑,以更好地激勵企業投入社會公益事業。
關鍵詞:企業所得稅;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限額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企業作為建立在社會需求基礎之上而獨立存在的“社會人”,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還擔負增進及維護社會利益的義務,即社會責任。公益性捐贈,作為對一種助力于社會福利與救濟廣泛實施的經濟來源,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我國在鼓勵企業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方面,采用了積極的立法手段,針對企業公益性捐贈給予了稅收上的優惠措施。
1 企業所得稅公益性捐贈的部分扣除制度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2017年修正)第九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該條規定明確了企業所得稅中公益性捐贈,可作為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中的扣除部分,并采用部分扣除的手段,對扣除的上限予以了比例基數及限額的規定,設定為企業年度利潤總額的12%。
稅收優惠的制定,目的在于推定公益性捐贈事業,利用稅收手段,讓渡一部分稅收收入于企業,保證其能在公益性捐贈過程中獲取一定的利益,從而促進企業積極履行其自身的社會責任,以促進第三次收入分配,進一步縮小社會中的貧富差距。
而企業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制度不僅具備激勵作用,同時還兼具約束性質。針對稅前扣除予以限額的規定,意味著對于稅收鼓勵條款所必然引發的稅務籌劃現象,稅務機關所采取的反避稅措施,從其自身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對征稅主體利益的保護原則上看兼具合理性。
2 稅前扣除限額存在原因之探析
2.1 遵循可稅性原理的體現
確定征稅范圍,即判斷某個征稅對象是否具有可稅性,是由收益性、公益性以及營利性這三要素決定的。稅前扣除限額的存在,體現的是可稅性“三要素”的考量。收益性作為基礎要素,應只對納稅主體生產經營活動中產生收益的部分進行征稅,以避免損傷資本,而針對企業公益性捐贈這一課稅對象,其存在突出的公益性質,“雖然公益性是征稅的否定因素,但營利性,卻又是公益性這一‘否定征稅因素的否定因素。”[1]企業自身作為營利性組織,盡管從事公益性捐贈,但不能違背其自身“營利性”假設,忽略營利特征,這時企業公益性捐贈作為征稅對象應具備可稅性,但是出于維護企業公益性行為的激勵,應采用一定限額內的稅收優惠。
2.2 旨在對征稅主體的稅收利益保護
由于稅收優惠從本質上來說,是國家稅收利益的一種讓渡。企業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是以減少企業所得稅的稅基為手段,以犧牲國家財政收入為代價的一種稅前扣除優惠,這中間存在著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博弈。企業作為納稅主體,為增加年度利潤總額,往往會運用稅務籌劃進行避稅,而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制度,恰恰為企業提供了漏洞以進行避稅,產生形式上合法,實質上違法的行為,直接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予以相應比例的限額規定,作為反避稅措施,是基于對國家作為征稅主體的稅收利益的保護。同時,有限的稅收優惠,也降低了企業巨額捐贈行為的概率,規避了征稅主體可能面臨的大額稅款流失的風險。
3 稅前扣除限額規定之局限性及優化路徑
盡管企業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之限額規定,具有其存在的意義,但是從內容和形式上看,規定的不合理性也同樣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并不利于充分發揮該項政策的激勵性。
3.1 超額部分向后結轉制度缺失
稅前扣除限額會直接導致,當年超出限額部分的公益性捐贈無法享受稅收優惠,其不合理性在于,其制度實現建立在假設:企業自身的經濟周期與公益性需求之間存在正相關[2]。但是,現實社會環境具有復雜性和突發性,例如某些自然災害年度,具有較強社會同理心及責任感的企業,可能在經濟收入萎靡的情況下,進行超出其自身能力范圍外的公益性捐贈。針對這類情形,向后結轉的缺失體現出了制度上的局限性,在利潤較少甚至虧損的情況下,稅收優惠限額下的稅前扣除總額較少,超出限額部分由于不具備時間順延的條件,使得這類企業的公益性行為需要負擔稅收上的成本,這直接加大了公益性捐贈的經濟成本,強化了經濟形勢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制約,從而對企業公益性捐贈產生負激勵性。
3.2 扣除限額的規定上缺乏對征稅主體的合理約束
征稅權作為一種索取的權力,其本身不包含支出的特征,稅式支出是由征稅機關優惠性條款而導致的稅收收入的損失。預算控制過程中應包括對稅收優惠的預算控制。企業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可以視為稅式支出的一種,是國家為了換取社會公共利益而進行的一種特殊公共支出。[3]既然具備與財政支出同等的實質效果,那么扣除限額的界定與調整,直接關乎最終稅式支出的總額,從預算管理角度來看,應具備相應的審查機構。以美國為例,針對稅收優惠措施的調整,其采用稅之歲出預算制度,對稅收優惠在實施過程中引起的稅收減收預估額進行統計并向國會提出,以進一步優化調整稅收優惠制度。而我國現階段,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限額在調整上,同其他稅收優惠制度一樣,并未被納入稅收預算支出的體系中,缺乏對征稅主體決策相應的合理約束。
3.3 完善路徑
1)建立超額部分向后結轉制度。對于向后結轉制度,可以借鑒美國相關規定:公司捐贈給公益慈善團體的扣除比例之外的部分,可以在以后的5年內進行抵扣。通過延長企業公益性稅前扣除超額部分的抵扣時間,加大企業公益性行為的經濟利益性,增強對于企業公益性捐贈的激勵作用。
2)以稅式支出視角完善限額的界定。在制度優化上,我國應把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這類稅收優惠,納入稅式支出的范疇,以稅收預算支出決策過程為導向,充分權衡各方利益,并納入公眾監督環節,以體現收入分配的正義原則,實現制度建立的民主化。
4 結語
企業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在設立限額上,存在激勵性及合理性。但是,從內容及制度角度對限額規定進行審視,超出限額部分不具備向后結轉的可能性,而且對稅收優惠稅氏支出性質的忽略,使得限額的調整和規定上缺乏合理約束性。相應的優化措施應在于對企業公益性稅前扣除限額的規定予以完善,以更好地激勵企業投入社會公益事業。
注釋
[1]張守文.論稅法上的“可稅性”[J].法學家,2000,1(5):12-19.
[2]李春明.公益性捐贈稅收制度優化問題探析[J].稅務研究,2013(5):86-89.
[3]李俊明.合理約束稅式支出的探索[J].稅務研究,2015(1):85-88.
參考文獻
[1]葉姍.社會財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進[J].當代法學,2012.
[2]葛偉軍.公司捐贈的慈善抵扣美國法的架構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外法學,2014,26(5):1337-1357.
[3]張守文.論稅法上的“可稅性”[J].法學家,2000,1(5):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