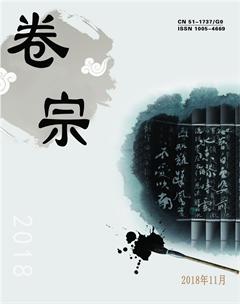中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的評價與反思
李鑫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已有30多年的歷史。其立法背景、國際對策、保護水平、行政管理、司法制度、適用效果、文化基礎、制度模式、戰略實施等都需要在法律層面上進行理性總結和思考。
1 “逼我所用”還是“為我所用”:知識產權的立法背景
近百年來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是從“逼我所用”到“為我所用”的法律變遷史,也是一個從被動移植到積極創造的歷史。從清末到民國政府5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處于被動接受階段。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從清政府實行新政向西方學習到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取材外國法進行移植,知識產權法無一不是被動立法的結果。從新中國成立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的50年里,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則是處于“調整性適用”階段。前30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知識產權制度強化了其管理職能,主要依靠一些行政法規保護知識產權;后20年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知識產權立法工作得以“撥亂反正”,建立和完善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并遵守國際知識產權制度。
2 “超高”保護還是“過低”保護: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選擇,基本依據是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狀況。首先,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本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根據2005年聯合國報告援引的千年項目的專家意見,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國際公約的最低保護標準,在不同階段選擇不同級別的知識產權保護。筆者認為,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利于低水平國家的發展,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他們難以獲得必要的知識和技術。然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社會、經濟環境和技術能力”,不能一概而論。因此,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將有助于促進技術創新,促進文化繁榮,實現經濟發展。同時,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有利于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知識產權制度的合理性,不在于為私權保護而保護,而在于實現知識創新和社會進步的政策目標。在這方面,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表示:“從長遠來看,發展中國家,如果能使文化產業成果的其他條件得到滿足,那么加強私人權利的保護將有助于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
3 “分散管理”還是“集中統一”:知識產權的行政管理
雖然中國的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體制和機制上仍存在一些問題,受到學者們的批評。
3.1 “管”、“罰”主體同一化,缺乏監督
中國知識產權管理體系的主要特征是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的一體化,知識產權管理組織不僅享有專利授權、商標注冊和版權登記的權利,還享有調解、裁決和調查的權利。總之,知識產權管理授權主體也是知識產權執法的主體,具有管理和處罰的功能,缺乏行政執法監督。
3.2 部門設置分散化,缺乏集中
在中國,有10個部門負責知識產權管理,各部門負責管理某一領域的知識產權。這種管理模式的優勢在于分工較細,職責明確,但會導致知識產權管理成本過高。此外,在建立地方知識產權機構的過程中,除商標局采取自上而下的統一組織管理制度外,其他機構法律和規章沒有明確規定。這導致機構設置模式多樣化,導致區域知識產權管理工作差異較大,并為區域協調和管理制造了一些障礙。雖然國家知識產權局已經在中國建立,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專利局的原有職能,只是增加了它的綜合協調功能,不能被認為是集中管理。總之,中國的知識產權行政組織太多,其職能過于分散,沒有統一的領導。這種情況應該在未來國家機構改革中發生變化。
3.3 保護標準多樣化,缺乏統一
由于知識產權管理的職能不同,往往導致“政出多門”,制度不統一。例如,中國頒布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但在實施中卻是由農業部和國家林業局各自制定實施細則,有關農業新品種和林業新品種的規定是不同的。有時,由于知識產權管理機構職能不同,可能存在權利沖突。例如,“金華”作為火腿商標,被金華市之外的一家浙江企業在國家商標局取得商標權, 而作為火腿的地理標記被金華市火腿協會在國家商品檢驗檢疫局取得地理標記權。雖然這兩種知識產權是由國家主管部門授權的,但不同權利主體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沖突。中國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也存在重疊的問題,對同一事務可能采用不同的管理標準。關于中國KTV的費用,國家版權局公告規定卡拉OK經營行業以經營場所的包房為單位,支付版權使用費。文化部在監督文化內容的基礎上,推出了“全國卡拉OK內容管理服務系統”,為KTV經營場所等單位提供免費的訪問和服務。這兩種標準的適用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4 “認同缺乏”還是“精神內化”:知識產權的文化基礎
4.1 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歷史惰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個體農業為基礎,以家族為單位,以倫理綱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法律文化是有惰性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內涵越豐富,消極的精神因素比以前也更加頑固。現代知識產權法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為基礎,將這一制度移植于義務本位、專制主義、人倫理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如果沒有自上而下的法律文化改造活動,沒有形成與移植法律相適應的新文化基礎,這將使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水土不服”,導致法律的異化。
4.2 社會認同法律的現實障礙
現代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引入是一種“被迫性移植”。雖然有清政府實施新政的要求,但更多是外國勢力強加所致。現代中國對知識產權規則的接受在一段時間內是“被動移植”,即國內立法是在國際貿易體系的框架內進行的。在知識產權法中,公眾缺乏社會認同感,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法律移植的差異性認識。當地社會成員接受法律移植有不同的法律期望,要么支持法律移植,要么反對法律移植。今天,考慮到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和各國利益的不平衡,這種情況必然會對當地社會產生不同的看法。第二,法律移植的需求是有限的。法律通常從發達國家移植到需要它們的欠發達國家,而不是相反。當一些知識產權制度或規則超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時,由于當地社會和機構解決方案的內部需求不足,法律移植的有效性將受到影響。
4.3 現代知識產權法建設中的文化缺失
知識產權法進入中國僅100來年時間,進入公共生活只是近10年、20年的事情。我相信,知識產權法律構建的成就雖舉世矚目的(Bergs博士,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席)。然而,知識產權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知識產權的制度創新和改革需要相應的法律文化改革和重建,倡導創新、尊重知識產權精神是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基本理念。它既具有“以人為本、神圣私權”的先進思想,也蘊涵著“利益平衡、和諧和諧”的地方傳統的合理內核。從中國知識產權建設的現狀來看,涉外法律的精神基礎,未能隨之移植而本土化,地方文化精神也未能加以轉化而現代化,這些都是知識產權法律構造中的文化缺失。
5 結語
本文分別從:第一,“逼我所用”還是“為我所用”:知識產權的立法背景;第二,“超高”保護還是“過低”保護: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第三,“分散管理”還是“集中統一”:知識產權的行政管理;第四,“認同缺乏”還是“精神內化”:知識產權的文化基礎這四個方面分析了中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最后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對今后的專家學者研究相關的課題有一定的幫助與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知識產權法律構造與移植的文化解釋[J].吳漢東.中國法學.2007(06):23-24
[2]文化多樣性的主權、人權與私權分析[J].吳漢東.法學研究.2007(06)76-77
[3]論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棘齒機制[J].蒙啟紅.全國商情(經濟理論研究).2007(01):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