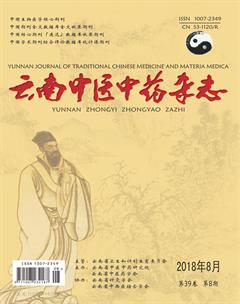血府逐瘀湯治療中醫(yī)腦病的臨床研究進展
李義 熊洪艷
摘要:血府逐瘀湯為清·王清任所創(chuàng),是治療血瘀證的代表方、常用方,因配伍精妙,臨床療效顯著,故可用于多科血瘀證疾病的治療。當前我國腦病隨老年人口數(shù)量的增長而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血府逐瘀湯在治療中醫(yī)腦病方面有獨特療效,現(xiàn)將近年來血府逐瘀湯治療腦病的流行病學調(diào)查、臨床應用等內(nèi)容進行綜合分析,希冀為臨床、教學和科研提供進一步參考。
關鍵詞:血府逐瘀湯;中醫(yī)腦病;臨床應用;綜述
中圖分類號:R7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349(2018)08-0088-04
血府逐瘀湯出自《醫(yī)林改錯》,為清·王清任所創(chuàng)。王清任為“近代解剖學家”,傾其一生醫(yī)學心得和臨床經(jīng)驗總結,創(chuàng)作了唯一的一部傳世佳作《醫(yī)林改錯》,全書載方33首。王清任特別重視實踐,對人體解剖和氣血理論做出了進一步發(fā)揮,在解剖學思想和活血化瘀學說方面有獨特貢獻。王清任根據(jù)瘀血停留在人體的不同部位創(chuàng)立了系列“活血逐瘀湯”,其效靈驗,為后世醫(yī)家所關注,廣泛推崇于臨床。據(jù)《醫(yī)林改錯》記載,血府逐瘀湯單獨應用或聯(lián)合其它方藥可治療22種癥目[1]。王階等人通過收集文獻資料,發(fā)現(xiàn)血府逐瘀湯可治療多科疾病,總計約200個病種[2]。血府逐瘀湯臨床應用范圍廣泛,治療中醫(yī)腦病有獨特療效,現(xiàn)將近年來血府逐瘀湯治療腦病的臨床應用概況進行綜述分析。
1 腦病流行病學調(diào)查
中醫(yī)學對腦及腦病學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臨床經(jīng)驗,腦病主要有頭痛、中風、癡呆、癇病、不寐等。流行病學調(diào)查可以為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提供依據(jù)。腦病種類繁多,病變復雜,癥狀廣泛,本文重點介紹幾種臨床上常見的有代表性的腦病流行病學情況。
頭痛在腦病中較為常見,2013年國際頭痛協(xié)會發(fā)表了第3版《國際頭痛疾患分類》的試用版,將頭痛分為原發(fā)性頭痛、繼發(fā)性頭痛以及疼痛性顱神經(jīng)病、其他面痛及其他頭痛[3-4]。世界衛(wèi)生組織減輕頭痛負擔研究項目調(diào)查顯示,中國成人頭痛發(fā)病率為24.6%[5]。中國最新流行病學調(diào)查表明,我國人群頭痛的年患病率為23.8%,其中偏頭痛為9.3%、緊張型頭痛為10.8%[6]。
中風包括現(xiàn)代醫(yī)學腦血管疾病,腦卒中是急性腦血管病的簡稱,是當前人類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世界衛(wèi)生組織公布:腦病的中風傷殘調(diào)整壽命年(DALYs)排在首位;發(fā)展中國家中風死亡占全世界中風死亡的85.5%,其DALYs是發(fā)達國家的7倍;2004~2005年衛(wèi)生部組織完成的全國第三次死因回顧抽樣調(diào)查報告顯示,中風已躍升為我國居民死因的首位[6]。
中風癡呆病主要指現(xiàn)代醫(yī)學的血管性癡呆,血管性癡呆是癡呆的重要類型,也是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的嚴重階段,曲氏等對我國1980年-2011年社區(qū)55歲以上人群中中風癡呆病流行病學進行Meta分析,患病率合并值為0.8%、發(fā)病率合并值為0.27/100人·年、死亡率合并值為14.6/100人·年;中風癡呆病的患病率、發(fā)病率均隨年齡的增加而升高[7]。
癇病主要指現(xiàn)代醫(yī)學的癲癇,癇病是一種反復發(fā)作性神志異常的病證,俗稱“羊癇風”[8]。當前,世界上有5000多萬癇病患者,4/5患者在發(fā)展中國家;中國有900多萬癇病患者,每年的新增病例約為45萬,農(nóng)村地區(qū)患病率高于城市地區(qū)[9-10]。
面痛包括現(xiàn)代醫(yī)學的三叉神經(jīng)痛,三叉神經(jīng)痛以三叉神經(jīng)走行分布區(qū)陣發(fā)性劇烈疼痛為主。1756年法國的Nicolas Andri首先報道面痛,面痛在我國多見于40歲以上女性,發(fā)病率隨年齡增加而增長[6]。而面痛在美國的年發(fā)病率為4~5/10萬[11]。
不寐主要指現(xiàn)代醫(yī)學的失眠癥,不寐是以經(jīng)常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為特征的病證。不寐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調(diào)查顯示,約有10%的成人患有不寐,多發(fā)于婦女和老年人;中國睡眠研究會對6個城市進行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中國內(nèi)地成人不寐患者高達57%,遠高于歐美等發(fā)達國家[12]。
從上述流行病學情況可以看出,腦病嚴重威脅著我國民生的公共衛(wèi)生健康,必須給予高度重視,深入研究腦病,降低腦病的患病率、發(fā)病率、致殘率、死亡率是當前首要任務,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2 腦病血瘀病理機制
人體大腦與經(jīng)脈、氣血、津液等有密切的聯(lián)系。經(jīng)脈是運行全身氣血,聯(lián)絡臟腑形體官竅,溝通上下內(nèi)外,感應傳導信息的通路系統(tǒng),是人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腦病可出現(xiàn)“疼痛”癥狀,疼痛與瘀血、經(jīng)脈失養(yǎng)有密切關系,若人體經(jīng)脈阻滯,氣血運行不暢就會出現(xiàn)“不通則痛”;若人體氣血津液虧虛,經(jīng)脈失養(yǎng)就會出現(xiàn)“不榮則痛”。《素問·舉痛論》曰:“經(jīng)脈流行不止,環(huán)周不休,寒氣入經(jīng)而稽遲,泣而不行,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由此可知,疼痛與經(jīng)脈、氣血、寒邪有密切關系。若人體氣血運行不暢,則形成血瘀,瘀血阻于局部,則容易導致頭痛、不寐等腦病。《素問·舉痛論》又曰:“寒氣客于背俞之脈,則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由此可知,疼痛與寒邪、血虛也有密切關系。若腦部血脈出現(xiàn)病變,寒凝血脈,瘀滯內(nèi)停,新血難生,日久血脈失養(yǎng),就會形成虛實夾雜病證,例如中風、癡呆等腦病。故腦病的血瘀病理機制主要是由于經(jīng)脈阻滯,氣血運行不暢形成血瘀,以實證為主;或氣血津液虧虛,經(jīng)脈失養(yǎng),血液推動無力,瘀血停滯,久病必瘀,以虛實夾雜為主。
3 血府逐瘀湯治療腦病的臨床應用
腦部疾病譜隨老年人口數(shù)量的增長而發(fā)生改變,當前有較大幅度的增加。腦病種類繁多,病理機制復雜,癥狀廣泛。以下對臨床上的幾種腦病進行介紹。
3.1 頭痛 頭痛在腦病中較為常見。頭痛首見于《黃帝內(nèi)經(jīng)》,并指出外感六淫和內(nèi)傷雜病是導致頭痛發(fā)生的主要病因[13]。瘀血是頭痛的一種常見病因,清·王清任提倡瘀血學說,在《醫(yī)林改錯》曰:“查患頭痛者,無表證,無里證,無氣虛痰飲等證,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劑而愈。”無論外感還是內(nèi)傷,都可引起人體經(jīng)脈不通,導致氣血運行不暢,形成血瘀性疼痛。醫(yī)者在臨證時,若見血瘀證之癥狀、體征,即可用血府逐瘀湯加減化裁治療,屢試屢驗。霍氏等[14]采用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急性期偏頭痛,觀察組50例用血府逐瘀湯加減,對照組50例用尼莫地平片及谷維素片,結果:觀察組患者偏頭痛發(fā)作次數(shù)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路氏[15]采用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叢集性頭痛54例,結果:治愈36例,有效14例,無效4例,有效率92.6%。
3.2 缺血性中風 中醫(yī)將腦梗死歸屬于缺血性中風范疇。《內(nèi)經(jīng)》曰:“血之與氣,病走于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缺血性中風多是在內(nèi)傷積損基礎上,復因外感或內(nèi)傷等,引起臟腑陰陽失調(diào),血隨氣逆,肝陽亢盛,內(nèi)風生動,夾痰夾瘀夾火,橫穿經(jīng)絡,蒙蔽清竅所致。瘀血既是本病的病理產(chǎn)物又是致病因素。賈氏等[16]用血府逐瘀湯治療急性腦梗死溶栓缺血-再灌注損傷患者,對照組50例溶栓并口服阿托伐他汀鈣片,治療組50例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血府逐瘀湯加減,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P<0.05)。朱氏[17]治療缺血性腦卒中,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聯(lián)合血府逐瘀湯,結論:血府逐瘀湯聯(lián)合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可明顯提高療效,改善患者癥狀,縮短療程,減少復發(fā)。
3.3 出血性中風 《靈樞·百病始生篇》曰:“起居不節(jié),用力過度,則傷陽絡,陽絡傷,則血外溢。”腦出血是非外傷性腦實質(zhì)內(nèi)出血,臨床上其致死率與致殘率呈上升趨勢[18]。中醫(yī)將腦出血納入出血性中風、頭痛、眩暈等范疇[19,20]。沈氏等[21]用血府逐瘀湯加減聯(lián)合西藥治療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對照組32例采取常規(guī)西藥治療,觀察組33例在對照組基礎上聯(lián)合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結果: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93.94%高于對照組71.88%(P<0.05)。
3.4 中風癡呆病 孫思邈認為癡呆與血瘀有關,《千金翼方》曰:“下焦虛寒損,腹中瘀血,令人善忘。”血管性癡呆屬于中醫(yī)“中風癡呆病”范疇,在中國是最為常見的癡呆原因之一,田金洲等[22]將血管性癡呆分為腎精虧虛證、痰濁阻竅證、瘀血阻絡證、肝陽上亢證、火熱內(nèi)盛證、腑滯濁留證、氣血虧虛證7種證型。王氏[23]用血府逐瘀湯合安理申治療血管性癡呆24例,結果:顯效9例,有效11例,無效4例,總有效率83.33%。韓氏等[24]用血府逐瘀膠囊聯(lián)合腦苷肌肽治療血管性癡呆110例,療效顯著,可改善患者認知功能、日常活動能力、神經(jīng)功能損傷的程度[24]。
3.5 癇病 癲癇與中醫(yī)學“癇病”基本相同,王清任認為癇病是由于元氣不能上轉(zhuǎn)于腦髓,瘀血阻于腦絡,腦失所養(yǎng)而成本病。中醫(yī)認為癲癇是由于先天、外因、內(nèi)傷等因素觸動風火,痰瘀內(nèi)阻,蒙蔽清竅,元神失控,氣機逆亂引發(fā)本病。司氏等[25]對癲癇常見證型進行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痰瘀阻絡證(10.53%)是常見證型之一。王氏等[26]在常規(guī)治療基礎上應用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腦外傷所致難治性癲癇40例,結果:顯效30例,有效8例,無效2例,有效率95.0%。江氏[27]用血府逐瘀湯加蜈蚣全蝎加減治療癲癇,中藥組32例,西藥組28例,結果:中藥組不良反應4例,西藥組不良反應10例,差異有顯著意義(P<0.05)。
3.6 面痛 三叉神經(jīng)痛的發(fā)生與手足陽明經(jīng)和足少陰經(jīng)脈循繞側(cè)頭面部的走行有密切關系,邪入經(jīng)絡,瘀血內(nèi)阻可引發(fā)本病[28]。中醫(yī)文獻中尚無三叉神經(jīng)痛的明確記載,根據(jù)相似特征及臨床表現(xiàn),可歸屬于中醫(yī)“頭痛、面痛、頰痛、眉棱骨痛”等范疇[28-30]。朱氏等[31]治療三叉神經(jīng)痛,對照組50例給予DSA引導射頻熱凝治療,觀察組50例在對照組基礎上聯(lián)合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結果:觀察組改善情況優(yōu)于對照組(P<0.05)。
3.7 不寐 中醫(yī)將失眠癥歸屬于不寐范疇,首載于《黃帝內(nèi)經(jīng)》。中醫(yī)、西醫(yī)的理論和實踐各不相同,在治療失眠癥方面各具特色和優(yōu)勢。西醫(yī)治療失眠癥見效快,但易出現(xiàn)依賴性及不良反應[32];中醫(yī)藥因綠色自然、簡便驗廉、不良反應少,在治療失眠癥方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優(yōu)勢。王清任首次提出應用活血化瘀法治療不寐,并創(chuàng)制了血府逐瘀湯,因臨床療效顯著,現(xiàn)仍被廣泛應用于臨床。羅氏等[33]用血府逐瘀湯加味治療失眠癥40例,結果:治療后匹茲堡睡眠質(zhì)量指數(shù)(PSQI)總分較治療前下降,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梅氏[34]用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頑固性失眠,對照組30例口服舒樂安定片,治療組40例采用血府逐瘀湯加減,結果:治療組有效率為92.5%優(yōu)于對照組73.33%,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4 討論
血府逐瘀湯是治療血瘀證的代表方、常用方,因配伍精妙,臨床療效顯著,故可用于多科血瘀證疾病的治療。本方由桃紅四物湯和四逆散加桔梗、牛膝而成,其中熟地易生地,白芍易赤芍,枳實易枳殼。方中桃仁、紅花共為君藥,桃仁性善破血活血,紅花偏于祛瘀止痛;赤芍、川芎活血祛瘀,牛膝活血通經(jīng),藥勢向下,可引血下行,三藥能加強君藥活血之功,共為臣藥;生地性味甘寒、當歸性味甘溫,二藥可清熱涼血,養(yǎng)血活血,桔梗、枳殼一升一降,寬胸行氣,柴胡理氣行滯,升達清陽,共為佐藥;桔梗還可載藥上行,甘草調(diào)和藥性,共為使藥。本方配伍特點:活血和行氣藥相伍,祛瘀與養(yǎng)血藥相配,氣血升降兼顧,攻補兼施,合而用之,可使血活瘀化氣行,則諸證可愈,故為血瘀證之良方。現(xiàn)代藥理研究表明,血府逐瘀湯具有抗纖維化、保護心腦細胞、抗動脈粥樣硬化、改善血液流變學、促進細胞再修復等作用[35]。血府逐瘀湯治療腦病研究意義重大,因療效顯著、不良反應少,價格優(yōu)廉,綠色天然,具有巨大潛力,故在未來研究中應當深入挖掘血府逐瘀湯臨床用藥特點和規(guī)律,遵循循證醫(yī)學證據(jù),重視標準化、規(guī)范化、科學化,繼承和發(fā)展中醫(yī)藥理論,以促進中醫(yī)藥在臨床、教學和科研領域的創(chuàng)新。
參考文獻:
[1]王清任.醫(yī)林改錯[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5:20-27.
[2]王階.血府逐瘀湯現(xiàn)代研究與應用[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1:7-10.
[3]馮智英,鄒靜,華駕略,等.國際頭痛疾患分類第3版(試用版)-原發(fā)性頭痛部分解讀[J].神經(jīng)病學與神經(jīng)康復學雜志,2013,10(2):121-140.
[4]Headache Classif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IHS).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Headache Disorders,3rd edition(beta version)[J].Cephalagia,2013,3:629-808.
[5]李炳祺.對602例頭痛患者流行病學問卷調(diào)查[J].現(xiàn)代醫(yī)院,2011,11(7):72-73.
[6]呂傳真、周良輔.實用神經(jīng)病學[M].4版.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252,144,889.
[7]曲艷吉,卓琳,王華麗,等.1980-2011年中國社區(qū)55歲及以上人群中血管性癡呆流行病學的Meta分析[J].中國卒中雜志,2013,8(7):533-543.
[8]周仲瑛.中醫(yī)內(nèi)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03:172.
[9]洪震.癲癇流行病學研究[J].中國現(xiàn)代神經(jīng)疾病雜志,2014,14(11):919-923.
[10]常琳,王小姍.中國癲癇流行病學調(diào)查研究進展[J].國際神經(jīng)病學神經(jīng)外科學雜志,2012,39(2):161-164.
[11]謝光武.原發(fā)性三叉神經(jīng)痛的治療新進展[A].浙江省醫(yī)學會疼痛學分會.浙江省醫(yī)學會疼痛學分會成立大會暨首屆浙江省醫(yī)學會疼痛學分會學術年會論文匯編[C].浙江省醫(yī)學會疼痛學分會,2011:5.
[12]中國睡眠研究會.中國失眠癥診斷和治療指南[J].中華醫(yī)學雜志,2017,97(24):1844-1856.
[13]周仲瑛.中醫(yī)內(nèi)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yī)藥出版社,2003:303.
[14]霍麗榮,周平.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急性期偏頭痛的療效及對血清ICAM-1和IL-6水平的影響[J].四川中醫(yī),2017,35(4):124-126.
[15]路毅.血府逐瘀湯加減治療叢集性頭痛54例[J].河南中醫(yī)學院學報,2008,(1):61-62.
[16]賈世杰,王輝,張新廣,等.血府逐瘀湯用于急性腦梗死溶栓缺血-再灌注損傷50例[J].中國藥業(yè),2015,24(22):226-227.
[17]朱衛(wèi)東.血府逐瘀湯治療缺血性腦卒中[J].吉林中醫(yī)藥,2015,35(9):907-910.
[18]殷俊,陳磊,翟國鎖,等.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微創(chuàng)手術后繼發(fā)腦水腫的影響因素[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3,33(1):54-56.
[19]呂士君,焦久存,牛玉國.腦出血中醫(yī)病因病機之古今[J].遼寧中醫(yī)雜志,2007,(11):1541-1542.
[20]王永炎,魯兆麟.中醫(yī)內(nèi)科學[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4:285-542.
[21]沈涌,羅烈嵐.血府逐瘀湯加減聯(lián)合西藥治療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的臨床觀察[J].中國中醫(yī)急癥,2015,24(2):337-339.
[22]田金洲,韓明向,涂晉文,等.血管性癡呆的診斷、辨證及療效判定標準[J].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00,(5):16-24.
[23]王玉宇.血府逐瘀湯合安理申治療血管性癡呆24例療效觀察[J].浙江中醫(yī)雜志,2013,48(10):730-731.
[24]韓麗,李鵬超,張志敏,等.血府逐瘀膠囊聯(lián)合腦苷肌肽治療血管性癡呆的療效觀察[J].現(xiàn)代藥物與臨床,2016,31(10):1591-1594.
[25]司富春,宋雪杰,李潔,等.癲癇證候和方藥分布規(guī)律文獻分析[J].中醫(yī)雜志,2014,55(6):508-512.
[26]王景春,田佳新.血府逐瘀湯在腦外傷所致難治性癲癇的療效觀察[J].陜西中醫(yī),2015,36(6):653-654.
[27]江霞.血府逐瘀湯加蜈蚣全蝎治療癲癇32例[J].浙江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06,(6):381-382.
[28]陳小玲,胡慶鐵.三叉神經(jīng)痛的辨證論治[J].新中醫(yī),1997,(3):62-63.
[29]周星楠.針灸治療三叉神經(jīng)痛的臨床實踐[J].中國醫(yī)院用藥評價與分析,2016,16(S1):165.
[30]陳玉璽.張明波老師治療原發(fā)性三叉神經(jīng)痛臨床經(jīng)驗總結[D].遼寧中醫(yī)藥大學,2015.
[31]朱洪寬,張順吉,陳永倫.DSA引導射頻熱凝聯(lián)合血府逐瘀方治療原發(fā)性三叉神經(jīng)痛療效及對血漿β-內(nèi)啡肽及P物質(zhì)的影響[J].現(xiàn)代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17,(27):3020-3022.
[32]中醫(yī)中醫(yī)科學院失眠癥中醫(yī)臨床實踐指南課題組.失眠癥中醫(yī)臨床實踐指南(WHO/WPO)[J].世界睡眠醫(yī)學雜志,2016,3(1):8-25.
[33]羅春蕾,張?zhí)灬裕瑥垈ィ?血府逐瘀湯加味治療失眠癥40例臨床觀察[J].新中醫(yī),2017,49(3):33-36.
[34]梅世明.血府逐瘀湯治療頑固性失眠臨床觀察[J].中醫(yī)學報,2011,26(10):1244-1245.
[35]吳劍宏,陳幸誼.血府逐瘀湯方劑的現(xiàn)代藥理研究進展[J].中成藥,2013,35(5):1054-1058.
(收稿日期:2018-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