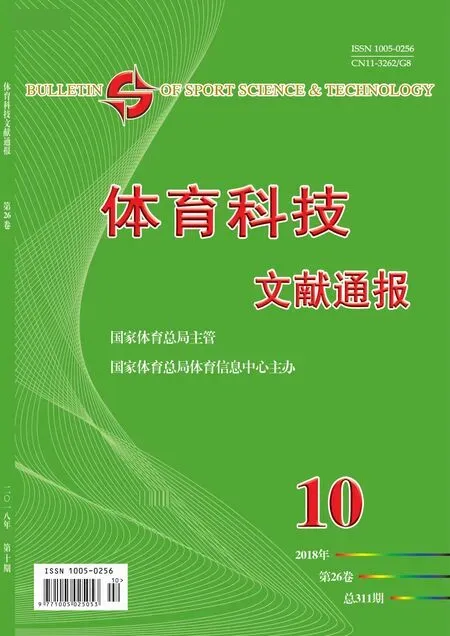“健康城市”國內外研究進展述評與建設啟示
范旭東
在當今世界,健康問題已經成為普遍性的、突出性的城市問題,而由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健康城市運動,正是旨在尋求這一問題的整體化解決。為此,各國及區域政府、組織、機構、國內外學者等基于不同視角,針對健康城市建設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1 “健康城市”的歐洲起源與發展動態
Cullingworth(1985)的研究顯示,為了促進居民身體健康、道德、品行與整體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英國在1909年頒布了第一步現代城市規范法案《Housing,Town Planning,etc Act 1909》。這可以看做是人類健康與城市發展在城市規劃領域的最早牽手。
1986年于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第一屆國際健康促進大會上一致通過的《Ott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健康促進:渥太華憲章》)中更加強調,建設更加健康的社會并非僅是健康部門的責任,全社會的健康促進勢在必行。
為了支持《健康促進:渥太華憲章》在各國家和地區層面的實施,推進新健康觀念的傳播,促進各個層面在全民健康改善過程中的擴部門協作,WHO于1986年設立了“健康城市工程”項目,隨后,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辦公室協同參與城市建立了“歐洲健康城市工程網絡”,以促進其成員之間的聯系、交流與合作。1987年加拿大政府啟動健康城市建設,多倫多、渥太華、魁北克等城市成為首批建設城市,并設有專門性機構推進該項工作。
1998年的雅典“健康城市國際會議”標志著健康城市活動已成為歐洲乃至全球性的運動。2003年后,歐洲健康城市網路逐漸完成第三階段建設任務,轉入可持續發展的第四階段建設過程。截至2015年,全球已有3000個左右的城市開展了健康城市建設工作,而這數字仍在不斷增加中。
2 “健康城市”國外研究進展與“運動即醫療”觀點
隨著健康城市運動的全球發展,健康城市的界定亦有了全新的內涵,WHO將其解釋如下:“健康城市是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結果來界定的。它不是一個已達到的特定健康狀況水平的城市,而是對健康有清醒的認識、并努力對其進行改善的城市。因而,任何城市,不論其當前的健康水平如何,都可以是健康城市;而真正需要的,是對健康改善有了承諾,并設置了相應的架構和程序來實現這承諾。”同時,為了強調健康城市建設中各部門的相互協調包容而非限制或抵觸,WHO還指出“只要基于健康促進的認同,每個專業可以結合自身的職能描述或重新定義健康城市”。這亦再次強調了健康城市建設過程中“健康”及“健康促進”是其根本的出發點和終極目標。為此,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結合自身的專業特點,在健康城市范疇開展了廣泛而有益的研究。
如Duhl(1999)在其專著中闡述了城市規劃對于健康城市建設的重要價值與意義。Gilbert(2011)從大氣環境的角度闡釋了空氣質量對城市癌癥發病率的影響,并提出健康城市下的空氣治理規劃,Herrin(2013)提出城市房屋質量與健康之間的關系。
2000年WHO研究報告指出,每年因各種疾病和其他健康問題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占世界總死亡人口的80%以上,其中以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惡性腫瘤為代表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下文均簡稱為“慢性病”)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頭號殺手,占到全球疾病負擔的70%以上。吸煙、酗酒、缺乏運動等不良生活方式,以及肥胖、高脂血癥發病率的迅速增長,更是加重了全球慢性病的負擔。
為此,WHO于2003年在瑞士日內瓦第55屆世界衛生大會上,發布了《全球運動有益健康概念文件》,并將每年的5月10日定為“運動有益健康日”,倡導開展全球性的“運動健康促進”項目,提升全球健康水平。
此后,各國研究者將“健康促進”及“健康城市”領域的研究聚焦到運動或體育健康促進工作上,Ronld(2004)的研究表明科學合理的運動及身體活動能夠有效改善II型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質量,具有顯著臨床治療效果;Jams(2005)提出規律性小負荷耐力訓練對于糖尿病患者具有明顯的治療效果;Edward(2007)的研究表明長時間耐力訓練有助于改善人體血脂水平,顯著降低高脂血癥的發病率;同時,尚有眾多研究者證明,科學合理的體育運動能夠有效治療肥胖、頸椎病、骨質酥松等慢性疾病,并對戒煙、戒酒、消除抑郁、客服心理障礙等方面有顯著療效;Harold Elrick (2013年)更是通過大量的臨床數據追蹤,提出“運動或體育既是醫療”(Exercise is Medicine)的重要觀點。
3 “健康城市”建設進展的中國答卷
我國健康城市的建設起始于1994年8月國家衛生部與WHO的合作項目,并選定北京市東城區和上海市嘉定區作為試點開展健康城市的規劃研究工作,海口市和重慶市渝中區于1995年6月參與健康城市運動,隨后大連、蘇州、日照等城市亦先后進入健康城市建設隊伍。2003年,上海市政府出臺《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三年行動計劃(2003-2005)》,成為我國首個全面開展健康城市建設的特大型城市。2014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愛國衛生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要探索開展全國范圍的健康城市建設工作。2016年7月,國務院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印發《關于開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鎮建設的指導意見》。216年11月,全球健康促進大會在上海召開,達成《健康城市上海共識》。2016年11月,國家衛計委發布《全國愛衛辦關于開展健康城市試點的通知》,確定38個城市為全國健康城市建設首批試點城市。
4 “健康城市”國內研究進展評述
從我國健康城市建設與發展的脈絡梳理來看,中國健康城市建設雖然晚于歐洲,且覆蓋范圍尚有所差異,但中國20年的健康城市建設亦積累了相當的經驗,我國學者從不同視角給予了健康城市建設研究相當的關注,尤其是對于體育促進城市人群健康及推動健康城市建設方面更是研究焦點所在,在所檢索的CNKI、維普科技、超星數字三大中文數據庫中,自1995年至今共有以健康城市為研究領域的研究文獻67篇,其中關于體育促進健康城市建設的文獻即有31篇。
梁鳴等學者(2003)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認為健康城市的構成應包含健康人群、健康環境和健康社會三大要素;傅華等學者(2006)在梳理中國健康城市建設理論過程中提出,以健康城市為載體來保障人群健康的概念;周向紅(2007)分別梳理了歐洲及加拿大健康城市建設先進經驗與發展規律,為我國健康城市建設提供借鑒;趙芳(2010)詳細闡釋了上海健康城市的建設過程中的健康促進能力發展走向;王蘭(2016)從大氣環境的角度論述了健康城市規劃的重要意義與作用;黃文杰等學者(2016)基于大數據調查,給出了健康城市指標體系的描述性系統評價。
鄧星華等學者(2005)倡導的體育人文精神的回歸與體育價值的重構,在肯定體育生物健康促進功能的同時,更加強調對人靈魂信仰內核的建構,進而引發體育在多領域的融合與延展,在隨后的健康城市研究領域亦有所凸顯;呂東旭等學者(2007)提出建設健康城市的體育健康促進目標體系,并于2009年詳細闡述了體育健康促進在健康城市建設中的作用與意義;顧紅(2012)從市民體育鍛煉認知的角度探索了其對健康城市發展的影響;李凌(2012)提出大力發展城市休閑體育路徑,建設健康綠道,發展建走運動的新觀點;鄭家鯤(2013)在健康城市背景下,詳細嘗試了學生體育健康促進行為的培養方法與路徑;張慶建(2014)為健康城市建設中的社區體育發展給出了發展對策與建議;魯海濤(2015)從多維健康觀視角,提出大健康概念,促進城市體育健康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鄭霞(2017)基于健康中國背景提出了健康城市的休閑體育空間供給側改革的模式與路徑。
5 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健康城市建設與研究在國內學界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眾多研究者雖然從不同視角闡釋了健康城市的建設作用與意義,但目前研究多集中于宏觀領域研究或理論的探索,缺失對一城或一地的解決方案與執行建議。而針對體育在健康城市建設過程所起的作用,亦局限在體育功能的理論論述,或提供某一方面的解決方案(如社區體育、休閑空間等),致使體育健康促進的過程僅僅變為體育介入的形式,而忽視了體育內在精神價值在健康城市建設過程中對市民的引導與激發,無法實現公民個體自發的、持續的、穩定的參與與堅持,難以促進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使健康促進的活動效果大打折扣。
為此,基于各城市社會經濟基礎、區域發展特色,創新體育健康促進的理念、模式與路徑,多維度、全周期的為各城市提供體育促進健康城市建設的解決方案就顯得尤為重要,這必將成為“健康城市”未來研究的聚焦點。